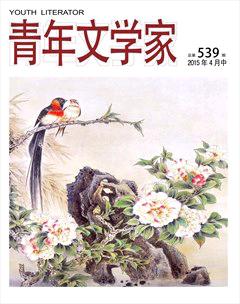電影中的夢境
摘 要:國外的電影有很多對夢境的表達,有的是純粹的幻想有的是為了生活而做夢。《伊萬的童年》和《穆赫蘭道》是其中的代表作,一個代表美國文化一個代表前蘇聯的文化。滋養他們的溫床不一樣,他們代表的夢境也不一樣。夢境和現實,夢中的人物都有不一樣的功能。能做夢對人來說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們可以回憶過去,幻想未來,也能占時麻痹自己。電影中的夢境是導演營造的,我們可以一同經歷、體驗
關鍵詞:夢境;現實;文化;渴望;幻想
作者簡介:漆佳(1990-),女,漢族,籍貫:四川省瀘州市,西南大學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在讀研究生,專業:戲劇與影視學。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2
電影就是造夢,我們都經歷著角色們的生活,好像自己做了一場夢。夢里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但是做夢的感受卻讓人上癮。很多導演不僅喜歡造夢還喜歡在電影這個夢里做自己的夢,讓角色做夢。觀眾經歷著雙重的夢境,體會著不一樣的人性感受。《伊萬的童年》是前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長故事片,伊萬的童年蒙受著戰爭的陰影,但在夢里確實一片繁花似錦、祥和安寧。《穆赫蘭道》是美國導演大衛·林奇的懸疑作品,女主角在經歷了一場車禍之后,仿佛墜入了另一個世界,充滿了冒險,夢醒后卻是殘酷的現實。這兩部電影創作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對于夢的闡釋卻那么獨特清晰,讓觀眾不自覺走入導演編織的夢境中。
一、夢境和現實
《伊萬的童年》是塔可夫斯基第一部長故事片,影片的背景是戰爭。戰爭會摧毀一切有生機的東西,毀掉一切美好,這些只能在夢里找到,夢境越美好現實就越殘忍。其實伊萬的內心還是一個小孩兒,但戰爭的陰影讓他過早的長大,而且是畸形的長大。為了復仇,他拒絕正常的生活,不愿意回到后方去上學,他需要在緊張的生活,復仇能夠支持他繼續活下去。伊萬的夢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渴望,但在現實中是絕不能實現了。伯格曼評價塔可夫斯基“他創造了嶄新的電影語言,把生命像倒影、像夢境一般捕捉下來”。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充滿了詩意的語言,悲傷彌漫開來很久都散不去。影片的最后死去的伊萬還在做夢,夢的最后一棵枯樹占滿了整個屏幕。塔可夫斯基通過這些夢境讓我們了解現實生活中的伊萬其實并不是他真正的樣子,12歲的年齡正是孩子天真可愛的時候,看看這殘酷的戰爭把孩子毀成了什么樣。沒有夢境的演示我們就無法看出現實的殘忍,戰爭對孩子的傷害。伊萬哪里還有孩子的樣子,那充滿復仇的雙眼,堅定的語氣,一切都顯得那么不合適,但他偏偏發生了。
夢境和現實的交互作用能讓我們看到單獨的一條敘事線索所無法表達的事情。在夢境的線索中,我們更能探尋人物的內心世界,他是不是這樣的人,在夢中一覽無遺。伊萬的母親和姐姐死在德軍的槍炮下,伊萬要為她們復仇,但是伊萬并不是天生就這樣的。《伊萬的童年》,其實伊萬并沒有童年,有得只是戰爭的創傷。他渴望和平和家庭,渴望一切美好的事物,卻始終無法得到。最后,伊萬死于絞刑。夢總是會醒的,塔可夫斯基卻在伊萬死后仍然讓他做夢,這不是伊萬的夢,是那個時代的夢,伊萬的一生結束了,但是他的夢不會結束,夢中的東西是一種象征,反對戰爭,期待和平。這并不會因為誰的死而結束,這是一個永恒的夢。
《穆赫蘭道》的夢顯然不同于伊萬的夢,伊萬的夢是對戰爭的批判和諷刺,穆赫蘭道的夢則是對現實的逃避。戴安娜和卡米拉在夢里夢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只是夢中兩人的身份對調了。現實中軟弱一事無成的戴安娜在夢中成了好演員,幫助卡米拉找回自己的記憶。這個夢是對現實生活中不可得的事情做的幻想,它不諷刺只是一種期望。《穆赫蘭道》是如何開始進入夢境的,影片一開始所有的角色就入夢了,但很多觀眾并不清楚,甚至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夢。知道影片快結束了,戴安娜被吵醒,觀眾才開始覺悟,原來之前的是一場夢,但又不敢肯定所有的東西都是夢。那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東西都是因為夢中的混亂,沒有邏輯也可以理解。塔可夫斯基對生命的思考,對戰爭的反思,大衛·林奇對夢境的探索,人性在夢中體現出來,在現實中得到印證。
大衛·林奇編織的夢前半段看起來很真實,似乎它就是現實,到后半段,匪夷所思的事情開始出現,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出現的。盒子旁邊的兩個老人,就是玩偶的大小,那場奇幻的表演,那把鑰匙,這些都可以和現實中發生的某些事對應起來,戴安娜為了掩飾自己做過的事情,將它們全部鎖在最深的地方,將自己做過的事情進行奇異的幻想,好像它們并不真實。但夢境醒來,她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最終絕望自殺。大衛·林奇的夢是奇幻的,有很多不真實的事件,但伊萬的夢中沒有任何奇幻的東西,只是對現實生活的渴望。夢境和現實在《穆赫蘭道》中被可以的模糊了,觀眾和角色都沉溺其中,入夢和出夢處理的讓觀眾幾乎感覺不出來,是夢里做了一場夢還是那個夢。夢境和現實是天平的兩頭,在生活中,現實占據了絕對重要的位置,但是兩位大師的電影里,夢境卻承擔了最重要的作用,一切的意義都實現在夢里。
二、文化差異下的夢
《伊萬的童年》是前蘇聯的作品,電影背景設置在二戰期間,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讓前蘇聯的民眾飽嘗苦難,當時的蘇聯人民都渴望和平。電影拍攝的時間是1962年,二戰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但是戰爭帶給人們的傷害還沒有遠離。塔可夫斯基通過伊萬的夢,表達了人民對自由和平的渴望。故事非常的簡單,一個被戰爭折磨的孩子,為了復仇成為了一個麻木的人,他沒有了童年,沒有了生活,有的只是對侵略者的恨。塔可夫斯基用了很多長鏡頭,在第一個夢境里,伊萬奔跑的鏡頭,在井邊喝水的鏡頭,節奏是那么緩慢,最終槍聲打破了一切的安寧和諧。塔可夫斯基不是在講故事,而是在表達一種感受,和平的生活是那么美好,那么值得珍惜。這一切到了大衛·林奇的手里簡直換了一個模樣。緊湊的情節,荒誕的故事,撲朔迷離的結局,故事的內容那么豐富,那么多種組合情節的方式,觀眾不停地被眼前的信息轟炸,甚至沒有時間細細的思考。造成這樣的差距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的文化不同。美國的文化就像麥當勞一樣,是快餐文化,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人們容易出現緊張煩躁的情緒。《穆赫蘭道》中的戴安娜就是其中的一員,現實生活將她壓的得不過氣,導致做出了極端的舉動。但是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卻沒有這樣的壓迫感,他的講述緩緩而來,觀眾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這一切究竟為什么會發生,責任在誰,我們應該要怎么樣。他不是在講故事而是在講述生活,生活本來就沒有那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平凡的力量更能直擊人心。《穆赫蘭道》確實是懸疑片中的佼佼者,夢境和現實的穿插讓觀眾如墜云端,卻不能抽身出來,那一刻,仿佛戴安娜的命運和我們自己聯系在一起,她是那么的無助和可憐,卻又做出讓人難以接受的事情。
用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的定義說:“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廣義而論,是個復合的整體,它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習1。”
蘇聯和美國顯然具有莫大的文化差異,自然它們對夢境的表達就不同。《伊萬的童年》中對夢境的使用是為了補充現實這條線索的缺陷,告訴觀眾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穆赫蘭道》準確地來說就是為了表現夢境,美國導演對夢境的表現是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來進行的,人在夢中的邏輯是混亂的,會出現很多奇怪的東西、奇怪的事,它們和現實生活中的某個東西相對應,除了做夢者和導演,觀眾需要努力地從影片中發現蛛絲馬跡。塔可夫斯基想要讓你發現電影的意義,讓觀眾開始反思戰爭,震撼心靈,反對戰爭的念頭越大戰爭就越不容易發生。涓涓細流往往有很大的力量,能讓你在無形中受到影響。塔可夫斯基的電影最重要的對生活對人性的思考,最不重要的就是故事,他不過是導演向觀眾傳遞信息的載體,這個載體不需要多豐富的語言,只要蘊含足夠多的信念。大衛·林奇卻不是這樣,眾所周知,美國電影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故事,強烈的戲劇沖突,緊湊的情節鋪排,環環相扣的發展鏈條,每一個步驟都不是多余的,它對情節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每一分鐘的時間觀眾都會被情節所吸引無法抽離,直到影片結束。《穆赫蘭道》在講故事上不是傳統的好萊塢電影風格,它一點也不好懂,但卻傳承了好萊塢的精髓,緊張刺激,無論是配樂還是情節,縱使你根本不懂這個情節實在講什么。它沒有什么留白,每一處都有導演留下的線索,亟待你去發掘。
三、夢中的人物
《伊萬的童年》中,伊萬的夢境里總會出現對自己最重要的人,他的母親和姐姐。這兩個人物是伊萬改變的開始。由于德軍的侵略她們都離他而去,她們代表的是美好,所以在夢里她們總會出現,她們成為伊萬活下去的動力,也許一切的努力就是為了能和她們在夢中相聚。《伊萬的童年》夢境中的人物很簡單,人物關系也不復雜,都是一眼就明了的狀態,但是每個人物都代表著一種力量,有的力量給予伊萬希望,有的力量摧毀伊萬的一切。《穆赫蘭道》夢境中出現的人物,也是戴安娜在現實生活中認識或者見過的人,不同的是,他們在夢中都換了一種身份,與原來的人物相去甚遠。這樣的狀況更像我們理解上做夢的狀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一定是對現實生活的某種反饋。在戴安娜的夢里,她想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那個世界里她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她在夢中還是沒能忘了自己在現實中所做的一切,所以她夢到了一切詭異的事情都和她殺人有關。
人物是故事的靈魂,沒有人物就不構成故事。我們平時做夢不一定非得夢到人,也許有動物也許是怪獸。在電影中,為了能基本的交代出故事,夢境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人物,有的是做夢者自己捏造的,有的是真實的。《伊萬的童年》人物都是真實的,現實和夢中人物的身份性格沒有差異,這使得伊萬的夢境更像是回憶,是他曾經擁有卻又失去的東西。《穆赫蘭道》中,人物的形象是真實的,但他們的身份和性格都是戴安娜幻想的,現實中并不曾有這樣的人物存在。某種程度上這表示,戴安娜并沒有經歷過夢中的一切,所有的東西都是她的幻想。她希望得到這一切,所以她幻想出不同的人物來滿足他,人物與現實生活中必須存在極大地差距,否則她就不能達到目的。《伊萬的童年》和《穆赫蘭道》夢境中的人物有著完全不同的設置和作用,前者代表美好的回憶,后者代表荒誕的幻想。
電影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觀眾就像做了一場夢,夢醒也許就忘了。電影中的夢境也是如此,夢境和現實的對照能讓觀眾感受到角色正在經歷的糾結,看到他們內心的渴望,不管是《伊萬的童年》還是《穆赫蘭道》,夢境里都有者做夢者的期許,這是所有夢境的共同點,不管夢中的是曾經的現實還是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后留給觀眾的,只能是夢中的感覺,這種感覺有的來自對生活的思考和表達,有的來自導演對現實的疑問,總而言之,電影中的夢境,是導演和觀眾一場共同的夢中夢。
注釋:
[1]Tylor.The Qrigins of Culture,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M],New York,19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