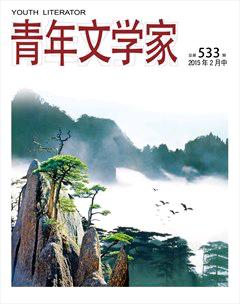《會飲篇》中的美學思想漫談
趙珺
摘 ?要:《會飲篇》是柏拉圖涉及美學較多的作品,在此篇中,蘇格拉底雖旨在為愛神寫頌詞,但通過對“愛”的親歷和認識,確是最能夠達到“美”的境地的,即所謂“愛美”。美的階層源于世界的階層,美感教育正是可朽的人為攀登上“美”的扶梯所進行的課程。同時,其他頌詞,如阿里斯托芬的頌詞,也是意味深重的,甚至是更具美學性的。
關鍵詞:美的上行;理式世界;愛與美的關系;美感教育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5-0-02
在《大希庇阿斯篇》篇末,蘇格拉底在探求美的本質而茫茫無所獲時,他得來的唯一益處是對“美是難的”的句子有了更深的認同。和希庇阿斯的交談是柏拉圖早期的作品,在中期作品《會飲篇》中,柏拉圖不再專門地為美開辟一次對話,而談“愛美”,為到達“美”而尋求到達的途徑。所以讀至對話結尾,雖仍然不知美為何物,但如何達到“美”,卻是清楚的了。
一、為“美的上行”抵達云端世界打開通途
對于美的區別和分層,在這里首先要理解柏拉圖對于世界的劃分,因為異質的世界中必然存在著符合其規律形態的“無須佐證”的“美”。這種“美”則分有了此世界所具的一切特質。
西方哲學界多喜用“三個”來構筑起一個概念的層進。柏拉圖的三種世界(可能“三重”更適合一些,代表著層減而非平行的關系)預示著美也將被毫無懸念地分成三種。
在柏拉圖思維中,理式世界作為唯一合法的真實存在者,現實世界只能是真理的一種尾隨者,藝術世界是尾隨者的尾隨。這種下行而非上行的單行關系,是理式世界普照下來的光芒由現實世界過濾給藝術世界,而藝術世界的產物卻無法再上傳至理式世界,這讓藝術世界成為被動的陰翳。
然而美果真是一個世界分有一種美嗎?和世界與世界的關系一樣,《會飲篇》中對美的理解與其說是有了進步,毋寧說是一種讓步,通過第俄提瑪的口,我們知道,從感性客觀世界中個別事物的美出發,認識理式世界最高的美,這無疑是為“美的上行”打開了一條通途。在《會飲篇》之前,柏拉圖是無法承認這種“逆行”的,理式世界永遠和感性世界存在著間離。在兩個感性世界中的“美”中出發,去關照另個無法觸及的世界中無限最高的“美”,當然,柏拉圖在這里只是提出一種可能性,為“美感教育”提供合理的依據。
二、愛與美的糾紛
《會飲篇》為了談話的順利展開集聚了一群精英人物,“會飲”本就含有酬神的舉動,所以酬答“愛神”成了這次會飲的一個主旋律,一個個人物以頌詞的展開結束進行登場與謝幕。就文本而言,對愛神的頌詞是飽含著對美的召喚的。顯然最初的幾篇頌詞幾乎是很自然地就將愛與美捆綁在了一起。
(一)蘇格拉底與蘇格拉底外的在場者談論愛與美
泡賽尼阿斯:“只有驅遣人以高尚的方式相愛的那種愛神才是美,才值得頌揚。”[1]P225
驕傲的阿伽通認為愛神是美的,甚至于把愛神看成絕美,這種美表現在于“秀美是愛神的特質”[2]P248,以至一切美的品質(如嬌嫩、正義、節制、勇敢)競相歸屬于愛神。
上述的言論證明美在愛神誕生的那一刻就“注定”顯現了,美成為愛神自覺性的伴隨本質。但這種“注定”刻意隱瞞了美的成因以及愛與美是何種關系,即使將愛神說成了絕美,這也不過是讓美成了愛神修飾性的一種附屬品。
蘇格拉底的頌詞借由第俄提瑪的教誨說出,是出于蘇格拉底無愛欲的天性, “蘇格拉底自己的靈魂在這方面多少是有缺陷的,無法提供相關的信息給自己。”[3]P35但他卻闡明了愛與美的兩脈暗流如何交匯。
第俄提瑪先是與蘇格拉底進了邏輯推理,美的反面不是丑,而是不美(缺乏美),中間存在著罅隙。愛神(他人口中的愛神,蘇格拉底口中的愛若斯)追逐的對象是美的,所以愛神本質是缺乏美與善的,所追求的必是缺乏的。
第俄提瑪繼而講述了愛若斯誕生的神話,貧乏神睡在豐富神的身邊,所以愛若斯降生(貧乏神所缺的是豐富,所以追求于豐富神,這種追求的成果本質上說是半成功的,因為她追逐到了本用于追逐的美的對象,所以這種結合產生的愛若斯注定也是分裂的,懸而未決的,非神的)。愛若斯是大精靈,即康德說的“沒有動物性而單純作為理性的東西”。同樣,愛若斯本質是愛欲,“即人與神的居間者”大精靈愛若斯“介乎人神之間”, 愛若斯從降生起即作為鐘愛者的身份追隨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是范式的神,是存活于理式世界不可更改的真“相”,理式近乎神界,她才是絕美。所以愛若斯追求理式美,同時也被感性世界中的一般人所敬仰追隨,“他們是人和神之間的傳語者和翻譯者”[4]P259。愛若斯為理式美與感性世界的事物美疏通一條互動的暗流,至此,愛與美之譯介便可而知。
相對于愛若斯介于美與丑之間,蘇格拉底的興趣更在于愛若斯介于無知與有知之間。于是他悄悄轉變了頌詞的方向,以哲學家的身份再次登場。柏拉圖認為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所以愛若斯以“智慧”為對象,愛若斯就這樣成為了“愛智慧”的哲學家,所以愛智慧者是“美感”教育的最高成就者,也被列為“第一等人”哲學家是最有可能觸及神性的人,“‘凝神關照為審美活動的極境,美到了最高境界只是認識的對象而不是實踐的對象”[5]認識到這一境界,即需要美感教育發揮作用。
(二)詩人與哲人之爭
蘇格拉底借第俄提瑪之口否決的了阿里斯托芬講述的神話,她說,“我知道有一種學說,以為凡是戀愛的人們追求自己的另一半。不過依我的看法,愛情的對象既不是什么一半,也不是什么全體。”[6]P264 雙方對于愛欲的流動方向,即“愛美者究竟愛什么”有著各自的見解。
且先看阿里斯托芬,他是一個諧劇作者,所創設的愛情因由的神話也非常的浪漫與滑稽。宙斯把渾圓的整一的人一劈為二,從此他們離散在這個世界,去尋求本屬于自己的那一半,一旦遇到,兩個一半的人便像磁石一般不再分離。“我們本來是完整的,對于那種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謂愛情。”阿里斯托芬以為的愛欲表面上似乎是肉欲的,實質是由分求合的一種召喚靈魂復歸的旅程,深處暗流涌動著的是靈與肉的沖突。
第俄提瑪提出了憑身體或心思的愛欲流動的兩種方式,但兩者都需在美中孕育,因為生殖只能播種于美以達到一種調和的境地。憑肉體的愛欲即表現為對美形體的向往,阿里斯托芬則認為愛欲表現的是對被分裂的另一半的求整合。第俄提瑪認為愛情的目的不在美,在憑美來孕育生殖,由此達到不死與永生,可朽的人具有不朽的性質,“愛欲指向一個開放的未來,愛欲指向人類的種的存續”[7],這是令平凡世界的人欣喜的事情。然而心靈的生殖力則更加旺盛,這是專屬立法者、偉大詩人、哲學家們的,養育的是心靈子女。這里將“美”幾乎作為“善”來看待,其道德的功勛更為閃耀。
阿里斯托芬創設的顯然是詩化的情境,諧劇式的外表和肅劇的內核。靈魂的契合潛藏在人類相擁交媾之下,這種純粹愛欲的流露,雖有靈肉激烈的沖突和排斥,但永處于永恒的追求之途中。蘇格拉底的愛欲流動正是求美善合一,達到至純的理式世界的最深密教的途徑,愛情僅作為方式存在,終有干涸的一天,不過那一天,哲人已憑臨美的大海而望洋興嘆,平凡人也受到后裔的憑吊與上天降下的福澤。“所謂純粹或理論的哲學有著詩的視域,這一沖突更深的靈魂學基礎在于血氣與欲求之間,或更狹隘地說,在于血氣與愛欲之間疑竇叢生的關系。”[8]阿里斯托芬用神話解釋了人化的愛欲之美,講愛欲之美“墮化”為凡人所屬的“求整合”。蘇格拉底卻是教可朽的人去追求神化的不朽。
三、美感教育
柏拉圖記述下的“愛情教義”染上了玄秘的宗教迷霧,但是到達最深密教的門徑的方法“美感教育”卻是非常質樸而清晰的記述。由蘇格拉底轉述女巫靈第俄提瑪的話,首先從愛某個美形體開始,以此一美形體度量彼一形體的美,“這就要在許多個別美形體中見出形體美的形式……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會不明白一切形體的美都只是同一個美了……他就應該把他的愛推廣到一切美的形體。”[9]P271這就類似于用必然的“共同感覺力”(康德提出)去認識到“形體美”。這樣以后,漸拋開皮囊之美,而探求珍視其“心靈美”,乃至廣大的“制度美”、“行為美”或學問知識之美,終于走向最深密教的門徑口:
“這時他憑臨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觀照,心中起無限欣喜,于是孕育無量數的優美崇高的道理,得到豐富的哲學收獲。如此精力彌滿之后,他終于一旦豁然貫通唯一的涵蓋一切的學問,以美為對象的學問。”[10]P272
這就是渴望到達的理式世界的美的純然本體了,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永恒的絕對的美。
柏拉圖此種行為是否是屬于先驗的,他給出一個宇宙萬物盡符合的超出概念的最高“理式”,這是先于一切而唯一真實存在的。“柏拉圖的任務是要堅持客觀論的立場,拯救現象,為各種美的現象找到存在的根基。因此,他力圖用美本身,美的本質來進行說明,這既是柏拉圖的深刻之處,是他作為思想家的偉大之處,同時又是他在思考什么是美時犯難之處。”[11]由于柏拉圖將所有美托付于深密而不可感知的“理式”,這種純然的孤立化絕對化將《大希庇阿斯篇》中的核心問題“美是什么”演繹得更趨晦澀難明。
四、凝神關照理式美的福蔭
柏拉圖以后,正如波普爾所說:“柏拉圖著作的影響,無論是好是壞,總是無法估計的。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圖的,或者是反柏拉圖的,可是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非柏拉圖的。”后來者都似乎有意識無意識地成為了柏拉圖產下的心靈子女的養育者。
正如它的姊妹篇《斐德若篇》中講述,“過去有一個時候,美本身看起來是光輝燦爛的。那時我們跟在宙斯的隊伍里,旁人跟在旁神的隊伍里,看到了那極樂的景象,參加了那深密教的入教典禮……那時隆重的入教典禮所揭開給我們看的那些景象全是完整的,單純的,靜穆的,歡喜的,沉浸在最純潔的光輝之中讓我們凝視。”[12]長久以來,在柏拉圖創設的理式美的蔭蔽之下,我們才有抬頭的勇氣望向灼目的太陽。
第俄提瑪在最后說道:“這種美本身的關照是一個人最值得過的生活境界,比其他一切都強。如果你將來有一天看到了這種境界,你就知道比起它來,你們的黃金,華妝艷服,嬌童和美少年——這一切使你和許多人醉心迷眼,不惜廢寢忘食,以求常看著而且常守著心愛物——都卑卑不足道。”[13]第俄提瑪認為值得過的生活是籠罩在理式美的光照之下的,加繆的《荒謬與反抗論集》中提出過,拒絕自殺的唯一理由是這個生活值得經歷。所以,也許只有接受這一系列的美感教育,通過對理式最高美的探索和追求,用愛欲來點燃通向這條最深密教路途的火把,才能拒絕死亡,贏來不朽。
參考文獻:
[1][2][4][6][9][10][12][13]柏拉圖.文藝對話集[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
[3][8]羅森.柏拉圖的《會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5:35,26,11.
[5]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2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10: 49.
[7]列奧·施特勞斯.論柏拉圖的《會飲》[M],伯納德特編,邱立波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1:283
[11]方姍.什么是美是困難的——對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的另一種解讀[J].美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