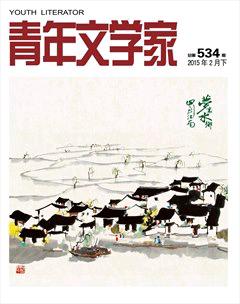二十年目睹社會之怪現狀
——關于黃建新電影文化斷想
摘 要:黃建新導演立足現實生活,借助平民視角從不同維度、不同方式記錄了高速前進的城市化步伐給城市生活帶來的多方面影響。本文將試析黃建新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想象與市民形象典型,梳理出都市演變中的現代性反思與人物承載的社會文化內涵。
關鍵詞:城市空間;平民視角;市民典型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6--01
在大陸的第五代導演之中,黃建新導演的另類性是顯在的。他的作品更多投射在都市形態的描摹上。黃建新電影無疑打破了這樣的間離效果,他規避了歷史的指認,著力于在現實的漩渦中完成個體價值與集體意志的直接性表達,這樣的表達是反諷性與兼容性的,在不斷縱深的城市空間中呈現出了商業都市的“現代性反思”。在黃建新的現實性鏡像中,我們看到的是小寫的“人”在龐雜的都市洪流中掙扎、反省,個體形態在社會機制中實現“蛻讓”。
一、都市幻影中的平民觸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一輪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深化發展,市場經濟大潮以鋪天蓋地之勢洶涌而來,中國進入了一個急速前進的現代化轉型時期。在這樣環境下,中國城市電影題材在審美維度與創作方式上產生了巨大變化。在黃建新電影中,“城市電影”一改表現主義濃厚的美學風格與批判反思性的精英姿態,俯下身去,將鏡頭融入蕓蕓大眾的日常生活百態度,“不隱惡,不虛美”,彰顯出生命體驗與人文關懷。
20世紀80年代末以《黑炮事件》揚名影壇的黃建新導演一改往日精英俯視姿態,以《站直了,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等完成了“客觀注視”到“主觀關注”的零度視野的轉變。在這些生活氣息濃郁的“城市寓言”中感知著商業時代里價值嬗變/人性扭轉的失語困境。在最為平凡的浮世畫卷里展示思想沖撞的多元情態,堪稱用影像架構了80年代中國社會變更的“人間喜劇”。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工人、個體戶等當代城市里各行各業各個階級的人物均以鮮活立體的形態成為城市生活的扎實地基,重塑了復雜迂回的空間形狀,完成了多元對立/相融的城市“碎片化構形”。在他的電影中,傳統價值觀念的善惡好壞評判尺度已然失衡,我們也無法且毫無必要去強力對人物進行價值衡量,群組式的都市圖譜化雕像展示出世俗又真實的底層風貌。正如黃健新導演所說:“人人有毛病,家家有苦衷;人人有優點,家家有真情。”在對傳統價值規范轉變的闡述當中,對世俗心態的精準描摹之中,黃建新導演加入了自我的批判性意識,在現代化轉型期用悲憫式的平民觸感傳達著極致性的都市體驗。
《站直了,別趴下》以“左鄰右舍”的微縮式景觀濃縮了社會文化的演變進程,舊有的社會階層不可避免走向衰亡與解體,新生權貴階層不可阻擋地崛起。影片通過個體戶張永武、政府代表劉干部、知識分子高作家三個人物犬牙交錯的人物關系,勾勒出社會文明演變的縮影。在龐大的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人們原有的意志形態、思想束縛都已解封,在逐利心態中默許了“怪象”的衍生與泛化,這何嘗不是一種人性的“扭曲”與“病變”?當張永武憑借財富開始具有話語主導權時,一向沉穩的國家干部開始焦躁惶惑,在飯桌上干部與個體戶的“國共合作”蘊藉著深層的社會反思空間:計劃經驗向市場經濟的“突變”瓦解了均衡化的社會結構與心理模式,導致了社會關系的重組與衍生。在新貴崛起的變更期,知識分子喪失了文化上的“剛性”優越感,在金錢面前自覺性地完成了自我價值與階層屬性的“蛻讓”。隨后的《紅燈停,綠燈行》延續了群組式的空間聚攏架構,通過“學車”這件細微的實踐延展出社會多元化的結構與階層,在細微之處對社會“怪象”進行了夸張與放大,將不同背景的人物進行合理的組接與勾連,完成了對新生社會的客觀性闡述,傳達出了被遮蔽的個體經驗的社會訴求。
二、欲望漂流里的反思與內省
欲望是底層社會介入都市化進程的一個關鍵詞,也構成了都市民間影像世界的重要內容。在黃建新的電影時空中,民間的物質與精神欲望無法在現實的都市空間里獲得完整的說法,只能通過反思與內省完成“想象性”的情感化解決。《站直了,別趴下》中,最后一個鏡頭全家福的傾斜似乎隱喻著虛化的集體化狂歡背后,是逐漸顛覆的社會價值與個體認定,這更是一種道德觀念與社會屬性的“傾斜與顛倒”,關于片中的人際矛盾在傾斜的主觀視角中被“假想性”地塑造成城市草根的和睦;在《紅燈停,綠燈行》的結尾,通過教練的“道德自覺”獲得“假想性”的情感彌合與人性回歸,但這樣的人文關懷過于極致性渲染,反而導致敘事形式與敘事內容的反思性割裂,在導演“人性美化”中流失了真實的現實批判力度,社會“怪象”在道德覺醒中被“想象性”解決。
然而,盡管黃建新導演中存在著一定的“人性美化”的趨向,但這也在某種內省層面上代表著導演對于“性本善”的最初回歸與期冀,對真善美主流意識的“皈依”與弘揚,對人性藝術化的“溫情撫慰”。但真實的社會形態仍值得我們反思與內省,黃建新導演在物欲橫流的時代讓我們“回歸傳統”,例如《電影往事》中的主人公在光影時空里完成了親情與愛情的雙重彌合,構成了自我價值的肯定與生存意義的確認。這樣的解決雖流于簡單化、純真性,但在虛擬的電影造夢里,導演卻讓我們歷經了最簡單質樸的社會愿景!正如彭浩翔《破事兒》中的杜汶澤在歷經與風塵女子的短暫邂逅之后,在面館獨自吃面時的黯然神傷令人感動憂傷一樣,也許電影的真正魅力并非是社會問題的“良方秘藥”,而是紛繁世俗潮涌下剎那的寧靜與安然,那一刻,正是人性最美麗之處。
參考文獻:
[1]路春艷.中國電影中的城市想象與文化表達.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2]聶偉.第六代導演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