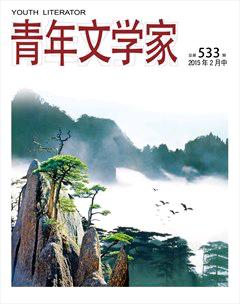“子所雅言”中“所”字用法探析
摘 ?要:孔子不僅在教育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在語言規范化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子所雅言”正是孔子對于規范當時語言的最好的見證,因此本文主要對“子所雅言”中“所”字用法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子所雅言;釋義;用法
作者簡介:竇倩男,女,河北省唐山市人,工作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5--01
一、“所”字釋義猜想
根據《康熙字典》對“所”字的解釋,另外筆者又結合對全句的意思的理解,找到了四種比較恰當的解釋,分別是:
(一)“所”,表所屬
“所”,表所屬,這句話里“雅言”所屬于“子(孔子)”,這時“所”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的”。“子所雅言”就可以解釋為“孔夫子常說的話”。
(二)“所”可理解為“指物之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里的“雅言”當是有別于常,意思是在講《詩》、《書》以及主持禮儀時,用“雅言”,以示尊重。“所”可理解為“指物之詞”。在(《康熙字典》“所”字條中,“所”所指的是詩、書,又進一步補充,執禮時都用雅言。
(三)構成“所”字結構
即,“所”字與后面的動詞結合,構成名詞性結構。例如: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
在“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個句子中,“子所雅言“為名詞性結構,“子”是“所雅言”(所字結構)的定語,古文中這種詞組形式不能獨立成句,只能充當句子成分,作主語、謂語或賓語等,所以要想這句話成立,需要構成“所”字結構,即與后面的動詞結合,構成名詞性結構。
(四)表示場合
即作為名詞,表示處所、地方、場合。例如:
不如早為之所。——《左傳·隱公元年》
雖眾,無所用之。——《左傳·僖公四年》
這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以解釋為“孔子說普通話的場合:(唱)《詩》、頌《書》、事禮,都是普通話。”
二、“所”字釋義之我見
筆者認為對于所字的解釋不能局限于這一種,因為對于它所在的句子的解釋不同,我們對于所字的理解與解釋就會產生差異。筆者比較同意本文中所字的第三種解釋,原因有二:
(一)放在句中解釋
要想探析”所“字的用法,我們首先應該了解整句話的結構及意義。
〔原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譯文1〕“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鄭玄
〔譯文2〕“《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朱熹
〔譯文3〕“雅、夏古字通”,孔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書》、執禮“則必用”平王東遷“以前”周室西都“周民族發源地陜甘一帶的夏音-——劉寶楠
〔譯文4〕孔子有用普通話的時候,讀《詩》,讀《書》,行禮,都用普通話。——楊伯峻《論語譯注》
〔譯文5〕先生平日用雅言的,如誦詩,讀書,及執行禮事,都必用雅言。——錢穆《論語新解》
由此可以得出,比較權威的解釋多是將“子所雅言”看做是整句話的主語。“雅言”名詞活用作動詞,與“所”字構成“所字結構”。
(二)《論語》中相似結構
在《論語》中像這種結構的句子較多,例如: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不難看出,在整個句子中,冒號前面的是整句話的主語,冒號后面做整句話的謂語,即“子不語”、“子以四教”分別作后面“怪、力、亂、神”、“文、行、忠、信”的主語。另外作主語的兩個短語又都是主謂結構的,其中:“子不語”中“語”名詞活用作動詞,“子以四教”中“教”本身就具有動詞形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和上面兩句的結構非常相似,從語勢看“《詩》、《書》、執禮”四字當連讀,與“子所雅言”組成一個判斷句,“子所雅言”作“《詩》、《書》、執禮”的主語,“子所雅言”這個短語中的“雅言”名詞活用作動詞:說雅言,講雅言的意思。那么這正好符合“所”字結構的用法,因為“子所雅言”充當判斷句的主語,“子”與“所雅言”構成名詞性結構,“所”字后邊的詞或詞組,一定是動詞性的,無論它原屬何種詞性,與“所”字結合后,都勢必動詞化。
此時“皆雅言也”自成一句,是對上句的補述。因此可以進一步印證了:“所”字與后面的動詞結合,構成名詞性結構的用法。
三、結語
孔子為當時語言規范統一,不僅教授《詩》、《書》和執禮時使用雅言,而且還為此做其他的努力。其一,整理古籍,同時進行正音正字的工作。其二,作《春秋》,參考、涉及多國的語言。其三,辦學、廣收弟子,皆以雅言教之。總之,“子所雅言”,是對語言統一規范的一種努力,是對中華語言的統一發展有著深遠意義的貢獻。孔子對中國古代語言的統一規范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李中生.《論語》“子所雅言”章辯義[J]中山大學學報.2003(02).
[4]郭墨蘭.孔子對中華古代語言統一的貢獻——“子所雅言”探析[J]東岳論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