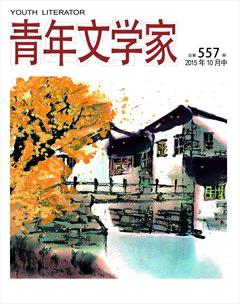美的選擇:青春版《牡丹亭》中“花神”的舞臺改編
摘 要:青春版《牡丹亭》對于花神的舞臺改編,是整出戲的一大亮點(diǎn),在服裝造型、道具的使用、舞蹈表演、登場的次數(shù)等方面與湯顯祖的《牡丹亭》及傳統(tǒng)版本的演出都有很大突破,是“意境美”的成功范例。主要從戲曲美學(xué)的角度,分析花神這一舞臺形象變革的美學(xué)價值。
關(guān)鍵詞:《牡丹亭》;青春版;花神;舞臺改編;美學(xué)價值
作者簡介:姜婷(1988-),女,湖北鄂州人,漢口學(xué)院中文系教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化文學(xué)的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9-0-02
“意境”是主觀與客觀、心與物的統(tǒng)一,情與景的交融,生動形象的呈現(xiàn)于豐富情感的寄托,并且這種交融和寄托還要有一定的深度[1]。意境是通過意象的深化而構(gòu)成的心境應(yīng)合、形神兼?zhèn)涞乃囆g(shù)境界。青春版《牡丹亭》中的花神是一個鮮活的生命意象,對于花神的舞臺改編,是整場劇目的一大亮點(diǎn),在服裝造型、道具的使用、舞蹈表演、登場的次數(shù)等方面較之傳統(tǒng)版本的演出都有很大突破,是“意境美”的成功范例,是對“美”這一意象較為成功的總結(jié)。本文旨在從戲曲美學(xué)的角度,分析花神這一舞臺形象變革的美學(xué)價值。
王驥德強(qiáng)調(diào)戲劇之道,出之貴實(shí),而用之貴虛[2],這種以虛代實(shí),虛實(shí)結(jié)合的藝術(shù)手段,正是中國古典美學(xué)的重要特征之一。戲劇的可貴,必當(dāng)有其因整體布局而有的美學(xué)作用,不在事相本身。這種充滿活潑生命意識與詩情的內(nèi)在精神心境,才是中國藝術(shù)所追尋的最高理想。
一、花神的服裝裝扮變革
昆曲服裝的設(shè)計(jì)是根據(jù)昆曲表演藝術(shù)的需要來進(jìn)行的,因此每件服裝在服務(wù)于表演的基礎(chǔ)上,還有利于輔助表演動作和增加舞臺色彩的美感。在長期的舞臺實(shí)踐中,服飾已經(jīng)成為刻畫舞臺人物性格、烘托情緒氛圍的一個重要的美學(xué)手段。服裝改革,也是戲曲改革的一個方面,服裝的風(fēng)格應(yīng)體現(xiàn)人物的特點(diǎn),傳統(tǒng)版的《牡丹亭》中的花神,色彩單調(diào),而且不利于舞臺氛圍的烘托,陳士爭版的《牡丹亭》則是大紅大綠,十分刺眼,不太協(xié)調(diào)。青春版根據(jù)劇情和塑造人物的需要,重新設(shè)計(jì)了服裝,呈現(xiàn)出一種素雅之美。
青春版的花神是有著仙氣和意境的,由一個主花神,兩個次花神以及十個小花神組成,手中不拿花燈花束,而是重新設(shè)計(jì)了花神服裝的顏色、款式和圖案,降低了服裝的亮度、彩度,以服裝上不同的四季花卉來區(qū)別身份。在服飾應(yīng)用創(chuàng)新上,特別添加了水袖和披風(fēng)的設(shè)計(jì),以當(dāng)令的花紋繡制花神的大披風(fēng),在披風(fēng)上繡制蘭花、菊花、海棠等艷麗的花朵。十二花神是在十二月令花的基礎(chǔ)之上,逐漸發(fā)展起來的民間俗神。十三位花神的服裝造型,在白底披風(fēng)上繡了十二種月令的花卉,獨(dú)創(chuàng)性很強(qiáng),美而不俗,素靜而雅致,青春版《牡丹亭》使花神的裝扮和歌舞,與主要人物的服飾風(fēng)格、歌舞韻律密切地結(jié)合起來,呈現(xiàn)一種和諧、淡雅、精致的風(fēng)格。
二、花神的道具創(chuàng)新變革
中國戲曲審美思想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虛擬。青春版中,大花神手中舉的幡是一個獨(dú)創(chuàng)性的虛擬設(shè)計(jì),幡的設(shè)計(jì),是從楚文化來的靈感,來自楚文化中的楚俑和招魂幡。長幡使舞臺空間顯現(xiàn)出“斷裂點(diǎn)”和“突破口”,使舞臺空間具有“不同質(zhì)性”,建立起杜麗娘夢境的“神圣空間”。大花神手中飄揚(yáng)的長幡在空中游動,使得劇中空間的層次變化感加強(qiáng)。招魂幡的運(yùn)用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戲曲表演以虛帶實(shí)、虛實(shí)結(jié)合的美學(xué)特征。
道具是寫實(shí)和寫意相結(jié)合的舞臺工藝物品,擺放在舞臺上的道具,既可用來交代劇中的情節(jié),又能夠烘托舞臺氛圍。道具的設(shè)計(jì)和使用,通常是以寫意為原則,以便有利于舞臺的表演運(yùn)用。劇中把彩幡用在花神催情﹑護(hù)送杜麗娘道冥府﹐接她回生的場面。根據(jù)劇情的發(fā)展和不同,幡在劇中出現(xiàn)有三種顏色,分別是綠、白、紅。《驚夢》一折中是綠色,綠色的幡隨風(fēng)搖曳,引杜麗娘入春夢,也象征著杜麗娘和柳夢梅愛情的萌發(fā);《離魂》一折中是白色,白色的幡代表著伊人逝去的哀怨,帶領(lǐng)著杜麗娘的魂魄入冥府;《回生》一折中則是紅色,燃起重生的希望。幡的顏色變化形象地傳達(dá)出劇中的情境和氣氛,呈現(xiàn)出虛實(shí)相化的空間。
三、花神的舞蹈語匯變革
王國維說: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3]。昆曲表演的屬性可以說就是一種獨(dú)特的歌舞表演。原來昆曲《牡丹亭》演出只是在《驚夢》中出現(xiàn)一些舞蹈,有時只是一個大花神。昆劇《游園驚夢》(1959)中的“堆花”表演由十二個花神扮生旦凈丑各種角色,手拿畫著代表一到十二月的各種花枝的絹燈,先由五月花神登場舞蹈,眾花神依次出場。站定后大花神出場,大花神身穿黃帔、頭戴九龍冠、手持牡丹花出場,眾花神合唱幾支曲子,唱時有的花神舞蹈,有的站著只唱不動,而陳士爭版(1999)中的花神則是由一個白發(fā)白須的老頭子扮演的,手持拂塵,只說不舞。
過去傳統(tǒng)戲曲、昆曲的舞臺上,較為講究“定格”。在青春版《牡丹亭》中,所安排花神的舞蹈場景,則是讓舞臺上起了流動感。透過舞蹈語匯、場面調(diào)度,讓花神、舞蹈不著痕跡地穿插其間,與整出戲合而為一[4]。劇中《堆花》的演出強(qiáng)調(diào)了這場夢境,具象地呈現(xiàn)出此情之美與善,渲染了一片春意盎然的氣氛。在舞蹈動作語匯的設(shè)計(jì)上,既強(qiáng)調(diào)戲曲表現(xiàn)的虛擬性,又不拘泥于約定俗成的程式性,對于舞蹈畫面的開創(chuàng)和開拓賦予了新的意義,特別是在畫面形態(tài)的“曲”和“圓”上,有著戲曲特有的旋轉(zhuǎn)韻律,體現(xiàn)出昆曲在虛擬化、寫意化以及程式化的特色之中所形成的獨(dú)特美學(xué)范式,融通了儒家傳統(tǒng)文化中和圓融的美學(xué)以及文化理想。戲曲在舞蹈中敘事,在舞蹈中抒情,在舞蹈中呈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戲曲舞蹈化的優(yōu)美語匯成為完整藝術(shù)形象所外延的情感。昆曲的舞蹈語匯是結(jié)合音樂歌唱,依循行當(dāng)配合手眼身步法的表演程式,將各套行動化為種種節(jié)奏性的線條,再組合創(chuàng)造富有表現(xiàn)力的舞臺形象,以抒寫情感與表現(xiàn)生活內(nèi)涵[5]。《牡丹亭》中運(yùn)用了很多舞蹈場面,以及場面的調(diào)度,讓花神與整個演出融為一體。《驚夢》是一個美好的夢境,這個夢境精辟地呈現(xiàn)出《牡丹亭》的主題“情”。杜麗娘和柳夢梅在夢中“結(jié)情”,而花神的出現(xiàn)則讓整個舞臺“境和”與“情和”,達(dá)到一種意境上、情與景的關(guān)系上、內(nèi)在精神和氣質(zhì)上的高度契合和理解。一連串的舞蹈設(shè)計(jì),不僅加濃了劇作的抒情風(fēng)格,而且使舞臺上充滿著詩意的畫面,如同經(jīng)歷一段美妙的旅程,但醒來發(fā)現(xiàn)還在人間。
四、花神的出場次數(shù)變革
在湯顯祖的原作《牡丹亭》第十折《驚夢》里,花神的情節(jié)交代很簡單,由“末”扮演的南安府杜家后花園的花神上場唱一曲〔鮑老催〕后就下場了。作為昆曲經(jīng)典劇目的《牡丹亭》,其傳統(tǒng)演出版本中的花神,只在《驚夢》“堆花”一折中出現(xiàn),而青春版《牡丹亭》中花神作為貫穿情節(jié)的重要意象,共出現(xiàn)了五次,顯得尤為突出。花神的唱詞也從原著中的〔鮑老催〕增加為〔畫眉序〕和〔滴溜子〕兩支曲子,還添加了“但是相思莫相負(fù),牡丹亭上三生路”的主題唱詞,起到了“點(diǎn)題”的作用。
花神首次出場,是在《驚夢》一折中,杜麗娘枕肘入夢,這時眾花神身披繡花紗衣,為情造夢,伴隨著昆笛編鐘和鼓的妙音圍繞于左右,她們張開寬大的袖袍,白色絲衫裊裊地舞動。在眾花神一一閃現(xiàn)退去后,出現(xiàn)了身著白衣的俊美小生柳夢梅。俊美的男子在花神的簇?fù)硐鲁鰣觯麄€舞臺場面唯美而不失大氣。《驚夢》里“堆花”一場舞蹈,滿臺五彩繽紛,又雅又艷。如果沒有花神的出場,整個舞臺表演就會黯然失色。是花神催動了杜麗娘的春情,是花神將柳夢梅和杜麗娘引到湖山石邊、芍藥欄前去私會。花神在《驚夢》出現(xiàn),氣氛一下子就起來了,像是一座山峰拔地而起,如果這個山峰起不來,氣氛就踏掉了。所以花神的出場很重要。絲帶的飄逸與昆曲唱腔的綿延融為一體,花神指法、身段等,都基本采用昆曲的程式。
花神的第二次出場是在《離魂》一折中,大花神舉著白幡上場,兩位次花神手托杜麗娘的紅衣,十位小花神群舞表演,帶領(lǐng)著杜麗娘入冥府;第三次出場在《冥判》一折中,判官道“喚取南安府后花園花神勘問”,出來四個小花神,她們?yōu)槎披惸镛q解并求情;第四次出場是在《回生》一折中,大花神舉著紅幡入場,十二位花神的舞蹈表演像是一朵漸次開放的層層疊疊的花,在花開放之時,杜麗娘穿著紅衣出場,象征重生;最后一次出場是在《原駕》中,十位小花神出場簇?fù)碇披惸锖土鴫裘罚嫱兄鴪A滿的結(jié)局。
劇情的全部進(jìn)展,都與花神緊密相連。在《驚夢》中催動杜麗娘的春情,借用了月老主男女婚姻之事的神職,見證了杜、柳之間的愛情,象征了二人相會的合歡之喜。在《離魂》中帶她死,在《冥判》中杜麗娘辯解和求情,在《回生》中帶她重生,最后再在大團(tuán)圓的《原駕》出場,歌頌?zāi)信鹘堑膼矍椤!笆ㄉ瘛钡某鰣鲣秩玖斯适碌睦寺髁x色彩,在生旦對角戲中增加的眾花神的群舞,對杜、柳愛情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五、結(jié)語
青春版《牡丹亭》的總導(dǎo)演白先勇先生提出的“昆曲新美學(xué)”的原則是:“尊重但不一定步步因循古典,選擇但避免濫用現(xiàn)代,古典為體,現(xiàn)代為用。制作的一切方向,都朝著抽象、寫意、抒情、詩化,體現(xiàn)昆曲美學(xué)進(jìn)行[6]。”這種美學(xué)原則緊貼昆曲的肌理,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可謂是做到了完美。青春版牡丹亭的“青春”,就是將傳統(tǒng)戲曲精華與現(xiàn)代審美情趣相貫通,在現(xiàn)代煥發(fā)出“青春”,不僅留住了熟悉傳統(tǒng)戲曲的年長觀眾,同時也吸引了具有現(xiàn)代審美思維的年輕觀眾。花神的舞臺改編不僅迎合了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情趣,也引領(lǐng)了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品位,從細(xì)微處反映出青春版《牡丹亭》在引領(lǐng)昆曲的新美學(xué)之路。
花神的造型和表演,牢牢抓住舞臺表演的傳統(tǒng)美這個核心,通過編導(dǎo)、舞美、服裝、音樂等舞臺整體美的有機(jī)結(jié)合,將古雅的昆曲藝術(shù)與現(xiàn)代氣息相溝通,較準(zhǔn)確地找到了傳統(tǒng)藝術(shù)與時代的契合點(diǎn),類似中國傳統(tǒng)的書畫藝術(shù),具有強(qiáng)烈的意境美。花神的幾次上場,都運(yùn)用主題曲的變化來烘托規(guī)定情境,既保留原來古典旋律美的風(fēng)格,又很具新意,整體音樂清雅、寬闊,呈現(xiàn)為人物心靈的折射,也烘托了舞臺表演的詩情畫意,使整個舞臺表演呈現(xiàn)出一種流動之美。雖然花神并不是劇情的主干,但是花神的出現(xiàn)作為情緒空間的一種升華,創(chuàng)造了一個情感濃郁的氛圍空間,用情緒來感染觀眾,使觀眾陶冶其中,得到怡情清心的審美享受。為了將劇作的內(nèi)在意蘊(yùn)化為可感可視的立體舞臺形象,編者進(jìn)行了巧妙的構(gòu)思和調(diào)度。于是,畫面、色彩、場景、情境,經(jīng)由“通感”的渠道,共同氤氳成稠密的特殊文化氛圍,使你感到撲面的濃烈,卻又不失含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花神的改編作為一種獨(dú)創(chuàng),無疑是成功的。
參考文獻(xiàn):
[1]駱 正.中國昆曲二十講[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7: 25.
[2]王驥德.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M].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154.
[3]王國維.王國維戲曲論文集[M].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 163.
[4]白先勇. 牡丹還魂[M].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4: 178.
[5]白先勇,陳怡蓁. 琴曲書畫昆曲新美學(xué)[M]. 臺北:天下遠(yuǎn)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165.
[6]白先勇. 青春版牡丹亭 [M]. 臺北:天下遠(yuǎn)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