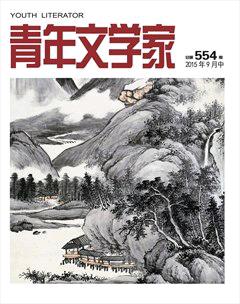淺析葉廣芩小說《月亮門》中的悲憫情懷
馬駿
摘 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家葉廣芩以其平和、溫婉的筆觸不動聲色地敘述著一個又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其創作題材涉獵之廣,主題挖掘之深令人驚嘆,更讓人無法忽視的是其作品里一以貫之的深切的悲憫情懷。本文以《月亮門》為主,主要分析小說中悲憫情懷的藝術表現,從她借助多元的敘事手段的詮釋來呈現作家獨特的藝術世界和審美追求。
關鍵詞:葉廣芩;《月亮門》;悲憫情懷;藝術表現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18-02
當代中國作家葉廣芩,本是北京市人,滿族,但她一九六八年十九歲時就到了陜西,先當知青,再當護士、記者和作家,歷任西安市文聯副主席、周至縣掛職縣委副書記、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雖然源遠流長的華夏思想,審美意識特別是漢語言文化對她有著根本而大的影響,但她的滿族出身和滿族歷史文化對她也有深遠的影響。正是這些內外在的共同因素,使得葉廣芩有了一顆悲憫之心,體現在藝術風格上,她平和冷靜敘事但不少溫情,嬉笑怒罵的冷幽默里卻是悲憫情深,這對作家溫婉又大氣的敘事風格,以及富有哲思的文本內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也是葉廣芩作品之所以能夠擺脫“新歷史小說”、“女性寫作”等標簽的根本原因所在。
小說《月亮門》主要講述了“我”與蘇惠五十年之后相見的情景,小說一開始通過老同學相約要見而開頭,之后采用回憶倒敘的手法,講述“我”和蘇惠情感的來龍去脈,最后又回到現實,順敘寫了她們見面的場景和“我”的情感。故事是比較簡單的,其中并沒有復雜的情感糾葛,正是這種簡單而又樸素的情感完全地吸引住了讀者,讓讀者跟著“我”一起開始回憶那段時光。
一、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
在小說《月亮門》中的“我”是貫穿全篇的敘事主人公,從一開始和蘇惠相約要見,到開始轉入回憶,讀者隨著作品中的“我”一起進入回憶視角,從“我”作為知青下鄉蘇惠前來送我以及當時我對她的情感,之后敘事時間繼續往前推入,作品中的“我”開始敘述學生時代的“我”和蘇惠以及當時圍繞在那月亮門左右的各種人和物和事,讓讀者不知不覺跟隨作品中的“我”一起回憶。作為第一人稱的敘事,讀者會有著不同于“我”的第二種情感,讀者會以一種統觀全局的視角完全體會作品中各個人物的情感。例如在寫到蘇惠對老七的愛意之時,蘇惠第一次讓“我”一個信封轉交給老七,還再三叮囑“我”說:“我”不可以看,“排隊買白薯的時候我把信封交到老七手里,老七問是什么東西,我說是蘇惠給的,讓他自己看。老七撕開花紙,里面是三斤糧票,困難時期的三斤糧票,其貴重程度無法計算。”[1]老七于是讓我還給蘇惠,但是“我”肯定是不愿意還的,在最后買白薯的時候,就順勢和自己家的糧票一起遞了過去,多買了十五斤白薯。我們現在來看當時“我”的心理活動:“老七在前邊蹬車,我在車上坐著,心里暗自發笑,前邊的倍值,后頭的認真,中間的我蔫兒壞。等于是我替老七受了蘇惠的饋贈,老七蒙在鼓里,蘇惠也蒙在鼓里。我承認,我把蘇惠的信交給老七的時間、地點都欠考慮。要不,蘇惠那顆少女的芳心下場不會那樣糟糕。可我也不知道那里頭是糧票呀,并且它是出現在我們買白薯的時候……”讀到這里的時候,讀者一邊會替蘇惠生氣,為什么“我”不能認真地把信封交給老七,一邊又能理解蘇惠,對于一個孩子來說,她當時的這種做法和心理是完全符合正常邏輯的。從這里我們也不難發現,作者是敢于正視現實的,努力掙脫自我的局限和狹隘,對自己熟知的人和事進行再次追問,從當事人和自身做出分析,對于可能是“我”制造出來的悲劇做出了反省,同時也對蘇惠流露出了同情。《月亮門》所體現的特質反映出了作家身上的那種獨特的悲憫情懷。
二、孩童視角的運用
不同視角的轉換是葉廣芩小說的顯著特色。其中以孩童視角最為引人注意,由于小孩子本身的年齡和經歷決定了他們認知的局限性,因此,以孩子的思維方式呈現的畫面不一定是最準確的卻是最為本質的、原生態的。
“那晚我要求和父親一起唾。躺在父親和媽媽的中間,我使勁抱著父親的胳膊不想撒開,媽說,這孩子怎變得跟小月窠似的。父親說,她是天天的見不著我,想我了,跟我撒嬌呢。”到后來蘇惠跟“我”說跟男人睡過的都會懷上小孩兒,之后“我”嚇得魂飛魄散,“我偷偷摸自己的肚子,暫時還沒有膨脹的跡象,但我知道它會慢慢長大,五姐姐就是這個樣子的。我每天都摸肚子,似乎覺得它在慢慢隆起了,害怕極了。我很憂郁,憂郁得有點兒茶飯不思,飯量大減。不敢跟媽媽說,也不想和蘇惠說,小小的心思一天比一天重。”[2]讀完這些內容,我們很容易被這個天真的小姑娘逗樂,當一個懵懂的小姑娘天真地自認為懂了很多的時候,跑去問家長,家長也會調侃她,而她自己也明白那是調侃,可是還是忍不住會害怕,她不能理解為什么大人會在自己孤獨無助的時候還漫不經心地調侃,瞬間她有一種被欺負的感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作家常通過孩童的視角來展現他自認為的大人的世界,但是這不代表她自己的價值判斷會被消解掉。從“我”的口吻中得知,“我”和蘇惠原本是屬于“形影不離”的,從兒童時的羨慕到青春期的嫉妒到成年后由于種種原因的不理解,導致了大約五十多年的不聯系,小說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籠罩在無法具體言說的憂郁之中。
三、平和冷靜的敘事
葉廣芩的作品始終貫穿著作家對人性、生命的情感觀照,平和、冷靜是其作品特有的敘事基調,作家以絕對清醒的姿態跳出個人視域,遠距離審視眾生命運和遭遇,深挖人性的缺陷。她的作品雖有人物糾葛、矛盾沖突但往往因其溫婉平和的敘述變得含蓄而內斂。
在《月亮門》中,“我”從一開始就對蘇惠的媽媽有著一種特別的情感,對她泡的玫瑰花茶,她的形態舉動,她的言行穿著,都是會讓“我”流露出一種逐漸想靠近的感情,所以在后來,當“我”看見蘇惠媽和“瓜子仁”的發生關系的時候,“在‘瓜子仁對她—次次的撞擊中,我看到了迎合,看到了投入,這讓蘇惠媽的形象在我的意念中徹底崩潰。崩成了一片破爛,再難拾掇。我已經沒有力氣使自己站立,我在月亮門這邊蹲下來,將臉埋在手心里,任由淚水涌出。”這樣平和冷靜的敘事,看似不動聲色,實則這已然牽動了讀者的心,一方面同情著蘇惠為了保護孩子們不得已做出的選擇,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性中最基本的一面即動物性,同時,也替“我”而傷心難過。在這里,作家并沒有刻意凸顯,情感波動大多借助情節的自然演進而慢慢表露。待文章行至末尾,讀者才最終了解到蘇惠媽與蘇惠的真實關系,以及那句“到時候我得完完整整還給人家”的真實含義,這時,讀者更多的不是對她與“瓜子仁”發生關系時的厭惡,而是不由得對蘇惠媽這種做法感到無奈和些許敬佩之意。這樣,在平和的敘事里,作家成功地借讀者之共鳴來表達自己對時代的悲劇、人的境遇的悲憫。
四、戲謔、調侃的冷幽默
葉廣芩善于用戲謔、調侃的口吻來勾勒人物的精神特征,以此來對人性、對文化、對社會等進行追問和詮釋。因此葉廣芩式的幽默早已超越了僅僅再現“京味”的符號作用成為她獨特的反思方式,即作家常常以同情的眼光審視筆下的群像,并對個體生命投射出極大的人文關懷,并將這一情愫凝結在富有冷幽默意味的文字里,使得作品總是表露出悲憫的情懷。
“說這話的時候我腦袋頂著個大中分,跟電影里的漢奸一個德行,是我媽嫌給我梳小辯麻煩,讓串胡同剃頭挑子給我剪的。剃頭的是走街串巷的天津寶坻人老鄭,老鄭屬于‘貼餅子熬小魚兒系列。他以當時寶坻的審美時尚,借助我那幾根黃毛,為戲樓胡同打造了一個讓人過目難忘的‘女漢奸。”作者以戲謔、調侃的口吻講述了當時自己被理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小漢奸”,對于這種發型如果換做蘇惠,那肯定是無法忍受的,但是對于“我”,就那么地接受了,即使周圍的人對我嘻嘻哈哈,反正不是“我”的錯,老師不正眼瞧“我”也無所謂。
葉廣芩常常是使用簡練的語言,依靠平和的敘事交代人物行為舉止,靠讀者的感同身受慢慢咂摸出其中的韻味來。因此,葉廣芩式的幽默和諷刺是含蓄而溫婉的;作家借助故事里的玩笑引起對人性、文化和歷史的追問和反思,看似輕松的玩笑中又浸滿了淚珠,其背后隱藏著作家的悲憫情懷,所以這份幽默是同情多于嘲諷的。
葉廣芩懷著一顆悲憫之心,運用精妙的小說敘事藝術為我們展現出了獨特的小說藝術世界,在作品中為我們呈現了精彩的人物形象及牽動人心的故事情節,讓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位有情有義的作家對人類社會和個體生命的傾情關注,也看到了作家以她獨特的寫作技巧和表達方式為我們精心構筑的藝術世界。
注釋:
[1][2]葉廣芩.月亮門[N]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