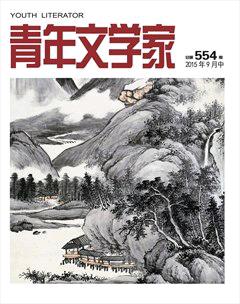淺談老舍早期的政治態度及轉變
摘 要:老舍是我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家,是我國新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并不對于政治十分狂熱,文學創作也是圍繞“民”而展開。但是建國以后,他對于自己創作的一些個人陳述卻與三十和四十年代他的論述不盡相同。本文將通過分析老舍早年的經歷和他的愛國思想來剖析他早年的政治態度。
關鍵詞:老舍;政治態度;文學創作;轉變
作者簡介:談沁怡(1994-),女,漢族,南京人,南京師范大學強化培養學院文科強化班,漢語言文學專業2013級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6-22-02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是二十世紀中國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展露了他的創作才華和對于人民生活的關注。后期老舍的政治態度有所轉變,他早年接受的教育和他的政治認識有也是導致他晚年的悲劇的重要原因。
一、早年與政治的錯過
老舍出生在北京一個平民家庭,父親“雖是個旗兵,可是已經失去了二百年前的叱咤風云的氣勢。”早年命途坎坷,一代文壇大師,竟然是到了十歲那年,“偶然遇見”劉大叔才得以上私塾。這位劉大叔在老舍的《宗月大師》一文中似乎就是宗月大師的原型,當時是個富人,后來皈依佛門,對于老舍一生多元的宗教思想的形成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老舍于1913年考入北京西城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學讀書,但是,困于經濟原因,好學的老舍偷偷報考了北京師范學校。在此期間,老舍對于中國古典的著作進行精細地閱讀,并且開始嘗試寫作。“我的中學是師范學院。師范學校的功課雖與中學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與國文。我對幾何代數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別人演題或記單詞的時節,我總是讀古文。我也讀詩,而且學著作詩,甚至于做賦。”不論是魯迅、胡適還是傅斯年,“五四”的先鋒們都是在吸收傳統文化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無論在這場運動中怎樣的批判“舊思想”,他們都是有著深厚的國文積淀的,深入內里的文化傳統并不是想要丟棄就能夠丟棄的。老舍無疑這一代成長在中國傳統文化里的文人,這也就使他對于北京生活的理解多了幾分民族性,對于中國白話語言的拿捏更加精準。
想要批判國民性或者說展示民族性,首先必須對于自己民族的向來傳統深入了解,但卻不至于浸透骨髓而不能自拔,這就需要作家對于傳統有相當的理性視角和一種距離感的保持。從師范學校畢業,老舍憑借他出色的成績成為方家胡同市立小學校長。經濟上的很大改善使得老舍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也走過一段彎路。在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
對于這個事件,老舍自己的說法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在1957年的《“五四”給了我什么》中老舍這樣寫道:“并不是說,作家比小學校校長的地位更高,任務更重;一定不是!我是說,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五四給我創造了當作家的條件。”他還細致地講述了自己在“五四”時期對于白話文的渴望,曾經不斷地嘗試寫新的東西。
但是在1935年的《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中卻寫道:“除了在學校里練習作文作詩,直到我發表《老張的哲學》以前,我沒寫過什么預備去發表的東西,也沒有那份兒愿望。不錯,我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曾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可是那不過是為充個數;連‘國文教員當然會寫一氣的驕傲也沒有。”在1918年至1924年他去英國教書期間,中國“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可是我們卻看不見老舍的身影,并非他的文章寫得不好不足以發表,而是因為當時他的政治熱情并沒有那么高漲。
1935年的老舍說:“前面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地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對于政治老舍似乎是并不關心,“五四”和“大革命”對于他來說是不夠熟悉的東西,他只是小學任職的人員而已,自認為是沒有資格去描寫、去評判的,所以他就干脆避開不談,就像蕭紅一樣,只落筆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上。
從老舍后來的文章來看,他揭露國民性就是寫中國最普通的民眾,最平常的家庭,最熟悉的場所。老舍的批判性是獨樹一幟的,站在“民”的角度看得更多,并不是為了契合當時的政治,只是單純地出于一顆愛國的赤子之心。
二、《貓城記》與抗戰——國家至上
老舍于192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教書,在英國,他的英語水平得到提升,并且閱讀了不少外國小說家的作品。“我是讀了些英國的文藝之后,才決定來試試自己的筆,狄更斯是我在那時候最愛讀的。”也就是在閱讀之后,老舍開始將自己多年來的對于中國的經驗記憶翻找出來,不斷地進行加工再造。老舍就是這樣,在一成不變的平淡日子里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內里有著如此深厚的文學記憶,需要通過一種文化上的比對,才能激發出來。通過在英國的文學熏陶,老舍的文學才華得以發揮。他的語言承襲了魯迅的犀利,但同時也不失英倫的幽默。在英國,老舍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就在這期間誕生。
歸國之后,1932年,他在青島寫下一部重要的作品《貓城記》,這是以他在英國的直接經驗寫成的一部科幻的諷刺小說。這部小說里老舍極盡諷刺之所能,將自己對于中國的現實每一點真實的感受一一記錄,通過對于貓星人王國的描寫揭露中國的黑暗現實。
但是老舍自己對作平不甚滿意。在1935年的《我怎樣寫<貓城記>》里他寫道:“我呢,既不能有積極的領導,又不能精到地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諷刺的弱點,而沒有得到它的正當效用。……眼前的壞現象是我最關切的;為什么有這種惡劣的現象呢?我回答不出。”這也體現了老舍對于政治的不夠關心,只是肩負起傳達的作用,卻沒有一個足夠支撐的立場,為國家尋得一條出路。老舍比起政治立場更加熱衷于拯救國家,對于國家的愛高于一切。所以他鞭撻了國民黨當局腐化的丑惡,也用“哄黨”、“馬祖大仙”等詞匯諷刺了共產黨當時的不夠成熟。
但在建國后,老舍反思道:“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發生的行動上,便缺乏了積極性,與文藝應有的煽動力。……最糟的,是我,因對當時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寫了《貓城記》,在其中,我不僅諷刺了當時的軍閥,政客與統治者,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這只因為我未能參加革命,所以只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們的熱誠與理想。”這種帶有認錯性質的口氣和他在1935年的反思相差甚大。那時的他“對國事的失望,軍事與外交的種種失敗,使一個有些情感而沒有多大見解的人,容易由憤恨而失望。”但是“失望之后,這樣的人想規勸,而規勸總是婦人之仁的。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能在糞堆上找到食物;一個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將就這堆糞。”老舍單純從文學角度在反思自己文學上思想性的缺乏不適于寫對于國家的政治作出評判的文章。作為一個作家而言,他是不會將就的,他是勇于直面自己創作不足的人。而他后期的話語是從內容到形式上徹底否定了自己《貓城記》的創作。
老舍是一個對于政治極其不敏感、不關心,但是卻關心國家安危存亡的人。在1938年,老舍說道:“愛你的國家與民族不是押寶……而應是最堅定的信仰。文藝者今日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這信仰去堅定別人的這信仰。”老舍就始終踐行著這樣的原則從事文藝創作。在抗戰中,老舍真正接觸到了政治,積極參與中華全國抗戰文藝抗敵協會的工作,努力做一個“文藝界盡責的小卒”。
正是秉承著愛國的熱誠老舍才會寫下不朽的名篇,但是對于政治的不夠敏感使他最終走上了悲劇的命運。
參考文獻:
[1]老舍:《正紅旗下》,《老舍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2]老舍:《宗月大師》,《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
[3]老舍:《我的創作經驗》,1934年12月,《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4]老舍:《“五四”給了我什么》,《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
[5]老舍:《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老舍文集》第15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6]老舍:《我怎樣寫<二馬>》,《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7]老舍:《我怎樣寫<貓城記>》,《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8]老舍:《血點》,《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9]老舍:《入會誓詞》,《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