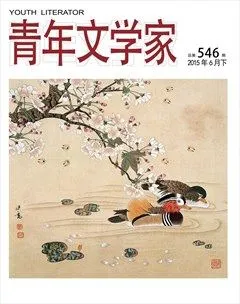那時,那時
莫晨霞
2014年的六一,我坐在臺下觀看學生的文藝匯演。服裝、音響、道具、燈光,表演者的水平,一切都是那么精美。這是一片由無數精美織就的云霞,當它們一片片在我眼前飄過時,1983年的六一卻像透過云霞的一道清麗的陽光,在我心頭輕輕撩撥了一下,然后回轉身沖著我莞爾一笑。
白襯衣,藍褲子,頭上紅色蝴蝶結。我要表演的是《一分錢》,講述一個拾金不昧好孩子的故事。那年我上三年級,表演的衣服是老師幫我從低一年級的女孩那借來的,因為我沒有白襯衣藍褲子,并且我實在是長得太瘦小了,簡直就是一根瘦瘦的豆芽菜。其實,我的綽號就叫豆芽菜。那天,豆芽菜因為能穿上白襯衣藍褲子在臺上表演而幸福無比。
我的臉上涂抹得紅紅的,像兩個紅鴨蛋長在了臉上。可我覺得那天自己特別漂亮,甚至感覺老師蹲下身子給我化妝的過程也是那么的美妙,我有點迫不及待地想上臺的樣子了。
“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民警叔叔手里邊……”
這首歌很短,所以,老師讓我在撿到一分錢之前加了另一支歌,我已記不得它的名字了,但是我記得它的歌詞:“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小鳥說,早早早,你為什么背著小書包?“我現在猜想,它應該是《上學歌》吧?我在上學的路上幸運地撿到了一分錢,然后興奮地交給了警察叔叔。我為自己能在臺上多呆一會而激動不已。
我在臺上又唱又跳。長得如同一根豆芽菜的我一點都不怯場。
與我搭檔的是一個男生,穿著黃綠色的卡其布做成的衣服,帶著一頂同樣顏色的帽子,帽子的前面釘著一顆紅色的塑料五角星。他一直筆挺地站在舞臺一角,他的臺詞只有一句:”再見!“但他演得無比認真。
那時候的我曾想,這應該是一個城市里的女孩吧?她穿著好看的白襯衣,她們那里有馬路,馬路上有警察叔叔……
這天的記憶就像一顆水晶葡萄,安靜地盛放在一個厚實而質樸的木碗里。而學校也漸次清晰了起來,它溫文爾雅地出現在我的視線里。
一道高高的木門檻,兩扇對開的大門,黑色的油漆斑斑駁駁,露出木頭原本的顏色。門上有兩個長滿了銅銹的門環,比我的頭還要高出許多。它們在我的眼里是那么莊嚴,因為年幼的我從沒在別的地方見過這樣的大門。每次進校門,我都會無比敬慕地望上一眼,就像看著一個我不認識的但肚子里藏著很多故事的老人。
老房子很大,但沒有舞臺,這舞臺是后搭的。據說是拆了正屋,改成一個“大禮堂“,當然是小小的大禮堂,舞臺正對著大門。臺下有兩根在當初小小的我的眼里看起來特別雄偉的大柱子,柱子已經掉漆,下面還有兩個圓圓的石墩。
據說,這里原本是一大戶人家的房子,解放那年主人攜全家逃走了,不知是逃到了香港還是臺灣。我想,他肯定是太急了,急得連賣房子的時間都沒有了。我想,在跨出這高高的木頭門檻的時候,他肯定回過頭投下了滿含憂郁的深深的一瞥。我甚至能聽到一個穿著青色長衫的男人對著房子發出的一聲長長的嘆息。
他不會知道,他的房子里有一天會涌進這么多的小孩,他家的青石板上會踏上這么多的小腳,他方方的天井里會飛揚著這么多孩子的嬉笑,他的東廂房,西廂房里會傳出“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愛毛主席”,或者“1加1等于幾”的聲音。他也不會想到他屋子的廊柱上有一天會掛上一個鋼軌,一個長著稀疏的胡須,帶著一副老花眼鏡的男人每隔幾十分鐘就會用一個大榔頭“當——,當當,當——,當當……“的極有節奏地敲上一通,緊接著,每一個教室里就會一下子涌出或者跑進四五十個孩子,讓人想到一張張吞吐著無數小魚或水草的鯨魚嘴巴。
現在這座學校已經不存在了。那天我路過它,一種神秘的力量拉住了我的腳步,讓我長久停留。風一陣一陣吹著,吹亂我的頭發和神經,以及我迷散的目光。天氣微涼,我沒有穿襪子,腳背上裸露的肌膚上有寒意像霜水一樣輕輕覆蓋,風從上面輕捷地跑過。我突然之間覺得這幢老舊的房子,多么像可以令我痛哭的親人。破碎的窗玻璃,裂開的白色紋路,像通往世界的無數條路徑,堅硬,鋒利,狹小,不容你選擇,如同我們無奈、頹唐,卻又有些微歡愉的人生。窗內的空間里,堆滿了積滿灰塵的雜物,他們像一個懶得翻身的農夫,質樸而狡黠,在微涼的天氣里他們選擇一成不變的姿勢回憶往事。
我長久地站著,風動我的寬大的褲管,吹動我略微有些干澀的頭發,甚至日見明顯的皺紋。我相信,人的目光是和身體同時老去的,在我將老未老的目光中,我仿佛看到了這座老去的建筑門口,灑滿了無力的陽光,一個將雙手攏在袖筒中的地主,戴著一頂黑色的呢帽,站在我的視野里。因為肥胖的原因,他的臉像雞蛋殼一樣發著淡淡的亮光。他朝我笑了一下,在他的笑容里,我看到細碎的日子慵懶卻又那么不可思議地飛快跑過,如同雪片紛紛揚揚,落在溫潤的初冬的土地上,遁了蹤影。
我想,這房子里應該住過他的幾房大小老婆,住過他外出求學的兒子,或者美麗的女兒。后來,又進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現在,這些愛過恨過笑過哭過打鬧過追逐過爭吵的鮮活的生命都流落到了何方?
風還是一陣一陣地吹著,它們或許認出了我?這個認出了這個表演《一分錢》的長大了,轉眼又長老了的豆芽菜?于是,對開的大門,門上的銅環,高高的木門檻,拼接得整整齊齊的青石板,雄偉的大柱子,雕刻著花紋的木格子窗戶,小小的“大禮堂”,以及大禮堂正中的舞臺,就一個個乘著風在我眼前飛過,我跟它們打招呼,可它們飛得那么快啊,似乎在趕著一次跟誰的約會。我聽到了歲月在風中發出的咯咯咯的笑聲,踏著它們神秘的凌波微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