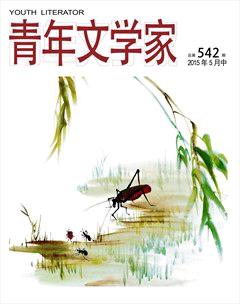桃花意象在唐代詩歌中的流變
李雪容
注:本文是長沙理工大學2012年研究生創新型課題論文。
摘 要:桃花作為意象,成為了唐代詩歌中重要的自然意象。隨著唐王朝的由盛轉衰,桃花意象也有著明顯的變化軌跡,由明艷轉灰暗、由繁富變簡約、由欣喜到哀傷。然而,其間始終存在著一股神秘的仙靈力量,這與有唐代宗教的興盛密切相關。
關鍵詞:唐代詩歌;桃花意象;流變;宗教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4-0-02
一
學界普遍將唐詩的發展分為初、盛、中、晚四個階段,而桃花意象也隨著唐詩的發展呈現出階段性特點。
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資糧,取給于道路焉。”[1]P452“貞觀之治”照耀下,初唐桃花也是絢爛多姿,滿載著激情與歡喜。一方面,與風光無限的江山、青春俏麗的佳人交相輝映,充分體現了新朝的萬千氣象。如太宗李世民《詠桃》中桃花是整座江山的縮影;長孫皇后《春游曲》中桃花不僅觸動了佳人的春情,更表露了詩人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受齊梁繁縟文風的影響,桃花詩歌也出現濃艷靡麗的特點,如宋之問《芳樹》(一作沈佺期詩)、沈佺期《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游》,書寫細膩,繁如富錦,對仗工整,格律精密。《新唐書·文藝中》:“魏建安后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2]P5751
初唐桃花詩受齊梁詩風影響,難免有繁富濃麗的弊病;盛唐桃花詩更重感情的抒發。李白隨性而發,在他筆下,桃花有“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3]P1724(《當涂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的瀟灑,也有“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3]P1751(《流夜郎贈辛判官》)的惆悵和“恩疏寵不及,桃李傷春風”[3]P1695(《上之回》)的憐憫。杜甫憂國憂民,桃花更多也是反面消極的象征,有“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3]P2538(《晝夢》)的夢牽魂縈,也有“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3]P2451(《絕句漫興九首》)的憤怒謾罵和“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3]P2438(《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的漂泊離愁。
但在盛唐詩中,桃花流露更多的是快樂。李白《山中問答》、《訪戴天山道士不遇》中“桃花”是飄逸仙骨的高歌,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喜晴》中“桃花”是淡淡哀愁中的喜悅,孟郊《與王二十一員外涯游枋口柳溪》、岑參《喜韓樽相過》中“桃花”是與友同游的愉悅……王維心系田園,桃花在他看來也多了幾分愜意和活力。“桃李雖未開,荑萼滿芳枝”[3]P1239(《贈裴十迪》)、“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3]P1278(《春園即事》)、“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3]P1306(《田園樂七首》)、“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3]P1298(《輞川別業》),詩人見證了桃花的一生,桃花也證明了田園生活的安逸靜謐。
安史之亂后,“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4]P359桃花意象背后呈現的情感也更加多元和復雜。
一方面,桃花作為故鄉的象征屢屢出現,并且染上悲情色彩。“故園柳色催南客,春水桃花待北歸。”[3]P1560(劉長卿《時平后春日思歸》)對于獨自在外的游子而言,家是不變的思念,這曾盛開在家鄉的桃花總會不經意間觸動他們的一腔相思。然而物是人非,“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3]P4148(崔護《題都城南莊》)桃花依然盛開,曾經的人已不再,“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3]P4112(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徒留無限傷感。故鄉渺遠,昔人已矣,容顏易老,這象征著溫馨美好的桃花也成了苦悶悲傷的化身。
另一方面,桃花盛開時光彩奪目,但花期短暫,經不起風吹雨打,俗話說:“三月桃花幾日紅,風吹雨打一場空。” 溫庭筠《敷水小桃盛開因作》:“二月艷陽節,一枝惆悵紅。定知留不住,吹落路塵中。”[3]P6744因此,桃花意象在詩中的時間意識非常強烈。“南家桃樹深紅色,日照露光看不得。樹小花狂風易吹,一夜風吹滿墻北。離人自有經時別,眼前落花心嘆息。更待明年花滿枝,一年迢遞空相憶。”[3]P4631(元稹《南家桃》)花開花落即是一年,映照著詩人的不幸:“他日未開今日謝,嘉辰長短是參差。”[3]P6203(李商隱《櫻桃花下》)
此時,還有一類詩歌,桃花甚至成為反面意象,如劉禹錫《秋詞》其二:“山明水凈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3]P4111這首詩重在寫秋,山明水凈,紅黃交加,情韻高雅,頗具君子風度,讓人敬肅。最后一句詩人用“春色嗾人狂”加以反襯,春天百花之輕狂更顯出秋天“深紅出淺黃”之嫻雅。春色以艷麗取悅于人,秋景以風骨陶冶情操,因此繁艷的桃花反而給人“濃得化不開”的嫌惡之感。又韓偓《湖南梅花一冬再發偶題于花援》:“湘浦梅花兩度開,直應天意別栽培。玉為通體依稀見,香號返魂容易回。寒氣與君霜里退,陽和為爾臘前來。夭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材。” [3]P4111用桃花與梅花對比,以桃花的輕佻襯托出梅花的高潔,在此,桃花成了趨炎附勢的無才小人的代稱。
隨著唐詩的發展,桃花意象由景致美到情致美,由外在的美艷到詩人內隱的情愫,意象表達漸趨復雜。
二
在唐代詩歌中,桃花常作為桃花源的象征,并時常打上宗教的烙印,文化意蘊深厚,審美情感獨特。
首先,桃花象征詩人對美好人間的向往,尤以桃花源為代表。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構建了一個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男女同作,老少同樂的純美世界,這也是唐代詩人夢寐以求的圣境,如張旭《桃花溪》、韓愈《桃源圖》、曹唐《題武陵洞五首》。“謫仙人”李白一生桀驁不馴,隨性灑脫,從不阿附于權貴,敢于讓龍巾拭吐、力士脫靴、貴妃磨墨,有著“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3]P1787(《南陵別兒童入京》)的壯志豪情,卻對“桃花源”情有獨鐘:“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3]P1813(《山中問答》))“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2]P1675(《古風》十五)“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里,將比通塘渠見羞。”[3]P1730(《和盧侍御通塘曲》)“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3]P1755(《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3]P1820(《答杜秀才五松見贈》)“石門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3]P1842(《下途歸石門舊居》)與桃花流水相伴,在紅花綠水間怡然自樂,詩人忘卻了一切俗世的煩惱。
其次,唐代文人筆下的桃花源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印記,成為與人間截然不同的、遙不可及的仙境圣地,正如王先謙所說:“《桃花源》章,自陶靖節之記,至唐,乃仙之。”[5]。在唐詩中,桃花時帶宗教意味,如元稹《劉阮妻二首》:“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3]P4640儲嗣宗《宿玉簫宮》:“借問燒丹處,桃花幾遍紅。”[3]P6882李群玉《送秦煉師》:“錦洞桃花遠,青山竹葉深。不因時賣藥,何路更相尋。”[3]P6590而宗教中的桃都是神物,自然生長于神境,敦煌詞《浣溪沙》(仙境美):“仙境美,滿洞桃花淥水。”[6]P125桃花是仙境的符號,因此,詩人常借桃花表達對仙境的憧憬,如王維《桃源行》、劉禹錫《桃源行》、白居易《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許渾《宿咸宜觀》。
唐代桃花意象這種宗教意味和仙靈氣息與唐代宗教發展密切相關。唐朝政教分離,宗教不干預政治即可存在,因此宗教興盛,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景教、摩尼教等多宗教并存,佛教與道教發展尤盛。除了太宗和高宗,其他皇帝都大力宣傳佛教。“武后大造佛像,中宗崇飾寺觀,肅宗、代宗在宮內設道場,憲宗命中使杜英奇至鳳翔法門寺迎佛骨。”[7]統治者“擢用方士,崇獎僧道”;文人士子也紛紛效仿,佛教徒比比皆是,如王維、杜鴻漸、元載等;百姓則“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寺廟數千,僧人上萬。道教是我國的本土宗教,修煉神仙之術,尊崇黃老之學。高祖李淵崇奉道教,并自稱是老子之后,建立老子廟。高宗奉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熟讀《道德經》,規定老莊之作為士子必讀書目,道教風靡一時,據《唐會要》記載,當時長安城內有三十多所道觀。宗教營造的是一個沒有硝煙彌漫,沒有陰謀權術,人人萬壽無疆,逍遙快活的極樂世界。因此,宗教往往和仙境緊密相連。唐代文人大都受道教影響,李白是道教教徒,賀知章也由佛教轉道教,王維也深諳道教,在他們文中時有一股仙風道骨。
三
唐代詩歌中桃花意象隨著政治的變遷而變化,在唐代詩人筆下,桃花不僅僅是春天的使者,代表著旺盛的生命、嬌美的容顏,更是詩人情感的寄托,寄寓了詩人對壯美山河的贊美、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對幸福生活的向往。雖然它帶有宗教的成分和幻想的泡影,但這種美好的追求正體現了唐代文人的積極進取、昂揚向上及對殘酷現實的不屈不撓,而這也正是唐代詩歌的魅力所在。
參考文獻:
[1](北宋)司馬光著,宋傳銀譯注.資治通鑒全譯第十三冊[M].貴陽:貴州人
民出版社,2002
[2](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吐蕃傳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清)彭定求等點校.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4](北宋)司馬光著,宋傳銀譯注.資治通鑒全譯第十五冊[M].貴陽:貴州人
民出版社,2002
[5] 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陶淵明資料匯編(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渠紅巖.唐代文學中的桃花意象[J].南京師大學報,2008,3(2):125
[7]聶石樵.唐代文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