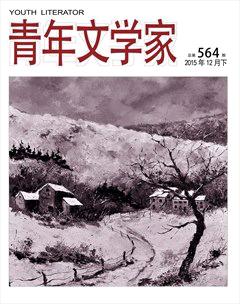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童心”和“自然”構(gòu)筑的精神天國(guó)
羅晶 劉麗彬 徐曉靜
摘 要:在盛極一時(shí)的朦朧詩(shī)隊(duì)伍里,顧城無(wú)疑是一個(gè)特殊的存在。他搭建的詩(shī)歌王國(guó),“童心”和“自然”是最堅(jiān)固的兩塊基石。顧城受外國(guó)詩(shī)歌影響較大,尤其傾心于洛爾迦,在現(xiàn)當(dāng)代詩(shī)歌史上,顧城和洛爾迦無(wú)疑是中外詩(shī)歌一對(duì)光輝的對(duì)稱(chēng)。他們有著極其類(lèi)似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向度,在他們的詩(shī)歌世界中,“童真”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與“童心”相伴隨的,是對(duì)于“自然”的歌詠和對(duì)隱逸的向往。對(duì)“純凈美”的追求,作為一種覺(jué)醒的個(gè)體意識(shí)的標(biāo)記,是顧城詩(shī)歌顯著的美學(xué)特色,表現(xiàn)在詩(shī)歌技巧上,顧城在通感、繪畫(huà)、保持語(yǔ)言的純粹性上,也深受洛爾迦的影響。
關(guān)鍵詞:顧城;洛爾迦;童心;自然;純凈美
作者簡(jiǎn)介:羅晶(1984.7-),女,漢族,籍貫:陜西省漢中市,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陜西廣播電視大學(xué)講師,研究方向: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為本文第一作者。
[中圖分類(lèi)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36-0-01
在朦朧詩(shī)登上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歷史舞臺(tái)時(shí),顧城無(wú)疑是其中特殊的一個(gè),人如其詩(shī),看過(guò)顧城照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雙絕對(duì)純真而清澈的“黑眼睛”, 他以一個(gè)“任性的孩子”的形象走進(jìn)了讀者的心中。顧城詩(shī)歌創(chuàng)作受外國(guó)文學(xué)影響較深,尤其喜歡西班牙詩(shī)人洛爾迦。在現(xiàn)當(dāng)代詩(shī)歌史上,顧城和洛爾迦無(wú)疑是中外詩(shī)歌一對(duì)光輝的對(duì)稱(chēng),在洛爾迦的影響下,顧城找到了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最佳載體和形式,他們同樣傾心于“童心”與“自然”,有著極其類(lèi)似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向度:重視對(duì)以“童心”和“自然”為客體對(duì)象的抒寫(xiě)。[1]
徜徉在洛爾迦的詩(shī)歌中,顧城感覺(jué)到“有一種做人的感覺(jué),做小孩的感覺(jué)”。在顧城的世界里,有的是“欣賞著暴雨的舞蹈”的藍(lán)海洋(《小春天謠曲》),是“干干凈凈的月光”(《草原》),是“麥田邊新鮮的花朵”(《不要在那里踱步》)是“褐菌的部落”,“花香和霧的涌泉”(《水鄉(xiāng)》)……在這個(gè)“天國(guó)”里“我是一個(gè)王子”(《小春天謠曲》)。
在顧城的精神天國(guó)里,與“童心”相伴隨的,是對(duì)于“自然”的歌詠和對(duì)隱逸的向往。在顧城的詩(shī)歌世界里,“城市”和“自然”是天平不相融合的兩端。在“城市”里,人們感受到的只有逼仄的道路,堅(jiān)硬密集的建筑,渾濁的空氣,被物化了的、失去感受力的蒼白的靈魂,城市像一座藏污納垢、無(wú)所不在的理性機(jī)械,控制著人們的言行及所思所想。顧城對(duì)城市衍生的罪惡、愚蠢和現(xiàn)代文明至為厭煩。而這一點(diǎn)洛爾迦感同身受。作為安達(dá)盧西亞的民間詩(shī)人,洛爾迦曾去紐約訪問(wèn)一年,在紐約,貪婪卑鄙的生意經(jīng),對(duì)人為的價(jià)值的崇拜,摩天樓寫(xiě)字間對(duì)人性的摧毀,這一切都使他大受折磨,這是一個(gè)“不眠的都市”,“到處是泥沼、電線和死亡的紐約”。在這個(gè)世界里“戰(zhàn)神和百萬(wàn)只灰鼠哭泣著經(jīng)過(guò)/富翁給與他們的情婦/一具小小的容光照耀的行尸走肉/人生并不高貴,不善也不神圣。”而“牧場(chǎng)”恰恰相反。這里有廣闊的天地、清新的空氣供騎手自由馳騁。顧城的童年在農(nóng)村度過(guò),他在詩(shī)行里不斷重現(xiàn)記憶中的田園牧場(chǎng):在那里“大地像磨盤(pán)一樣轉(zhuǎn)動(dòng)”;在那里他可以“一個(gè)人隨意走向任何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對(duì)太陽(yáng)、風(fēng),面對(duì)著海灣一樣干凈的顏色”。[2]
“童心”和“自然”構(gòu)筑了顧城的精神“天國(guó)”。他決心“要用心中的純銀,鑄一把鑰匙,去開(kāi)啟那天國(guó)的門(mén)”,去表現(xiàn)“純凈的美”。“純凈”,就成為顧城詩(shī)歌顯著的美學(xué)特色。表現(xiàn)在詩(shī)歌技巧上,首先是通感的運(yùn)用。在《愛(ài)我吧,海》里,顧城運(yùn)用了這樣一個(gè)意象:“聲音布滿(mǎn)/冰川的擦痕” [3],聲音本來(lái)僅僅作用于聽(tīng)覺(jué)器官,但是在這里,聲音卻變的可感可觸,像是有形的身軀,被堅(jiān)硬的冰川擦刮出痕跡,無(wú)法消退。顧城化無(wú)形的聲音形象為有形的視覺(jué)形象,消融了聽(tīng)覺(jué)和視覺(jué)之間的感官壁壘。同樣,洛爾迦在自己的《吉卜賽謠曲》中寫(xiě)道:“請(qǐng)你不要讓我憶起那大海,就在那種青橄欖的土地上就在那樹(shù)葉兒的喃喃輕語(yǔ)下萌發(fā)的是那黑色的痛苦。”在這里,痛苦是黑色的,通過(guò)吉卜賽女郎的話(huà)語(yǔ),詩(shī)人描寫(xiě)了那份使女郎難以安睡的莫名的痛苦,讓它映現(xiàn)在海水的波光中和種滿(mǎn)了橄欖的土地上。
此外,顧城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之余,還十分傾心于繪畫(huà),因此,他的詩(shī)句中不斷閃現(xiàn)著繪畫(huà)的技藝。色彩的強(qiáng)弱、光線的明暗、線條的虛實(shí),在顧城的詩(shī)句里自由穿行,變換自如。在我們非常熟悉的《感覺(jué)》一詩(shī)種,顧城寫(xiě)道:“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樓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中/走過(guò)兩個(gè)孩子/一個(gè)鮮紅/一個(gè)淡綠/”,在這里,紅色與綠色本來(lái)是一對(duì)炫目的互補(bǔ)色,再襯以灰色做背景,則更加醒目明亮,短短幾行詩(shī),卻如油畫(huà)一般,給人以極其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沖擊。
而最讓顧城感到契合的地方是,洛爾迦這位西班牙詩(shī)人的聲音里“有一種白金和烏木的氣概,一種混血的熱情,一種絕對(duì)精神”,而正是這種固執(zhí)的聲音震動(dòng)了顧城。顧城在其他場(chǎng)合提到過(guò)這位短命(38歲被佛朗哥殺害)的詩(shī)人:“洛爾迦這些偉大的詩(shī)人都不是現(xiàn)存功利的獲取者,他們?cè)谏钪幸粩⊥康兀麄兊穆曇簦麄冋故旧澜纾瑒t與人類(lèi)共存。”
參考文獻(xiàn):
[1]林平喬,《顧城詩(shī)歌美學(xué)風(fēng)格成因初探》,《理論與創(chuàng)作》,2004年第1期.
[2]唐曉渡,《顧城之死》,《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2005年第6期.
[3]張虹,《淺論顧城詩(shī)歌的藝術(shù)特點(diǎn)》,《青島大學(xué)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