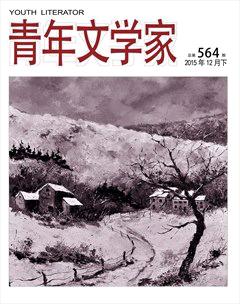由《戰國策》的接受史解讀古代儒學思想的發展
摘 要:自從劉向編訂《戰國策》以來,各代對其理解不同,褒者認為其“繁詞瑰辯,爛言盈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而貶之者則認為其有劇毒,應以儒學為之去毒。按照現代闡釋學的觀點,理解是在時間中發生的歷史性行為。對《戰國策》的理解的差異正見出其背景文化之一——儒學的思想變遷。本文以《戰國策》的接受史為切入點,解讀古代儒學思想的發展變遷。
關鍵詞:《戰國策》;接受史;儒學
作者簡介:劉衛華(1977-),女,湖北京山人,湖北大學知行學院人文系講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6-0-02
戰國時期列國紛爭,各諸侯國為了爭做霸主,紛紛延攬人才以壯其國。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口若懸河的謀臣策士便登上了歷史舞臺,《戰國策》就是一部記載策士言行的著作。其言恢宏譎誑、汪洋恣肆;其事權謀詭詐、聳人聽聞,其人崇計重利、放言無憚。正是這些特點造成了《戰國策》一書引起后人爭議的地方,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古代儒學的思想變遷。
原典儒學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制社會,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他把人與人之間的宗法等級差別規范化、制度化、倫理化,以禮樂制人。
在對“利”的態度上,儒家學者多恥于談利。《論語》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將對利的態度作為了君子與小人的分水嶺。隨后發展儒學的學者也同樣如此,孟子說:“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董仲舒也曾說:“正其誼而不計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他們都認為應該以義制利,而不是見利忘義。戰國策士則思想行為不受禮法拘束,崇計重利。當蘇秦說秦不成歸來時發出的感嘆:“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就公開宣揚了積極追求功名富貴的思想。儒家重行仁義之事,崇尚君子之風。而戰國策士則利用時勢,利用權術,只要能達到目的,用什么手段是不必忌諱的,蘇秦在游說齊閔王時說:“是以圣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權藉”、“時勢”是他們致力之所在,他們雖然也說“圣人”、“仁義”,但他們從不把它看得至高無上,有時反而對之進行批評。
現代解釋學認為“理解是一種在時間中發生的歷史性行為[5]”,不存在超越時間和歷史純客觀的理解,即任何接受史都要受到“先行結構”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出一定時間和歷史中的先入之見,本文就以《戰國策》的接受史為切入點,解讀古代儒學的發展變遷。
《戰國策》最早由劉向校訂成書,云:“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長短之說,左右傾側。”他指出了《戰國策》產生的時代背景,是紛亂的社會中產生的亂世之學。他雖然高度評價了縱橫家皆“高才秀士”,能“扶急持傾……出奇策異志,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但同時也指責這種亂世之學是“權于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是“救急之勢”的權宜之計。
他的觀點是有思想根源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學的獨尊地位,從思想上控制了士人,“征圣”、“宗經”成了儒生所信奉的金科玉律,與此相反的縱橫之學自然也沒有了信奉的市場,趨于衰落。漢武帝對縱橫之學特別反感,他策問嚴助時曾特別指示:“具以《春秋》對,勿以蘇秦縱橫!”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的劉向自然深受影響。
魏晉之際,欲代魏自立的司馬氏打著儒家明教的旗號行不忠不孝之事,激起了士人的憤怒,他們提出“越明教,任自然”,放誕不羈,恣情越禮。在他們眼里,儒學成了一套僵死的模式,正如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描述的“服有例程,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例程。……揚聲明于后世,齊功德于往古。”他們多崇尚老莊之學,品評士人的標準也與儒家截然不同,不再是行止坐臥皆有一套禮法規定的翩翩君子形象,而是任誕放達、狂放不羈。
在《世說新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袁悅有口才,能長短說,……后丁艱,服除還都,唯齊《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病痛事,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袁悅將《戰國策》當成天下要物,對《戰國策》的高度評價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正見出漢魏之際儒學衰微,道家復興的思想現狀。
唐代三教并存,文人一方面把儒學當作立身揚名的途徑,同時又從老莊玄學中吸取營養。儒學一直未能恢復獨尊地位,這種局面直到才有所改變。
《戰國策》的命運到宋代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宋代文人雖欣賞其文汪洋恣肆的語言及氣勢,但對其思想內容一直評價不高。其中突出代表是曾鞏,他在《<戰國策>目錄序》中認為,劉向的論述雖然很好,但對其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大加批駁,認為是“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甚至認為戰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變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弊其患。……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莫之悟也。”他之所以要“訪之士大夫之家,……盡得其書”,只是要“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后以禁”。這是采用了放而絕之的方法。至于其他人也大都作如是觀,宋代李文敘在其《書<戰國策>后》中雖認為“人讀之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文辭極勝”,但同時也寫到“《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葉適在《習學記言》中也評價《戰國策》是“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利益相亂,其為學者心術巨蠹甚矣”。
由上可見宋代文人多贊賞《戰國策》的文辭之勝,且受到其“辮麗恣肆”文風的影響。但他們對《戰國策》的評價仍然不高,無疑是受到當時理學的影響。
宋代繼承韓愈的道統思想,重整儒學,儒學一變而為理學、道學。詩人多將儒家道統由外在的仁義教化內在的心性本體,甚至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觀念,然而禁欲背后的物欲橫流無疑是對趾高氣揚的理學的嘲諷。道德觀念不再是個人主觀的欲求,而成為模式化的東西,儒學在發展中逐漸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力,而孔子則偶像化為令人們誠惶誠恐的“大成至圣先師”,與孔子的原典精神相去日遠,在人性扭曲的時代當然會忌諱無拘無束的生命力,當然也會對《戰國策》采取黨同伐異的態度了。
明清時期,對《戰國策》的理解同宋元沒有太大的區別,一方面仍贊其語言之美,一方面對其思想傾向的批駁更加不遺余力。清代譚獻在《復堂筆記》中評到:“《國策》乃沉而快,《國策》乃雄而雋。”高度稱說其文字之美。而元代吳師道評價《戰國策》是“相詐相輕,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則批駁其思想傾向。更有甚者,清初學者陸隴其選出《戰國策》中的40篇文章,用孟子的觀點一一加以批駁,書名就叫《戰國策去毒》。
至此,對《戰國策》的評說越來越遠離文本的藝術價值,而注目于其思想內容是否合乎正統。這種情況顯然與儒學的發展狀況有關。明清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文人多避實就虛,不敢過問政治,于是儒學發展到明清一變而為明代的實學和清代的考據之學,專注于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在現實中,大多文人不再游離于王權之外,放棄了同王權的抗衡,于是在《紅樓夢》的描述中,原初充滿人情味的孔子成了泥塑木雕似的賈政。
顯然從《戰國策》成書以來漫長的歷史中,其接受史也呈現了很大的差異,由于大多數文人是站在傳統儒學的角度去評說《戰國策》,導致儒學興盛時,文人對《戰國策》多持批駁態度,而儒學衰微時,文人則對《戰國策》多加稱頌,呈現了理解和文本的偏差,而這種偏差正可見出起其背景文化——儒學的發展消長。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
[2]孟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
[4]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1987.
[5]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6]班固.漢書·嚴助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7]劉義慶.世說新語·讒險[M].北京:中華書局,1991.
[8]阮籍.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曾鞏.曾鞏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0]胡如虹.論《戰國策》的語言藝術[J].湘潭大學學報,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