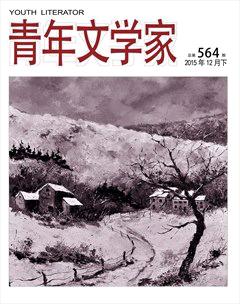孔子對管仲的評價研究綜述及存在的問題
尉春艷 何青霞
摘 要: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一方面否定了管仲的“儉”和“禮”,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管仲的“仁”,可謂有貶有褒,如何解釋孔子對管仲的這種矛盾性評價?學界也多有論及。本文就目前學界對孔子評價管仲的幾種觀點進行綜述總結并指出所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孔子;評價;管仲
作者簡介:尉春艷(1979-),女,河北圍場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文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漢語史;何青霞(1973-),女,河北藁城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文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是現代漢語。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6-0-02
管仲,春秋時著名的軍事家、軍事改革家、出色的政治家,以其超乎尋常的才能輔佐齊桓公使其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雖然和管仲一樣,也生活在動蕩的春秋時期,但是管仲早孔子172年出生。那么,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是如何評說管仲的呢?
在《論語》二十篇中, 論及管仲的共涉及到兩篇,四段史料:
(1)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
這段史料中的“器小;焉得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否定了管仲的“儉”和“禮”,是從儒學的角度,以恢復周禮為根本對管仲的否定性評價。
(2)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憲問》
(3)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
(4)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
這三段史料皆來自《憲問》,“如其仁!如其仁!”等肯定了管仲的“仁”,無疑是頌揚管仲功業的。而在孔子所建構的儒學思想中,對“仁”和“禮”關系最為經典的表述是“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仁、禮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內在關系。“仁”傾向于人內心的道德意識,而“禮”傾向于外在的道德規范,只有內在的“仁”與外在的“禮”相互結合起來才能達到仁的要求,即真正地做到“天下歸仁”。反之,不仁的人是無法克己復禮的(“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既然“仁”和“禮”是統一的,管仲既不知“禮”, 不守“禮”、越“禮”而行,又怎么能是“仁”呢?孔子為什么對于管仲作出“不知禮而仁”這樣自相矛盾的評價呢?
如何解釋孔子對管仲的這種矛盾性評價?以往的研究歸納如下:
近代學者何滿子和顧頡剛的觀點是主要出于古今版本的不同。《論語》現在的版本是東漢時期的鄭玄參照《魯論》、《齊論》和《古文論語》編定的。《憲問》篇都來源于《齊論》,而《齊論》是頌揚管仲的,《八佾》篇來源于《魯論》,而《魯論》主要是談論修身和禮樂之事的,鄭玄既采《魯論》,又采《齊論》,因此在現在的版本《論語》中出現了孔子評價管仲的前后不一致的現象。
商松石(1989)的觀點:孔子論人, 多用兩分法, 指出其優點, 也提出其缺點。他高度評價了管仲, 也提出管仲有器小、奢侈、非禮三個缺點。但是這三個缺點,是“瑕不掩瑜”,或者說是“白璧有瑕”。原因是:這是在肯定管仲功績前提下提出的,“無求備于一人”(《微子》)。且這三個缺點并不多么嚴重。說管仲“器小”,只是嫌管仲器量狹小,為什么有條件做到“優秀”(王),而偏偏滿足于“良好”(霸)?至于管仲位比國君,樹塞門,設反坫,是不應有的,但這是得到桓公同意的,管仲又毫無篡逆之心,只能說是不知禮。孔子指出管仲占人田的非禮行為,卻又從伯氏失地后到死無怨言反襯出管仲的威望。孔子對管仲的“不死”也予以諒解。商指出孔子提出的“鳥能擇木”的論點(見《史記·孔予管家》),所謂“良臣不事二主”,是后世儒家的忠節觀。
于孔寶(1990)、閆春新(2003)認為,孔子是站在兩個不同的角度對管仲進行評價的。其一是從事實的角度,其二是價值判斷的角度。從功利與道義這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評價管仲,一方面符合管仲功勞有余而德行不足的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又能解釋通《論語》中孔子對管仲評價的不一致之處,而且還進一步深化了孔子實事求是堅守道義的圣賢者形象,這樣更貼近真實的歷史和人物。沈素珍(2010)也認為孔子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德”,是一位“仁人”,對于管仲的缺點也給予了直言不諱的批評。同時指出孔子之所以能夠給予管仲全面而非單一的評價,原因在于孔子具備嚴寬并存的獨到政治眼光。馮浩菲(2006)認為孔子是根據“仁學的實踐標準”評價管仲為仁人,這樣的評價既與歷史事實相合,又具有理論依據。
王世巍(2015)從《論語》文本的特點和孔子所作評論的具體語境出發,指出眾所周知的孔子教育的一大原則是“因材施教”,因此在面對子路、子貢提出的關于管仲是否為仁的問題時,孔子的回答也是重在“因材施教”,而對于管仲是否為仁,孔子并無深究。面對子路的管仲“未仁乎”的疑問,孔子針對子路直率、好勇、魯莽的性格特點,重在強調管仲輔佐齊桓公的功勞,“不以兵車”應該是特別針對子路的勸誡和教育,體現在他倡導用非武力的方式會合諸侯。孔子在回答子貢的疑問時,針對子貢謙遜的性格特點,除了強調管仲的功績外,實際上還趁機鼓勵謙遜的子貢,即重點指出不可以因為小的信義而放棄大仁大業。也就是說,孔子其實并沒有直接回答弟子們的疑問,即沒有直接論證管仲是否為仁,孔子對子路、子貢的回答實在是重在教化而并非判斷。因此《論語》前后兩篇中看似相互矛盾的不一致的評價,實質上沒有直接的聯系,表面矛盾的兩處實際上并沒有構成矛盾。
以上是目前學界對孔子評價管仲的幾種觀點。每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著問題。閆春新(2003)質疑了顧、何的不同版本說,首先他據史料推斷出《憲問》應是出自《魯論》而不是《齊論》,而且指出顧、何所持的《齊論》一定會頌揚管仲,《魯論》定是貶斥管仲的這一觀點值得商榷。而以上商、于、閆、沈、馮的觀點就相當于承認了孔子稱一個極度破壞先王禮制的人為建立奇功偉業的仁人。這種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所以很難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而且馮也沒有明確指出所謂的仁學、仁學的實踐標準究竟是指什么?王世巍(2015)因回答的提問對象相異而有不同回答的觀點,可謂另辟蹊徑,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論語》中很多篇章里出現孔子回答弟子問政、問仁的,因弟子性格或身份不同而給出不一樣的回答。
孔子對管仲的批評折射出了他們之間思想上的不同,而對他的褒揚則表明兩人思想的相通之處。但是這個評價不是保持平衡的,會有一個傾向,基于以上觀點所存在的問題,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還有繼續研究探討的空間。
參考文獻:
[1]商松石.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管子學刊1989(4).
[2]沈素珍.孔子評管仲新解[J].管子學刊2010(3).
[3]王世巍.再論如何理解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 管子學刊2015(1).
[4]王世巍.學界對《論語》“如其仁”的誤讀[J].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15(1).
[5]閆春新.從《論語》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再探[J].管子學刊2003(1).
[6]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
[7]于孔寶.論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社會科學輯刊,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