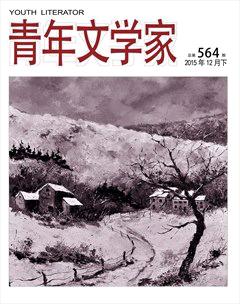一見傾城難再得,還須詩對會家吟
摘 要:以詩傳心,是中國古代愛情特有的一種表達方式。《西廂記》中的詩,是溝通崔張二人心靈的橋梁。詩意的融通,加速了二人沖破禮教藩籬,自由結合,譜寫完美的詩意愛情。
關鍵詞:西廂記;詩;愛情
作者簡介:陳媛(1992.3-),女,漢族,湖北鄂州人,南昌大學碩士研究生,專業研究方向: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6-0-01
蒲關佛殿一相逢,疑是南海水月觀音現。一見傾心,秋波暗轉,是崔、張愛情的“開場白”。兩下里千萬種思量,怎奈“粉墻兒高似青天”?傾城之貌,潛藏深閨,何得再見?唯將詩情,隔墻高吟,以采芳心。于是,以詩傳心,成就了一段終成眷屬的千古佳話。
詩情的流露,詩意的表達,詩心的互證,體現了崔張愛情的發展脈絡。
一、因詩相知
“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欲往京師應考的張生,一睹鶯鶯芳容,便成了瘋魔漢,無心應舉。故在鶯鶯燒香之際,他于太湖石畔踮腳飽看,側耳細聽。那一句“心中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兩拜中”,使張生會意鶯鶯內心之愿。文君之意,相如豈不知?小姐既不便直言,張生便以詩相探:“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傾慕之心,溢于言表,足以撩人心扉。鶯鶯聞此,隨即依韻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其應酬之快,全然在于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春光萬般好,而自己卻只能固步蘭閨,不得一見姹紫嫣紅、蜂嬉蝶鬧的春景。恨春光自好,無奈韶華如逝水,孤影徘徊,豈不是空負年華?芳春無人同賞,芳華無人與共,實是鶯鶯內心深處最悵惘的哀嘆。面對隔墻吟詩的張生,她傾瀉了內心的孤獨與惆悵,毫不猶豫,毫無保留,若非有情,何以至此?縱然高墻相隔,一詩一句,一對一答,已然兩心相知。不是因詩互通情愫,也不會有此后為情愁,為情分,為情合的曲折愛情。
二、因詩相憂
崔張二人情意既通,便只待兩相結合的契機。而賊兵圍困普救寺,無疑給了張生莫大的機遇,一介書生,勇施謀略,化險為夷。他的智和勇,確非一般酸腐儒生可比。因此,鶯鶯相許之心,更加堅定;相思之情,更加深厚。兩人以為婚姻自有成,豈料老婦人一聲:“近前拜了哥哥”,恰似銀河,阻斷牛郎織女!為此,張生瑤琴傳恨意,更賦詩以傳情:“相思恨轉添,謾把瑤琴弄。樂事又逢春,芳心爾亦動。此情不可違,虛譽何須奉。莫負月華明,且憐花影重。”他自知小姐芳心已動,便期與之幽會,以不負良宵。鶯鶯回復:“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應約之意,亦是不言自明。約會之夜,張生頻鬧笑話,屢遭尷尬,但這些都展現了他志誠與情深的一面:為情而癡,為情而傻。而鶯鶯卻礙于閨秀的身份,未肯赴約。至此,明明詩中情意昭然,好事卻難成。一個愛而不得,相思憂之;一個欲進卻退,躊躇憂之。一個憂到深處成病重,一個自是難舍情深,終于決意放下理的牽絆,奉新詩為媒,承諾“今宵端的雨云來”。因詩致憂,也唯詩,可解憂。
三、以詩相憐
鶯鶯因情所致,以身相許,終于成就了一段自由結合的戀愛。然兩人“合歡未已,離愁相繼”,張生不得不為搏得狀元郎的頭銜而赴京應考,他躊躇滿志,誓曰:“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故在長亭送別之際,其心情是榮歸的壯志大于離別的傷感。而鶯鶯呢,面對望不盡的十里長亭,她有著流不完的離人之淚。恨相聚匆匆,別離亦匆匆,原來離別之悲,遠勝于相思之苦。臨別之際,千言萬語,千頭萬緒,化作口中一絕:“棄擲今何在,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以此道盡心中所有的憂慮:張生赴京后,是否會不念舊情,棄其如遺跡?如若情深至此,還遭見棄,那癡心豈不要化成灰燼?鶯鶯之憂深矣。對此,張生亦以一絕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最關親?不遇知音者,誰憐長嘆人?”離別須臾,最情深意重者,當然是眼前之人,如若不是兩心相知,豈愿心心相惜!張生以誠摯的心情視鶯鶯為知音,充滿憐愛之情。遠別之際,以詩互剖心跡,是兩人互相承諾的獨特方式。
四、以詩相盼
分離半年之久,鶯鶯終日獨上妝樓,望斷秋水,終得魚雁一封,內附張生詩曰:“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話浦東窈窕娘。指日拜恩衣晝錦,定須休作倚門妝。”張生如愿以償,折得桂冠,特向鶯鶯報喜:自己即將衣錦榮歸,鶯鶯不必終日倚門翹首、不知歸期了。此詩一則傳達喜訊,一則深知鶯鶯日日相盼,故以詩寬其心。鶯鶯復作一絕:“闌干倚遍盼才郎,莫戀宸京黃四娘。病里得書知中甲,窗前覽鏡試新妝。”欣喜之情,流溢不絕;告誡之心,諄諄醇醇。得知張生高中,鶯鶯最熱切盼望的是他早日歸來,而不要留戀于京都里的女子。殷殷期盼半年之久,茶飯難咽,脂粉懶施,已是人比黃花瘦。而今聽得張生即將歸來,自是增了七分精神,覽鏡試妝,以待歸人。
故人一別,相隔千里;一朝中舉,歸心似箭。鶯鶯與張生,兩情依舊,即使身未重逢,而兩心早已相守。因詩相知,以詩互證,用詩譜寫才與貌、情與義結合的完美愛情,使得《西廂》成為一部詩化的戲劇,詩情流溢,句句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