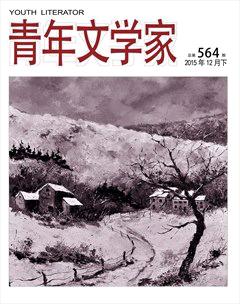哈姆萊特的中國(guó)形象簡(jiǎn)論
張歡
摘 要:本文首先梳理了哈姆萊特在中國(guó)的形象的演變過(guò)程,發(fā)現(xiàn)筆者國(guó)莎學(xué)界受蘇聯(lián)影響,從五六十年代開(kāi)始就將其確定為“人文主義者”的形象,改革開(kāi)放后,不少學(xué)者質(zhì)疑哈姆萊特的“人文主義者”身份,但由于傳統(tǒng)觀念的根深蒂固,兩派的爭(zhēng)論至今存在卻處境尷尬。通過(guò)對(duì)不同觀點(diǎn)的了解,筆者認(rèn)為哈姆萊特富有人文性,卻并不是一個(gè)人文主義者,由此也得到了啟示,筆者做文學(xué)研究時(shí)候要注意跳出教材思維局限,善于借助新工具并且要多關(guān)注學(xué)術(shù)爭(zhēng)鳴,做到兼聽(tīng)則明。
關(guān)鍵詞:哈姆萊特;人民性;人文主義;人文性;非人文主義者
[中圖分類(lèi)號(hào)]:I106.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5)-36-0-02
《哈姆萊特》作為莎士比亞最為成熟的悲劇作品之一,在中國(guó)與全世界都有著廣泛的影響,俗話說(shuō)“一千個(gè)讀者心中就有一千個(gè)哈姆萊特”,可見(jiàn)對(duì)此書(shū)主人公哈姆萊特形象的研究是一個(gè)永恒的話題。然而令筆者奇怪的是,不論在筆者高中還是大學(xué)接觸的有關(guān)的教材中,關(guān)于哈姆萊特形象的研究卻似乎總是千篇一律,“人文主義者”似乎像一塊烙鐵,深深地打在了哈姆萊特的身上,筆者相信,在一千個(gè)中國(guó)人心中,哈姆萊特的形象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一千個(gè)之多,相反卻是十分單一與僵化的。筆者在研究這個(gè)題目時(shí),才發(fā)現(xiàn)其實(shí)在中國(guó)學(xué)界,對(duì)哈姆萊特的形象研究的分歧與爭(zhēng)論是極大的,也是在逐步發(fā)展與深入的,因此,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試圖做的就是:根據(jù)筆者所搜集到的資料,梳理出一條哈姆萊特中國(guó)形象的變化線索,并且根據(jù)前輩們的成果,談一談自己的理解與得到的啟示。
一、哈姆萊特中國(guó)形象的變化
(一)長(zhǎng)期以來(lái)在中國(guó)具有“人民性”和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哈姆萊特
在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伴隨著蘇聯(lián)在各方面對(duì)中國(guó)的巨大影響,中國(guó)莎學(xué)界毫無(wú)意外的全面受到蘇聯(lián)莎學(xué)研究的指導(dǎo)與影響,尤其是阿尼克斯特的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莎學(xué)理論。在這個(gè)階段,卞之琳的莎士比亞研究取得了開(kāi)創(chuàng)性成果,但他的研究依然建立在全面接受蘇聯(lián)莎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上,其將蘇聯(lián)理論直接應(yīng)用于自己的研究過(guò)程,雖然在廣度與深度等方面對(duì)阿尼克斯特有一定的超越,但與此同時(shí)也強(qiáng)化了階級(jí)斗爭(zhēng)的觀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了哈姆萊特作為人文主義戰(zhàn)士的身份特征。
(二)新時(shí)期對(duì)哈姆萊特“人文主義思想家”身份的質(zhì)疑
1978年以后,對(duì)莎士比亞的研究開(kāi)始自由起來(lái),從80年代開(kāi)始,就陸續(xù)有學(xué)者對(duì)這種傳統(tǒng)觀點(diǎn)發(fā)出質(zhì)疑,1986年,高萬(wàn)隆發(fā)表《哈姆萊特是人文主義思想家嗎》一文,旗幟鮮明地對(duì)題目所提問(wèn)題給予了否定回答。整篇文章從哈姆萊特的封建意識(shí)、哈姆萊特的愛(ài)情、哈姆萊特的人生觀、“重整乾坤”問(wèn)題、哈姆萊特的悲劇性偏激及其自筆者否定性格等方面入手,對(duì)文本進(jìn)行了重新的發(fā)掘與分析,推翻了之前的許多傳統(tǒng)結(jié)論,并提出:“那種先從‘哈姆萊特是人文主義思想家這一既定概念出發(fā),而后從劇本中找根據(jù)的批評(píng),只能圖解、割裂甚至歪曲原作中的藝術(shù)形象。”
從叢在1989年于《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上發(fā)表《論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一文,在駁倒傳統(tǒng)觀點(diǎn)的同時(shí),也得出了一些新的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對(duì)于哈姆萊特延宕復(fù)仇行動(dòng)之原因的問(wèn)題給出了一種全新的回答:哈姆萊特作為一個(gè)封建王子,其天然形成的宗教宗法觀念與殘酷現(xiàn)實(shí)間的兩難沖突,是造成他屢屢延宕行為的主要原因;而次要原因則是其野心與其受挫失意心理的矛盾沖突,這種結(jié)論實(shí)際上借鑒了弗洛伊德采用的用“俄底浦斯情結(jié)”來(lái)分析解釋哈姆萊特行為的研究思路,但與此同時(shí)又可以在文本中找到充分的論據(jù)。筆者說(shuō)哈姆萊特不是人文主義者,“并不意味著否定莎士比亞是一個(gè)人文主義者的典型代表,也不意味著否定《哈姆萊特》一劇具有明顯的人文主義傾向。”
(三)是還不是,至今令人尷尬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辯
令人奇怪的是,雖然不少文章的發(fā)表已充分顯示出一些評(píng)論家們對(duì)傳統(tǒng)觀點(diǎn)的強(qiáng)勢(shì)挑戰(zhàn),但它們似乎均未能引起學(xué)界廣泛重視與研討。在中國(guó)知網(wǎng)上搜索該問(wèn)題會(huì)發(fā)現(xiàn),就算到了現(xiàn)在,那些論證與說(shuō)明哈姆萊特的人文主義特性的文章仍然層出不窮,雙方大有一種“你說(shuō)你的,筆者說(shuō)筆者的”的態(tài)勢(shì)。兩派之間呈現(xiàn)的是一種觀點(diǎn)勢(shì)成水火卻又缺乏論爭(zhēng)與火花的尷尬狀態(tài)。
究其原因,可能是這種情況,受到長(zhǎng)期慣性思維的影響,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莎學(xué)對(duì)其的巨大影響至今仍然存在,改革開(kāi)放之初,有一些老一輩研究者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將哈姆萊特簡(jiǎn)單定位于人文主義者的不足之處,但他們已沒(méi)有能力或者精力再來(lái)糾正清理這種偏頗,從而致使這種觀點(diǎn)影響了20多年并且至今在莎學(xué)研究、哈姆萊特研究中還大有市場(chǎng)。因此盡管挑戰(zhàn)傳統(tǒng)觀點(diǎn)的文章仍有少量出現(xiàn),但90年代以來(lái)出版的有關(guān)高校教材、研究專(zhuān)著和重要工具書(shū),幾乎仍是傳統(tǒng)觀點(diǎn)的一統(tǒng)天下的現(xiàn)狀并沒(méi)有改變。
二、筆者看哈姆萊特:具有人文性的非人文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lái),對(duì)于哈姆萊特是不是人文主義者的判斷,不能簡(jiǎn)單地用“是”或者“不是”來(lái)判斷,在這種問(wèn)題上,筆者要摒棄中國(guó)傳統(tǒng)的“非忠即奸”“非好即壞”的思想的影響,因?yàn)檫@是一種道德的懶惰,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并不可取。在筆者看來(lái),哈姆萊特應(yīng)該是一位具有人文性的非人文主義者。
首先,哈姆萊特是富于人文性的,關(guān)于“人文主義”的解釋?zhuān)钯x寧《歐洲文學(xué)史》有:“人文主義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張一切以人為本,以此 來(lái)反對(duì)羅馬教會(huì)所代表的神權(quán)的絕對(duì)統(tǒng)治……人文主義反對(duì)禁欲主義和來(lái)世思想,肯定現(xiàn)世生活,歌頌愛(ài)情和個(gè)性解放……認(rèn)為人是有理性的動(dòng)物,應(yīng)該有權(quán)追求知識(shí),探索自然,研究科學(xué)……鼓吹仁慈、博愛(ài),歌頌友誼和個(gè)人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險(xiǎn)精神”,筆者以此來(lái)分析文本中哈姆萊特的人文性。“筆者把筆者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針,至于筆者的靈魂,那是跟它自己同樣永生不滅的”。哈姆萊特并非不從人的角度出發(fā),相反,正是對(duì)其父尊重,見(jiàn)到其亡魂時(shí)才會(huì)有:“是的,筆者可憐的亡魂,當(dāng)記憶不曾從筆者這混亂的頭腦里消失的時(shí)候,筆者全記著你的。記著你!是的,筆者要從筆者的記憶的碑板上,拭去一切瑣碎愚蠢的記錄,一切書(shū)本上的格言,一切 陳言套語(yǔ)”。哈姆萊特對(duì)亡魂充滿了尊敬與憐憫,以及他著名的對(duì)“人”的歌頌,足以看出他已有人文主義意識(shí)的存在。
“廣義人文主義”的基本要素是對(duì)人的尊嚴(yán)和價(jià)值的普適性肯定,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我們從哈姆萊特對(duì)于人的贊美、審慎的思維、顧慮以及對(duì)于智慧與真相的追求上都可以看出其身上濃郁的人文色彩。同時(shí),我們還可以從哈姆萊特與奧菲莉亞的愛(ài)情中發(fā)掘其人文性,在劇本第二幕第一場(chǎng)奧菲利亞與波洛涅斯的對(duì)白中不難看出哈姆萊特對(duì)其的愛(ài)戀,如果丹麥王子不是一個(gè)人文主義者,那么其在貴族法則的束縛下不會(huì)那般瘋狂地去見(jiàn)他的戀人,甚至產(chǎn)生失雅的行為。
但另一方面,筆者又看到哈姆萊特并不是一個(gè)人文主義者,道理很簡(jiǎn)單,哈姆萊特是十二世紀(jì)的丹麥王子,而歐洲近代的人文主義思潮最早產(chǎn)生也要到十四世紀(jì)下半葉,前后相差兩個(gè)世界那么多,在這種情況下,他怎么可能是一個(gè)典型的人文主義者呢?就好比筆者看到十七、十八世紀(jì)的作品中出現(xiàn)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也不會(huì)相信一樣,如果莎士比亞將他如此塑造,是有違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時(shí)間法則的。
其實(shí),如果筆者不要把莎士比亞與哈姆萊特等同起來(lái),很多問(wèn)題就迎刃而解了,筆者可以將莎士比亞看成一個(gè)典型的人文主義者,可以認(rèn)為“莎士比亞把時(shí)代精神通過(guò)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細(xì)胞輸送給古老的故事傳說(shuō),將16世紀(jì)后半葉人文主義者的靈魂轉(zhuǎn)寄到哈姆萊特的身體中使之成為時(shí)代之子。”但并不能就把莎士比亞的身份等同于哈姆萊特,他具有莎翁的“人文性”,但并不是一個(gè)人文主義者。
參考文獻(xiàn):
[1]卞之琳,莎士比亞悲劇論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版。
[2]高萬(wàn)隆,哈姆萊特是人文主義思想家嗎?山東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6年第4期。
[3]從叢,論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