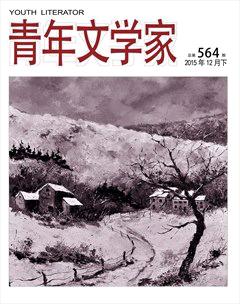托妮?莫里森的姐妹情誼觀
王東升 王麗捷
摘 要:姐妹情誼是美國黑人女性文學的瑰寶。莫里森的多部作品涉及到這一主題,其中《秀拉》、《天堂》和《愛》聚焦于姐妹情誼。通過分析這三部作品中的姐妹情誼,可以了解莫里森對姐妹情誼的理解、態度及其思想演變的過程。
關鍵詞:莫里森;姐妹情誼;秀拉;天堂;愛
作者簡介:王東升(1978-),男,漢,吉林農安人,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吉林醫藥學院講師,主要研究英語語言文學;王麗捷(1978-),女,漢,吉林九臺人,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吉林醫藥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6-0-02
作為美國黑人文學的領軍人物,托妮·莫里森筆耕不輟,至今已發表了10部小說,并于199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姐妹情誼一直是莫里森關注的焦點,她的小說《最藍的眼睛》、《柏油娃娃》、《爵士樂》、《寵兒》都涉及到這一主題,《秀拉》、《天堂》和《愛》更是聚焦于姐妹情誼。莫里森如此鐘情于這一主題是由于姐妹情誼對美國黑人女性的生存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姐妹情誼
姐妹情誼最早由白人女權主義者提出。在第二波女權運動中凱西·薩拉查爾德提出了“姐妹情誼就是力量”的口號,號召全世界女性團結起來,掙脫父權制的桎梏。然而,由于這種提法未能反映不同階級、不同種族的女性的不同需求,因此未能產生應有的影響。隨著美國黑人文學的興起和黑人女作家對姐妹情誼的大力倡導,“姐妹情誼”重新煥發出絢麗的光彩。由于黑人女性遭受著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壓迫,因此“僅僅為了生存就要求黑人婦女緊緊團結在一起”[1]。威姆斯指出姐妹情誼是“女性之間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他們分享各自的情感、焦慮、愿望和夢想”[2]。有了姐妹情誼的堅強后盾,黑人女性群體得以發展,黑人女性的力量得以展現。
二、莫里森小說中的姐妹情誼
姐妹情誼的重要作用使其成為黑人女作家創作的母題之一。莫里森沿用了這一主題,并使其發揚光大。《最藍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和克勞迪婭、《柏油娃娃》中的瑪格麗特和昂迪、《爵士樂》中的維奧萊特、菲利斯和艾麗斯、《寵兒》中的塞斯和艾米都從姐妹情誼中獲得了力量、溫暖和支持,使她們在艱辛的人生路上不至于踽踽獨行。《秀拉》、《天堂》和《愛》的發表時間跨度約40年,姐妹情誼貫穿這三部小說的始終,這體現了莫里森對姐妹情誼深入和持久的關注和思考。
《秀拉》中的秀拉和內爾來自兩個迥異的黑人家庭。她們個性互補,秀拉勇敢、魯莽;內爾果斷、有主見。她們共同面對白人男孩的欺辱、共同經歷“意外死亡”事件,并建立起真摯的友誼。內爾婚后留在家鄉相夫教子,秀拉則遠走他鄉探索人生。十年的分離,并沒有影響兩個人的友情,她們依然親密無間。此時的秀拉桀驁不馴,我行我素,與不同的男人發生關系,并將他們拋棄。內爾發現自己的丈夫裘德和秀拉發生關系后,認為秀拉背叛了她,因此斷絕了和秀拉的友情。三年后,內爾探望病中的秀拉,兩人開誠布公地交談。秀拉死后,內爾才意識到自己失去了最珍貴的友誼。秀拉和內爾的友誼使她們共同成長,秀拉的去世也使內爾省察自己的人生,并開始新的成長之旅。秀拉和內爾就像一個完整人格的兩個不同部分,姐妹情誼使這個人格趨于完善。然而父權制打破了人格的完整,使人的內在自我和外顯行為間發生斷裂。循規蹈矩的內爾和桀驁不馴的秀拉是這種斷裂的極端表現。她們之間情誼的破裂也象征著父權制使黑人女性的人格經受著分裂般的痛苦。
《天堂》講述了三代黑人幾經輾轉建立魯比鎮的過程,同時講述了距小鎮十七英里之外的女修道院中五個落魄女子的經歷。修道院里聚集的女人們年齡、身份、種族、階級各不相同,但都被生活打擊得遍體鱗傷。一直住在女修道院里的康瑟蕾塔很小就被遺棄并被強暴,后被修女帶到美國。她與魯比鎮的迪克相愛卻被拋棄。修女死后,康瑟蕾塔失去了精神支柱,更加萎靡不振。瑪維斯在家中毫無地位,被丈夫成為“地球上最蠢的女人”,她由于疏忽而將兩個雙胞胎兒子悶死在車中,因此自責不已,進而產生了幻聽和被害妄想。格蕾絲(吉姬)親眼看到警察槍殺無辜的黑人男孩,內心充滿恐懼。西尼卡被少女母親拋棄,被收養她的家人的孩子強暴,因此自殘、自傷。帕拉斯家境很好,然而3歲時她的父母就離異了,她全心愛著的男友和她的母親發生了性關系,這讓她受到很大刺激,在出走的過程中,她被人強暴并懷孕。康瑟蕾塔接納了先后來到女修道院的這四個女人,給她們時間和空間去療愈內心的傷痛,并通過儀式讓女人們互相傾訴來卸下內心的重負。魯比鎮的男人們認為是修道院里的女人們破壞了魯比鎮的團結,因而圍攻了女修道院。面對男人們的暴力,修道院里的女人們并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進行反擊。在反抗暴力的過程中,女人們樹立起自信心,這也使她們在回歸生活后,宛如新生般地自信、果敢、堅定。在這部小說中,莫里森并沒有刻意指出這五個女子的種族。莫里森隱瞞這個白人女子的身份是想讓讀者知道“角色的內心、過往、過錯和力量比種族這一信息重要得多”[3]。這五個內心支離破碎的女子走到一起,姐妹情誼像一個粘合劑使她們每一個人都變得完整,失落的一角變成大圓滿。
在《愛》中莫里森重回姐妹情誼這一主題。克西斯廷是上層黑人柯西的孫女,留心是窮黑人家的女兒。克里斯廷不顧母親的反對和留心交往并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柯西一意孤行娶了留心,這一決定深深地傷害了克里斯廷,她結束了和留心的友誼,離家出走。多年后,走投無路的克里斯廷回到家中,和留心生活在一起,卻彼此怨恨。直到留心死前,兩人才敞開心扉,談起過往,最終實現了和解。克里斯汀和留心之間的友情給她們各自的生活染上了蜜糖色,然而她們之間的姐妹情誼也如蜜糖般易碎,男性的介入和身份地位的變化,使她們之間的情誼瞬間瓦解,并造成了她們一生的不幸。
三、莫里森的姐妹情誼觀
在四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莫里森一再觸及姐妹情誼這一主題,這既是在延續美國黑人女性文學的創作傳統,也是由于姐妹情誼對黑人女性生存與成長起到重要作用。在莫里森筆下,姐妹情誼幫助黑人女性在艱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同時幫助她們成長,逐漸達到人格的完善。然而父權制社會的整體架構使姐妹情誼受到威脅,階級和種族的差異也橫亙在女性之間,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此,莫里森主張用交流消除隔閡,用無條件的接納來融化各人心頭的堅冰。秀拉與內爾最終互相理解,克里斯廷與留心實現了和解,這都是她們敞開心扉進行交流的結果,然而這最終的和解都來得太晚了,她們付出了一生幸福做代價。康瑟蕾塔無條件地接納來到她身邊的女人,為她們療傷,同時也治愈了自己。在療傷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也是傾訴。當人們說出生活的真相時,她們內心的傷痛便會得到治愈。在《天堂》的結尾,莫里森沒有寫這五個女人從此在女修道院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而是寫了康瑟蕾塔的死和其他女人的新生,這說明莫里森并不主張女性脫離男性社會,建立自己的樂園,而是主張內心豐盈的女人們回歸自己的生活,直面真實的人生。
四、小結
早在非洲歷史的早期,一夫多妻制使女人們共同生活、勞作、撫養彼此的孩子,在這一過程中她們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黑人被販賣到美洲大陸后,由于青壯年男子都被買賣,因此留下來的女性們只能相互扶持,維持生計。這使女人間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美國內戰后,黑人奴隸獲得了解放,但他們仍然受到種族歧視和經濟剝削。黑人男性可以將這些壓力轉嫁給黑人女性,黑人女性卻要擔負起其他人拒絕承擔的重負。在這樣的重壓下,黑人女性必須團結一致才能夠生存和發展。正因如此,美國黑人女作家們紛紛探討姐妹情誼。作為其中的佼佼者,莫里森更是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莫里森通過她的作品傳遞出姐妹情誼對黑人女性的重要意義,同時主張用對話和接納推翻壓在黑人女性身上的種族、階級和性別三座大山,實現黑人女性,乃至整個黑人民族的復興。
參考文獻:
[1]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Clenora H. Weems. African Womanism: Reclaiming Ourselves [M].Michigan: Bedford Publishers, Inc.
[3]Timehost,“Toni Morrison”Transcript form Jan.21,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