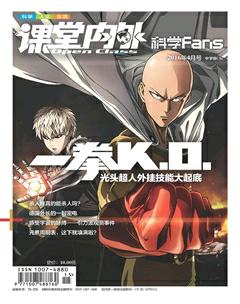興奮劑始末
毛穎
在北歐傳說中,神勇戰士巴薩卡斯(Berserkers)在戰斗前要服用一種名為“不頭疼”(Butotens)的飲料,它可以大幅提高其戰斗力。后經考證,這個“不頭疼”很可能就含有令人興奮的毒蘑菇成分。
據記載,在公元前3世紀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曾有運動員試圖服用從毒蘑菇中提取的致幻劑來提高運動成績的報告。從那時候起,運動員就嘗試飲用各種白蘭地或葡萄酒混合飲料,或者食用蘑菇,以便獲得附加的“力量”來戰勝對手。
最早登上現代體育舞臺的興奮劑是鴉片,而英國傳統的耐力賽跑則是現代體育使用興奮劑的源頭。1807年,參賽者亞伯拉罕·伍德(Abraham Wood)聲稱自己使用了鴉片酊才保持了24小時的清醒狀態,打敗了其他選手。那時候人們并不覺得服用藥物參賽是不光彩的事,因此這一經驗迅速得到推廣,并創造了一系列“冠軍”紀錄。
很快,這一做法推廣到了自行車運動中。在美國,著名的六天自行車耐力賽的參賽選手大規模使用可卡因成為公開的秘密。1899年,世界一英里場地自行車賽冠軍馬紹爾·泰勒(Marshall Walter Taylor)在一次參加比賽的過程中突然退出比賽,他聲稱有一個持刀歹徒一直在追他——他因為服藥產生了幻覺。
1896年,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啟程,吸引了大批運動員的參與,同時也促使了興奮劑在運動中的進一步使用。1904年的第三屆奧運會,馬拉松比賽冠軍是美籍英國人托馬斯·希克斯(Thomas J. Hicks),在比賽過程中,他的教練一直拿著注射器跟隨著他,為其注射●士的寧(Strychnine)。但此后,希克斯卻再也沒有參加過正式比賽。
1924年,記者在對一位環法自行車賽選手進行采訪時,這位選手指著他的裝備炫耀道:這是可卡因,對眼睛有好處。這是氯仿,對我們的牙有好處。這個,是搽劑,能讓我們的膝蓋回暖。你想看藥片么?說實話,我們是靠著炸藥騎車的(意指硝酸甘油)。
1934年,麻黃素的類似物——安非他命(苯異丙胺)被商業合成,商品名為●苯齊巨林(Benzedrine)。雖然這種藥物的研究由軍方主導,但在它面世后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就已經隨處可見它的身影了,它得到了一個新名字叫“速度”。
1954年,越南舉辦了一場舉重比賽,一位前蘇聯生理學家在醉酒后向美國運動醫學專家約翰·齊格勒透露,他們給運動員使用了睪酮。回國后,這位醫學專家開始給自己和兩名舉重運動員服用小劑量的睪酮,隨后他們的肌肉都變發達了,力量也變大了。為了降低副作用,齊格勒又使用合成類固醇美雄酮來代替睪酮[就是名字響當當的“大力補”(Dianabol)]。
在這期間,雖然興奮劑得到大力發展,但它的副作用卻始終存在,只是人們暫時還沒有認識到其巨大的危害性。1960年,羅馬奧運會,丹麥自行車選手簡森(Knud Enemark Jensen)突然在比賽中昏厥,隨后死于醫院。尸檢證明,他服用了安非他命、酒精和另一種擴張血管的藥物。
1967年,前奧運銅牌選手,英國自行車運動員辛普森(Tommy Simpson)死于環法比賽途中,死時衣袋中還有未吃完的安非他命。此后,曾經風光一時的神藥們顯露出越來越大的危害。
1968年,國際奧委會終于開始在第十九屆夏季奧運會中開展興奮劑檢測。真正讓人們認識到興奮劑的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男子飛人大戰中加拿大人本·約翰遜(Ben Johnson)一舉擊敗卡爾·劉易斯(Carl Lewis),并大幅提高了世界紀錄。不過,他的金牌僅僅在脖子上掛了數小時,隨后被宣布查出禁藥司坦唑醇。
20世紀90年代,促紅細胞生成素EPO(Erythropoietin)被列入禁藥名單。作為一種新型違禁藥物,EPO最早被作為一種治療貧血等血液疾病的藥物,由于能促進紅細胞生成,提高身體的耐力,它被很多耐力項目選手用作興奮劑。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之前,人們都無法檢測這種興奮劑。即便如此,興奮劑藥物給人類帶來的嚴重后果卻是不可忽視的,這場榮耀與利益給人類帶來的誘惑戰終究會想辦法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