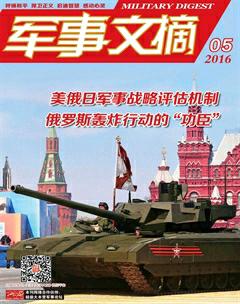解析日本防衛力量戰略評估機制
易本勝+張人龍


二戰期間,日軍雖有戰時大本營、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等戰略管理機構,但因缺乏有效的戰略評估機制,使得戰略目標在野心的驅使下失之過度,加之戰略實施上失之粗放,缺乏具體可行的規劃措施,造成軍事戰略凌駕國策之上,陸海軍種戰略對立、作戰戰略裹脅指導戰爭的混亂局面,進而使國民經濟負擔沉重卻無法收獲相應效益,并在其他因素的疊加作用下,最終導致慘敗結局。戰后,日本針對這一層次或角度的教訓進行了反思,在確立政治統軍原則、剝奪防衛力量(防衛當局和自衛隊)干政權力的前提下不斷探索,并借鑒美軍經驗,逐步建立起具有日本特色的戰略評估機制。
發展過程
起步階段 冷戰前期,由于在國內反軍輿論的特殊背景下諱言軍事問題,軍事上以“少說多做”甚至“只做不說”的姿態埋頭軍備重建,其戰略評估機制僅在頂層具有雛形,集中表現為首相私人智囊團以及內閣的國防會議(1986年改組為安全保障會議)。前者以吉田茂的政經問題智囊群和軍事問題智囊群為代表,為“吉田路線”這一國家復興戰略的出臺做出了重要貢獻,并成為日后“有識者懇談會”機制的先河;后者主持出臺1957年版《國防基本方針》,僅有4項、10余行內容,但統領4期《防衛力量發展計劃》,使軍備數量迅速擴充。相比之下,以1963年“三矢研究”為代表,防衛力量自身的戰略評估受到較大制約,發育較為緩慢。
發展階段 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著防衛力量重建的基本完成以及在日美軍事同盟中的職能擴大,日本防衛當局開始思考軍備建設效率與實際運用問題。在頂層,轉為以1976年版《防衛計劃大綱》(按年份簡稱“XX大綱”)統領《中期防衛力量發展計劃》(簡稱“中防”,包括前身《中期業務預估》)的體制,確保軍備質量持續升級;在下層,防衛廳、參聯會及各自衛隊參謀部等,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繼出臺一系列法規,其戰略評估在此時取得較大發展。
升級階段 冷戰結束后,日本防衛當局正式進入運用軍力謀求國家利益的新時期,對戰略評估提出了更高要求。從“95大綱”開始,確立起以首相私人咨詢機構(各類懇談會)為先導、以政府職能部門(內閣安全保障會議)為主體的頂層評估機制;至“04大綱”時,所涉內容從軍備計劃擴展到國家安全戰略層面,被賦予更高的戰略定位。與此同時,防衛廳相關職能部門在大綱擬制過程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其戰略評估機制有所加強。
定型階段 在“10大綱”和“13大綱”出臺前后的最近幾年中,一方面日本形成了明確的戰略評估體系。2013年,日本內閣安全保障會議改組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負責總攬以外交政策與軍事政策為主體的國家安全戰略管理,發布《國家安全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回歸單純軍事計劃的本來面貌。至此,初步形成了由“10年國家安全戰略—10年防衛計劃大綱—5年中期防衛力量發展計劃—年度計劃”的計劃體系,據此實施系統化戰略管理與戰略評估。另一方面,進一步強化了防衛力量自身的評估機制。2007年,通過“廳改省”實現了防務部門的升格和擴權;2009年,為防衛省設置防衛會議,其下隨即開設防衛力量愿景檢討委員會,形成了與首相私人懇談會并行的頂層評估機制;及至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改組,首相懇談會升格為針對國家安全戰略建言,日本防衛當局則相應成為事實上包攬各項軍事政策評估的實施主體。
現實狀態
日本防衛力量戰略評估機制已在國家整體以及軍事的長期、中期、年度等四個層面之上,按照形勢評估、政策擬制與實施、政策評估三個系列,形成“四橫三縱”的基本格局。
國家總體層面,由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負責擬制《國家安全戰略》,由內閣情報會議以《情報評估書》等形式為其提供形勢評估等支持,由首相組織的所謂“有識者懇談會”等為其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評估等支持。
長期軍事規劃層面,由各自衛隊參謀部以未來10~20年《長期防衛預估》、情報本部以未來5~20年《聯合長期情報預估》等,為聯合參謀部提供參考;由聯合參謀部以未來5~20年《聯合長期防衛戰略》,為《防衛計劃大綱》提供參考;由防衛力量檢討委員會、防衛大臣官房企劃評估課以及防衛省各項政策分管課等部門,為大綱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評估等支持。
中期軍事規劃層面,由各自衛隊參謀部未來3~8年《中期防衛預估》、情報本部未來3~8年《聯合中期情報預估》等,為聯合參謀部提供參考;由聯合參謀部未來3~8年《聯合中期防衛構想》和《聯合中期能力預估》,以及各自衛隊參謀部未來3~8年《中期能力預估》等,共同為“中防”提供參考;由防衛省各項政策分管課,為“中防”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評估等支持。
年度軍事計劃層面,由聯合參謀部與各自衛隊參謀部,依據“中防”分別出臺《聯合年度業務計劃》和《各自衛隊年度業務計劃》;由防衛省各項政策分管課,為年度計劃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評估等支持。
除上述全局性、綜合性的戰略評估外,自衛隊在各專業領域,多以常設審議會或臨時委員會的形式,履行戰略評估、規劃等咨詢職能,分為政策研究、事態應對、事業推進、業務協調和調查審議五類。不僅如此,部分內外機構也擁有戰略咨詢功能,甚至設有相應職能部門,承擔自行課題或委托課題的相關研究、評估工作。內部機構主要以科研院所為主,如防衛研究所、技術研究本部、防衛大學、各自衛隊軍官學校等,防衛研究所即設有防衛戰略研究會議;外部機構則以安保領域各類研究所為主,如森野軍事研究所、防衛基礎建設協會等。
突出特點
框架要素比較完善。日本防衛力量的現行戰略評估機制雖成型不久,但框架要素齊備。一是形成了以政府和防衛當局高層為主導、以專職職能部門為骨干、吸納內外智力為補充的戰略評估組織體系,層次較為分明,職責相對明晰;二是評估內容涵蓋全局課題與局部課題、長遠課題與短期課題、政策課題與技術課題,項目較為全面;三是評估周期貼合各級戰略實施周期,時機相對固定;四是評估體制總體上呈現“樹立國家理念,論證國家利益,設定國家安全保障目標,提出安全保障課題,擬定對策措施”的基本路徑,程序相對合理。
基本保障比較完善。為確保戰略評估制度化、規范化和標準化,日本防衛當局主要從兩個方面加強保障。一是制定各種法規,以對戰略評估的組織、實施等做出明確規定。如《關于情報業務實施的訓令》(2006年)和《關于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法律》(2013年)等。二是在各層級設立相應的專職機構,負責為戰略評估和規劃工作提供情報支援。為確保提供客觀、準確的情報支援,日本防衛力量堅持“情報與政策分離”的觀念,強調情況部門依據政策部門的情報關注進行情報搜集、整理、集約、分析和成果反饋,政策部門依據情報制定和實施政策,提出新的情報關注,形成良性循環。如2008年出臺的《官邸情報功能強化方針》規定,為進行適時正確的政策判斷,需要由獨立于政策部門之外的其他部門,以客觀視角對所獲情報加以評估、分析,官邸政策部門與情報部門在分工上應相互獨立。
反饋調控比較完善。日本防衛當局強調,戰略評估乃至整個戰略管理工作均須密切跟蹤客觀形勢,依據形勢變化做出適時、妥當調整。從頂層看,屬于長遠規劃的《國家安全戰略》和《防衛計劃大綱》均在文末規定,實施過程中定期進行體系化評估,根據形勢變化適時加以修訂。從下層看,屬于短期計劃的各自衛隊《年度業務計劃》也規定,由各自衛隊監理部門首長和具體計劃主管、責任人等,以年度計劃中對力量建設和維持有重大影響的主要業務事項、預計目標達成困難的事項、實績顯著偏離目標的事項和業務整體共通問題事項等,隨時進行分析檢討;如有必要,計劃實施過程中可隨時調整,以更有效地促進目標達成;分析檢討的結果應區分為“業績”與“問題事項分析檢討”兩個部分,及時逐級上報。
信息發布比較完善。由于戰后日本國內反戰、反軍思潮高漲這一歷史背景,防衛力量自重建以來在軍事政策評估方面始終重視對民眾發布信息。進入新世紀,除傳統的宣傳窗口外,還強調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手段,加強政策評估結果及其對政策反饋情況等的信息發布。在頂層,各種懇談會、委員會除發表中期報告、最終報告外,還及時公布歷次會議研討紀要、參考資料等;在下層,防衛省企劃評估課對于歷年主要事業、業務的各類評估情況,均在互聯網上及時公布。其目的:一是制造力量體制公開透明的印象;二是為防衛政策贏得合法性地位;三是引導輿論走向;四是在形式上為政府決策與國民共識之間保留一個互動渠道。
存在問題
自主空間十分有限。日本在防衛戰略上對美附庸,這對其戰略評估成效形成了根本制約。戰后,日本作為戰敗國早已淪為美國軍事殖民地,雖然通過日美同盟貌似實現了和平與發展,但事實上是以犧牲民族獨立、國政自主和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也是日本被視為“非正常國家”的真正根源。正因如此,日本防衛戰略決策從根本上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決策空間,必須也只能服從和服務于美方戰略利益,其戰略評估不可能為戰略規劃提供真正有效的依據,突出表現為日本拱手將自己有限的軍事資源獻給美軍享用,形成軍備成果“所有權歸日方、使用權歸美方”的局面。如駐日美軍享受“東道國支援預算”(關懷預算),比例高達75%,在所有東道國中位列第一,較美國本土駐軍還省錢。

懇談會是日本戰略評估的重要一環
頂層規制十分有限。體制機制不健全,事實上造成日本防衛當局頂層戰略評估空洞化。二戰前,日軍戰略管理體制的封建專制色彩濃厚,決策不外乎出自天皇、首相等高層核心政治家的所謂“圣裁”“英斷”,因決策圈子過小而很容易缺乏專業性、科學性,不可能實施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評估。二戰后,日本防衛當局吸取教訓,逐步形成了借重首相私人咨詢機構(各類專家懇談會)實現戰略評估和規劃的機制,收到一定實效,較之戰前有所進步。然而,此類懇談會機制本身的不足,正在日益削弱戰略評估的作用。首先,懇談會并無法律依據,既非政府機構,也非執政黨派,只是首相私人咨詢機構,存在“不合法”的硬傷;其次,懇談會機制雖然有利于在較短時間內高效而廣泛地匯集專家及各方意見,但未必能確保形成科學的最終結論,特別是受通常不足1年的會期限制,其研討往往欠缺深度、精度和長遠性;再次,隨著近年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根據政治領導人個人意愿組成的懇談會日益淪為已有“預設結論”的政策工具,戰略評估和規劃機制在總體上有從“科學決策”模式向二戰前那種先拍板、后論證的“決策科學”模式回歸的跡象。
運作能力十分有限。由于戰略評估機制形成較晚,因而持續實施可靠戰略評估的能力十分有限。一是評估力量尚不充分。因為負責整體調整的政治領導力偏弱,造成戰略評估和規劃的總體功能存在缺陷,在跨領域政策事項中尤其如此。雖有各類審議會、委員會之類的機制,但由防衛省內主管綜合政策或分管具體政策的課履行其“事務局”職能,事實上承擔評估和規劃實務。而這些部門中的職員通常以事務型為主,情報分析或政策研究的專職力量較為薄弱。二是情報分析體制尚有不足。受資源投入等因素限制,評估所需的情報分析仍停留在統計情報圖表化和簡單的案例介紹階段,對外調查機構實施的委托調查,往往只能以問卷、采訪等方式為主進行。三是指標體系尚不完善。除涉及軍事技術等有明確技術指標可循的領域外,總體上尚未形成指標體系。如只有力量建設的總體規模設想,并無與各項軍事功能相對應的專項規模設想,因而在行動想定、力量規模、輪戰計劃等方面欠缺具體性,這與美軍的四年防務評估有明顯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地位作用十分有限。日本政權的短命和不穩,可能降低其戰略評估效用。這一問題不僅限于軍事領域,也存在于整個日本政治體制內。受一黨長期執政、派系輪流坐莊的“1955年體制”影響,政壇高層人事頻繁變動成為戰后日本特有的政治現象。日本首相任期不定,通常不過1~2年,極為短暫。較之與總統任期相一致的美軍四年防務評估,其戰略評估的生命力相當存疑。另一方面,政權短命可能降低政治領導人對安全保障領域的關注程度,進而引發政治主導力在安全保障領域的嚴重缺位。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戰略評估的地位作用往往大打折扣。通常帶有某任政權色彩的評估結果,往往在政權交替后會部分修訂,甚至全面推倒重來。如從“04大綱”到“13大綱”期間,短短10年即經歷了2004、2009、2010和2013年的4次調整,毫無嚴肅性可言。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策連續性,戰略評估結果或許被迫成為各方意見妥協的最大公約數,在迷失方向的情況下發揮促成政策調整的效用。
責任編輯:劉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