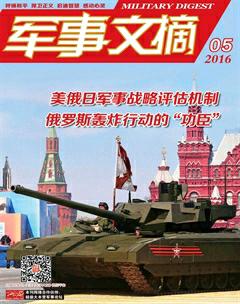戰爭進入“融空間”時代
韓旭東
近來,美國計劃封存現役先進武器裝備的舉措引人關注:美國計劃未來陸續封存現役22艘巡洋艦中的一半,以及大批性能卓越的戰機。美國看似瘋狂的舉動背后深藏根源:美國正在為規模更大和形態更先進的戰爭做準備。

二維陸地戰爭在人類戰爭史上占據了相當漫長的時間
美國意指的新型戰爭形態是一種在“融空間”內進行的戰爭,美國正在將傳統戰爭中的戰場轉化為“融空間”內的戰場。在“融空間”內,美國可以憑借技術優勢繼續維護霸權地位。
傳統作戰空間是三維空間
自原始社會后期現代意義上的戰爭出現開始,人類戰爭很長時間內都是在二維平面戰場上展開的,即在地面上展開。這主要是受限于當時武器裝備依賴的作戰平臺尚未涉入水下或空中。
隨著水面航行技術和能力的提高,人類將戰場從陸地延伸至水面,但水面作戰相對于陸地作戰而言依然處于輔助地位。雖然在地中海地區,陸地作戰表現為服務水面作戰的特點,但這種“逆向”相對于整個人類戰爭史而言,無疑只是局部和偶然的。
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異常緩慢,二維陸地作戰在人類戰爭史上持續的時間相當長,不經意間走過了木石時代、金屬時代和火藥戰爭時代。隨著氣球的出現和潛艇的發展,人類戰爭才開始漸入三維戰場時代。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時,大陸軍企圖用耶魯大學大衛·布什奈爾制造的“海龜”號潛艇攻擊英國皇家海軍“老鷹”號軍艦。雖然這場開創潛艇襲擊軍艦先例的嘗試沒有成功,但是開啟了三維戰場時代。在1848~1849年的奧意戰爭中,奧地利軍隊使用200個小型氣球攜帶30磅炸彈,計劃漂浮至威尼斯上空后用于襲擊意大利。無奈風向不利,計劃未能獲得成功,但這是人類嘗試以大氣空間平臺作為戰場的開始。美國南北戰爭后期的1864年2月17日晚,南方邦聯軍隊派出“漢利”號潛艇,成功炸沉北方聯邦的“豪薩托克尼”號護衛艦,首次實現潛艇成功炸沉軍艦,從而創造了三維空間成功作戰的第一戰例。1911年意土戰爭期間飛機運用于空襲后,真正意義上的三維戰爭開始登上舞臺。
后來,隨著潛艇和飛機性能的迅速發展,潛艇逐漸成為重要的水下作戰平臺,飛機也逐漸成為了空中主宰,但即便至二戰末期原子彈開始顯示巨大威力,人類戰爭舞臺依然被束縛在三維空間里。
太空博弈推動戰場向“融空間”延伸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軍事斗爭的日益激烈,戰爭舞臺逐漸突破了三維空間的局限。1957年8月,蘇聯首次試射成功第一枚SS-6洲際彈道導彈;1959年,美國開始列裝第一枚“宇宙神”洲際彈道導彈,人類開始具備“不動地方”就能打遍全球的能力,戰爭初露從地區性向全球性擴展的端倪。隨著戰略轟炸機、加油機、航空母艦和戰略核潛艇等具有全球作戰能力的武器裝備陸續登場,全球性戰爭正在加快形成的腳步。此時,人類的戰爭空間正在逼近整個地球,戰場的地理空間達到最大限度—全球。于是,為奪取新的戰爭優勢地位,人類開始尋求新的作戰空間。

盡管1959年美國進行了第一次反衛星試驗,1972年蘇聯裝備了反衛星武器并組建部隊,但這只能看作是將外層空間作為戰場而進行的準備而已。隨著2010年人類首架空天飛機X-37B搭乘“阿特拉斯”-5型運載火箭發射升空,人類武器平臺真正實現了從大氣空間向外層空間的延伸,并將大氣空間與外層空間融為一體。人類作戰空間正在發生“界限性”的變化。而美國和俄羅斯相繼組建太空部隊,則標志著太空已然成為新的作戰空間,傳統的三維戰場拓展到太空,開啟了“融空間”博弈的新時代。
虛擬空間推動“融空間”完善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戰爭博弈正從現實空間向虛擬空間延伸。海灣戰爭爆發前,美國把伊拉克從法國購買的一種用于防空系統的新型電腦打印機內的某芯片換為植入病毒的同類芯片,從而通過打印機將病毒侵入到伊拉克軍事指揮中心的主機。當美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時,美軍用無線遙控裝置激活隱藏的病毒,使伊拉克防空系統陷入癱瘓。這一事件可以認為是開啟了虛擬空間的博弈,人類邁入了虛擬空間博弈的時代。
傳統戰爭作戰空間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空間的延伸和拓展,作戰空間依然是在地球三維空間之內變化,并未出現質的飛躍。而“融空間”的出現,是戰爭形態發生轉變的一個根本性標志。
所謂“融空間”,是指戰爭從現實地球的三維空間延伸到外層空間、虛擬空間,并且大氣空間與外層空間形成一體,構成一體化的現實空間;同時,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相互交融,人們能夠在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之間進行交互式的軍事活動。以往傳統戰爭形態的變化,都是在現實空間內進行的,而“融空間”卻使戰爭從現實空間跨入了虛擬空間,這是革命性技術推動下的發展。
隨著“融空間”的出現,現實空間的軍事博弈將從主導性降為輔助性,虛擬空間的軍事博弈將上升為主導性。形象地說,在“融空間”時代,“神經的軟博弈”將是主導博弈,“肌肉的力博弈”將是輔助博弈。“神經的軟博弈”主要表現為技術上的博弈,“肌肉的力博弈”主要表現為以人員和武器為主要內容的軍力博弈。
“融空間”作戰的突出特點是交互性
可以認為,未來的“交互化戰爭”主要體現為技術上的博弈。近年來,隨著3D打印技術的不斷發展,也逐漸應用于軍事領域。近日,美國海軍首個3D打印導彈零部件已經秀于“三叉戟”導彈上,預示3D打印技術即將在軍事領域開啟廣泛運用。
將電腦中戰爭需要的武器通過3D技術打印出來,然后在現實戰爭中打響電腦中構想的戰爭,這種技術就是“融空間”軍事博弈的一個現實案例。
首先,人們可以通過電腦對未來戰爭進行兵棋推演,大致勾勒出未來戰爭的輪廓。在推演過程中,對作戰雙方需要的武器裝備進行預想,對武器裝備的技術數據提出要求;通過電腦對武器裝備進行設計,最后通過3D打印技術生產產品,即預想中的武器裝備。在現實作戰中,軍隊運用這些武器裝備于戰場,并根據戰場實踐檢驗武器裝備,繼而對武器裝備提出新的改進建議和設想,然后重新進入電腦進行兵棋推演,以驗證新武器裝備的實際作用。這就是通過虛擬的未來戰爭設計武器裝備的過程。
其次,虛擬空間的戰爭與現實戰爭進行互動。從美軍捉捕本·拉登的戰例可以看出,美軍將在巴基斯坦捉捕本·拉登的現場畫面通過攝像傳送到美國本土戰略指揮部,戰略指揮人員通過觀察作戰場面進行指揮,戰場現地人員根據指揮部的指示適時調整作戰行動。這種虛擬與現實之間的互動,實現了捉捕本·拉登的預期作戰行動。現實空間作戰行動-虛擬空間作戰行動-現實空間作戰行動之間的轉換,可以認為是“融空間”內的主要作戰樣式。因此,在未來的作戰行動中,只有將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作為統一的整體來籌劃,將二者視為統一的作戰空間,作戰行動才能夠取得預期的結果。
結 語
不難發現,“融空間”內的作戰力量正在構建,“融空間”作戰正在形成。不正視“融空間”作為未來作戰空間的觀點是不對的,不重視“融空間”軍事發展問題就想贏得戰爭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探索“融空間”內戰爭的特點與規律是當務之急。只有站在“融空間”戰爭的潮頭,贏得“融空間”戰爭才有希望。
責任編輯: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