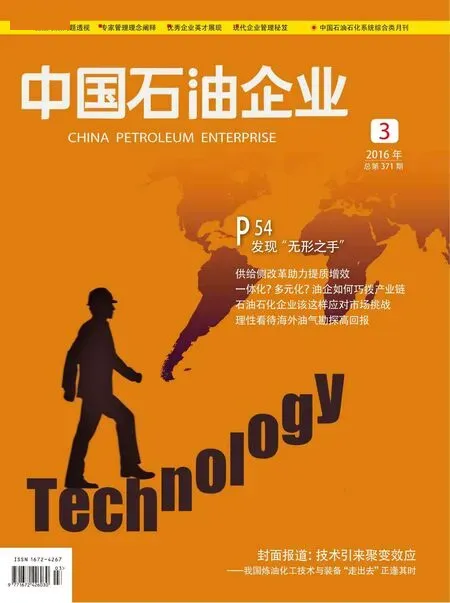說說“兩會”說得少的話
?
說說“兩會”說得少的話

2016年的全國“兩會”舉世矚目,其委員和代表們討論的話題和提交的議案,可以說是“全面”和“到位”,有些發言和議案還大有“一箭中的”的非凡力量。但筆者在瀏覽大量報刊信息中卻發現了一個問題,有關農業的發言和議案卻說得少,電視報刊媒體的記者圍繞著農業當下存在的問題而展開說的話題,卻更加少之又少。以個人之愚見或直言,當今我們這個社會有“重商輕農”的傾向。
無疑,古代之中國太“重農輕商”了,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在周秦諸子之中相當普遍。那時的古人并非知道如司馬遷所說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道理,只知道一味地從事男耕女織才是“上業”,貧寒者可以借“末業”脫貧,那是成不了氣候的。
當然過去古人的“重農”或許還有別的意思。成功“商人”呂不韋所編《呂氏春秋》的《上農》篇就有這方面的記載,其要點用今天的話翻譯出來還蠻有意思:古先圣王引導百姓優先從事農業,不僅是為了開發土地資源,而是重視其思想修養。因為務農者行為穩重,少徇私誼,則公法容易確立;而事工商者喜歡用智,小聰明耍多了便行為詐偽,總想鉆法令的空子;是非既不確定,容易不聽從號令,又何能對敵作戰?務農者產業為不動產,就安于本地,不輕易遷徙。反之,力工商者多為動產,其逐利而居,正類游牧者之逐水草,很容易遷徙。一旦國家有難,就會不居本地而遠避,自然談不上保家衛國。今天我們從呂不韋的這些“意思”里不難看出,古人重農輕商大多看重的是文化因素,那就是落葉就要歸根,所謂“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提示著國人所居之地就是國土的范圍,怎樣使農業姓農、人民安居而不遷徙,是遠古時代人君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即農業和商業各有其附載的行為模式和思想風尚,不能僅從直接獲“利”多少的物質角度來計算,還要考慮其他方面的輕重緩急。
毫無疑問,中國社會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鄉村。社會越是發展,農業發展就越顯得重要。完全可以這樣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黨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著農業、農民的問題。公元1958年,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應運而生。太陽系中這顆蔚藍色星球的北緯32.95°—33.18°,東經113.37°—114.10°之間—河南省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從此開始了最真實的“天國”神話和最莊嚴的人間荒唐,直至數億人爭放糧食高產“衛星”,畝產最高產者聲稱達824500余斤。1958至1978年的人民公社,其間又有多少悲劇、鬧劇與絕痛令人“不堪回首”?但是我個人一直認為,這一段歷史是“特別”重視農業的創造實踐,應該是有血有淚也有喜悅的歷史!曾被稱之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它對于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至深至巨,這更是一段人們無法忘記,同時也不應當忘記的歷史。
不可否認,我們眼下“重商輕農”的表現還在不斷地放大,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舒爾茨和費孝通的農業經濟理論。舒爾茨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他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從事農業經濟問題研究,60年代把對農業經濟問題與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結合起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問題,尤其是在其《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獨樹一幟地闡述了農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農業政策的有效性。《江村經濟》一書是費孝通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時撰寫的博士論文,論文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的實地考察寫成的,旨在說明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和動力問題。費孝通晚年把自己研究的所得歸納為簡單的四個字“志在富民”。
一言以蔽之,農業問題是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要說中國目前改革中最大和最艱巨的問題是什么,回答是“三農”問題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有異議。但如何讓這個問題落地生根,卻是個被忽視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說得精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能丟了農村這一頭。”他還深情地說:“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習總書記所說的“農村這一頭”和“鄉愁”,應該需要我們深深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