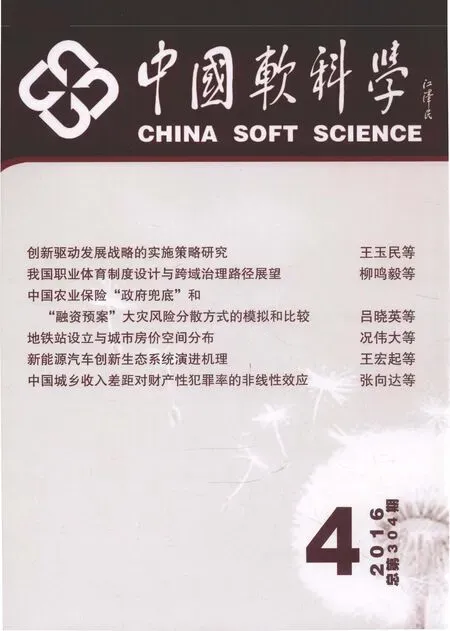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策略研究
王玉民,劉海波,靳宗振,3, 梁立赫
(1.中國科學院,北京 100864; 2. 中國科學院 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北京 100190
3.中國標準化研究院, 北京 100191; 4. 科學技術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北京 100045)
?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策略研究
王玉民1,劉海波2,靳宗振2,3, 梁立赫4
(1.中國科學院,北京100864; 2. 中國科學院 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北京100190
3.中國標準化研究院, 北京100191; 4. 科學技術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北京100045)
摘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提升產業結構、實現跨越發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從驅動對象、驅動方式和驅動力源泉三要素出發,以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鏈條為坐標軸,構建了“四相模型”,理清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本認識問題,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策略選擇思考和策略選擇路徑,并對現階段存在諸多阻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難題提出了策略建議。
關鍵詞:創新驅動發展;四相模型;策略性問題;策略選擇;知財運營
在以創新為競爭焦點的發展新時代,創新能力的提升已經成為國家發展與國際競爭的核心。我國適時地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改革開放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等戰略有機結合,構成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整體。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是我國把握時代發展機遇、應對國際競爭挑戰、謀求國家跨越發展的重大舉措。
在國家整體戰略中,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效益與水平,是實現我國國家整體戰略的基礎,直接影響其它各戰略實施的有效性。認真研究并深入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當前各界的緊迫任務,在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政策設計、措施安排中,需要講求踐行的策略選擇,以提升創新驅動發展的實際效益。本文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實施舉措之間的若干策略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旨在厘清價值關系、明確戰略重點、提出策略選擇。
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價值導向
正確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檢驗標準首先是實際效益,而不是踐行的方式或舉措,因為符合價值導向的實際效益是戰略實施的目的所在,是檢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效性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是對戰略自身導向性的判斷與踐行行為指向的問題。
(一)明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要點是戰略順利實施的前提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本身直接顯示出三個要點:驅動對象、驅動方式和驅動力源泉。從戰略學的角度看,創新驅動的戰略方向即為創新驅動什么和要達到什么樣的驅動意圖,這是踐行創新驅動的價值導向性問題。如何實現有效驅動以及驅動力的源泉則屬于體現價值導向的戰略措施,之后才是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政策設計與進程組織。充分認識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價值導向,是把握與實施戰略的基本前提[1],是戰略實施的出發點、落腳點與判別創新驅動效益的標準,是判斷創新驅動內容、選擇創新驅動方式與謀劃創新驅動實踐過程的基本依據,而后者則是為戰略價值導向提供支撐,是依據環境條件以導向效益的最大化為原則而因時、因地、因實施主體特征而靈活選擇的。顯然,探討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問題,必須要界定、擺正并理清創新驅動價值導向與驅動方式、發揮驅動功能的創新力三者的關系。
(二)發展知識經濟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導向的直接目的
創新驅動的影響效應十分廣泛,波及到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全社會各領域。就學術研究而言,需要把創新驅動作為特定對象予以界定。首先,創新驅動是經濟發展動力理論的重要內容,美國經濟學家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將人類經濟發展歸納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驅動階段[2]。創新驅動特指經濟發展從以投資為經濟主要驅動力基礎上邁向創新驅動發展的新階段,是新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創新驅動發展自然因其經濟基礎功能而顯示對社會上層建筑的拉動與影響,但這不屬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專項研究的范疇,因為創新驅動發展直接導向在于經濟發展。其次,在從以資本、勞力、資源為主導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向以知識、人才、信息為主導要素的創新發展模式轉變進程中,創新驅動的新經濟,是指以“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經濟,或者概括為知識經濟,即不同于傳統經濟,也不是指支持知識經濟發展的知識創新活動與成果本身。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創新驅動導向的重點是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以知識為第一要素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效益與水平提升。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目標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同于原有的粗放型、以資源換經濟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從經濟質量出發,推行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推動創新生產力提高,實現生態經濟和綠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綠色經濟增長,是將環境保護、技術創新、社會進步和居民福祉充分結合。再次,以創新為驅動力的知識經濟的重點,是通過知識資產與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所產生適應現代社會生產、生活所需要的產品形態與經濟效益,核心是知識資產的運用與經營,即知財運營[3]。
(三)綜合運用創新驅動的源泉和要素則是基礎性的保障
創新驅動源泉是指能對知識經濟發展發揮驅動作用的創新以及創新能力。首先,創新與創新能力作為驅動源泉,對實現創新驅動導向的經濟效益十分重要,但卻不屬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價值導向內容,這是不能顛倒或者混同的。其次,創新因素的界定標準是具有創新驅動功能。創新不只是技術創新、科學創新,還包括科技創新之外的各種具備驅動功能的因素,諸如觀念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體制機制創新與組織創新等。為簡便計,把除科技創新之外的其他各類創新綜合簡稱為管理創新。因此,創新驅動不僅是技術創新驅動,也不限于科技創新驅動,而是科學、技術與管理創新的綜合作用。誤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同于科技創新驅動戰略的提法,是不全面的。再次,要充分認識管理創新的關鍵作用和重點地位。管理創新遠遠超過重新分配勞動力、資本和產品的范疇,需要依據新的信息技術、文化和市場,建立組織機構的新規則和結構,通過逐步加強與改進、重建創新制度和結構,促進技術創新、組織機構、社會環境、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系統的穩定性建設[4]。朱英明(2013)指出了我國普遍存在的重科技創新輕管理創新的現象。他論證了目前普遍接受的創新主要集中在新產品、新技術或新服務方面,然而創新還包括組織創新和業務創新,創新需要整個行業或全球視角的管理創新[5]。弗利曼、倫德瓦爾也論述過創新與創新驅動能力并不完全取決于創新資源優劣、創新主體強弱,而在于創新資源、創新主體以及社會創新要素的涵養、集聚與整合的形式與能力[6]。創新資源包括內部創新資源和創新能力,還包括外部的知識集聚、技術引進和創新資源的引入,將內外部資源進行集聚、消化吸收再創新,突出“后發優勢”,成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技術支撐和資源支撐。還應該注意到,創新具有集成性,Roper和Dundas(2015)認為創新的成功依賴于技術知識、戰略經營和相關市場的開發。他們運用企業創新面板數據來分析內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檢索以及創新產出,發現企業的知識流來源于內部創新與外部吸收,并直接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7]。從區域創新系統來說,Wang et al.(2015)運用資源開發—利用的框架分析區域創新,發現傳統的創新方法,即結構性、功能性、三螺旋的創新方法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知識代際交替及知識應用更為突出[8]。
(四)驅動方式實質上是創新的價值觀問題
驅動方式是指創新驅動源對知識經濟的價值顯示形式,表觀形式是創新體系建設,但其實質是創新的價值性。對其認識與運用的實踐所表現的是社會創新價值觀。正確的創新價值觀,是確保創新驅動價值導向的根本原則。短視的、急功近利的創新價值觀,將阻斷或消弱創新的價值功能。在網絡化的創新鏈條中,不同的創新活動具有不同的價值屬性。一般科學創新具有思想、人才、文化、學科等價值,對經濟發展作用大多是間接的、隱性的、長期的,但卻發揮著根基性戰略性的影響。忽視或者不適當地替代其在創新鏈條中的價值作用,都是值得警惕且必須盡力避免的。技術發明既具有類似科學的隱性價值,又具有商業流通的經濟價值,還具有技術物質化創意經營的潛在經濟價值,而技術的商用化創新、產品化創新和經營化創新則側重顯示直接的、現實的經濟價值。管理創新在創新鏈條內無處不在,其價值作用與管理創新對象的價值性類同,更為明確地說管理創新具有創新鏈條中各種創新價值性的特征,并依賴創新整體予以顯現。在創新驅動方式上,創新資源、創新體系、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對經濟的作用形式具有復雜化和差異化的特征。從經濟效益與創新價值的辯證關系來看,是通過有形與無形的知識或資產,直接或潛在地推動經濟發展。對于網絡化的創新鏈條的價值性,大致可以歸納為間接與直接、潛在與現實、長期與短期價值性耦合、漸變的組合形式。以上是分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價值導向的重要依據。
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點關聯的“四相模型”
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個要點的討論,有助于厘清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本認識問題,但對于如何提升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有效性問題,還需深入解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要點之間的關聯性,關鍵是分析創新驅動能力與驅動方式綜合表達創新驅動價值導向的關聯關系。要解析其關聯內容,把握基本的關聯因素,概括要素之間的關聯形式及分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要點的關系處理問題,是亟需解決的難題。
(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點關聯性的簡化分析工具
比較分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點關聯性,較為可行且容易理清的方式就是簡化的框架結構分析。首先是以簡化的創新鏈條與驅動價值鏈條為依托,通過兩者交叉透視創新驅動三要點的基本關系,基本分析辦法是以科技、經濟與管理耦合的創新鏈條為縱軸,以創新驅動價值性組合方式為橫軸,構建創新驅動發展的四相模型如下圖。圖中的四個象限代表關聯關系的四類內容或四種類型。

圖1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點的關聯內容
(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點的關聯內容
上述簡易化的四相模型中,顯示出三個戰略要點關聯的具體內容,由此可以引入關聯內容的影響因素,為關聯形式的分析做好基礎。
A象限是創新顯示的現實的、直接的經濟效益象限,代表創新驅動的價值導向。其內容即為以知識為第一生產要素的知識經濟發展,核心因素是知識創新的運營與效果,即知財運營。知財運營,是通過知識運用與經營手段實現知識資產財產化的過程,包括知識資產的財產化、知識財產的無形資產運營、知識財產的物質產品創新及產業結構優化的方式。將知識市場化和財產化,是知識、技術和信息為主導要素的創新發展的路徑[3],知財運營創新處于創新驅動知識經濟發展的戰略支點的地位。在推動知識財產化過程中的創新,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提高生產效率,深化產業分工和促進經濟增長[3];有效地提高知識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最終達到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目標,實現我國從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以知識為第一要素的新型經濟轉變的跨越發展戰略意圖。
B象限顯示創新培育知識資產的現實效應。這是創新培育知識經濟的第一生產要素的直接成果,是現代有形生產力一種表現形式,是實現A象限所代表的知識經濟發展導向的基礎或重要條件。知識財產獲取的影響因素,不僅取決于知識的創造,更取決于將知識進行財產化的經營意識創新、知識財產制度創新、知識管理創新等重要內容。知識管理創新是獲取、提升知識生產力的核心因素。從經濟效益導向的視角分析,創新培育知識資產的表征量,不僅在于知識財產的來源,還取決于獲取或擁有知識資產的數量與質量,其中包括知識財產的創造、流通、借助或善用人類智慧等各種有效形式。強調知識創造的重要性,表述的是競爭性、政治性因素,是非常必要的;進一步而言,強調知識資產的擁有量,表述的內容是效益關聯性、實力性因素,從效果出發強調擁有的量與質更為重要。或者說,為加速知識經濟發展所必須擁有的足夠強大的知識資產實力,自主創新是必要的,知識流通獲取與學習借鑒也是必要的,同時也需要善于借用人類智慧而達到效益,這些都值得鼓勵。加速知識管理創新,促進我國知識資產擁有量的實力,其本身就具有創新驅動的策略性意義。
C象限是顯示創新的無形、間接效益的知識成果。創新成果特別是重大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成果,對經濟、社會的思想、文化、人才具有隱形、間接且長遠的作用,影響因素有助于明確科技價值觀。對創新成果的隱形作用,既不能急功近利地以現實效益為導向,更不能予以漠視、淡化或取消。在這方面,我國曾發生過值得深思的教訓。其實,生產力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包括人類改造自然的物質能力與精神能力。從生產力與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隱形作用的創新成果發揮改造自然的精神力量作用,因而也是知識經濟生產力的組成部分。與知識財產及其他物質資源相比,知識是一種發揮潛在、間接、長遠影響的精神性的軟生產力。知識成果軟生產力與知識財產有形生產力結合才構成完整的知識經濟的第一生產力。要從提升我國知識經濟第一生產力的高度重視創新成果的價值,要強調創新驅動的軟性、有形雙驅動力的概念,提高完整生產力的意識,絕不可偏廢或脫離。創新成果以知識教育、思想解放、文化意識和人才培育等隱形功能為主要表現形態,對國家創新、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發揮著難以發覺但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的支撐作用。隱性知識在知識積累、技術創造及市場應用過程中,在企業等創新主體內部進行知識、信息和技術的傳播,具有難以復制化和顯性化的特點,對經濟發展和人才能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知識文化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9],有助于提升生產力水平,加速經濟轉型升級。
D象限是指優化生產力創新并驅動知識經濟發展的驅動形式。其基本形式是創新能源的集聚、整合的運作模式,具體內涵包括推動知識成果創新的模式,也包括知識財產獲得的引導模式,更包括綜合發揮知識生產力的作用顯示知識經濟發展成果的驅動模式。以上三種模式的有機綜合,已經大大超越了原有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成為了包括國家科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性、系統性、整體性的國家戰略內容。最值得關注的是,國家創新體系已經升華為了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實現形式,因此拓展、升級“國家創新體系”概念,進行國家創新體系的重構,是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當務之急。從國家創新體系總體框架角度出發,張景安(2003)提出需要綜合利用各方資源,既要積極推動產學研協同發展,充分發揮各類創新主體的作用,大力推進自主創新、集成創新、互動創新和開放創新,更要從國家戰略層次優化整體頂層設計,在科技、經濟、社會的整體中強化對資源的優化配置,拓展并調整創新體系結構,突出國家創新驅動的戰略導向[10]。此外,國家創新的邊際化也逐步淡化,劉云等(2010)認為需要推動國際化的創新,豐富創新的內涵和外延,提出了創新政策制定的互動、創新資源的流動與優化配置和創新主體創新活動國際化的路徑,促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11]。
(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要點的關聯形式
四相模型中表述了三要點的關聯作用與核心要素,其內容、要素之間的制約性則又決定為三要點關聯內容的存在的形式。從圖1中可以發現,三要點關聯因素包括:其一,發展知識經濟是創新驅動發展順利實施的發展模式,體現了知識經濟的價值方向,具有戰略前提的制約作用,這是知識經濟逐步發展并改造升級傳統經濟、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智慧經濟崛起的過程。其二,知財運營是直接體現知識經濟發展效益的關鍵或稱為創新驅動的戰略支點。知財運營是以知識作為第一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為典型特征,包含的無形資產、技術產品的創意經營恰是技術服務業或創新服務業,是生產型服務業的內核,是現代服務業的精華[12]。其三,驅動作用力的大小取決于作為第一生產要素的知識生產力的高低、善用程度和發揮作用,其中既包括現實的知識財產擁有量,又包含顯示軟性生產力作用的知識成果,更包含其相互偶合所形成的知識生產力的實際大小。第四,借助知財運營驅動支點,發揮知識生產力驅動能力撬動知識經濟發展效果的驅動杠桿工具,即為創新要素的集聚與整合形態。其中包含知識創新的要素整合、知識財產管理創新的要素整合,以及以知識軟生產力、硬生產力的耦合為基礎,實現知財運營創新的要素整合,這應當屬于國家創新體系的構建與優化的范疇,其中的作用關系由圖二虛線箭頭所示。通過對三要點關聯形式進行歸納,可采用杠桿撬動的形象表述:以運用國家創新體系的杠桿方式、發揮知識生產力的能量作用、借助知財運營的驅動支點實現驅動我國創新發展的戰略意圖,這是由創新驅動三要點內容所決定的存在形式(見圖3)。

圖2 創新驅動要點關聯內容要素的作用形式

圖3 創新驅動要點制約因素的關聯形式示意
經過上圖的分析,引申出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三要點關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創新驅動的形式與內容相適應、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是奪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效果的基本保障。
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策略性問題
(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策略性問題的界定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形式適應于內容、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的要求,統籌概括起來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聯內容的制約形式,實質是價值導向的實現過程,也就是效益引導性;二是其關聯形式必須適應并支撐創新驅動的內容,要適應創新驅動發展進程中需求調整的變化,這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客觀要求。同時,如何適應內容調整而相應的演變,則取決于關聯形式的思路概括與總體設計。以上是屬于國家創新戰略驅動所涉及到管理創新的主觀問題,是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總體性問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內容及實施過程中形式演變,和其關聯形式將影響創新驅動戰略的順利實現。不適應內容需求的形式不僅不能促進發展,反而會產生嚴重的阻礙作用,這就是必須討論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策略問題的原因所在。
所謂策略一般含義廣泛,大可與戰略同義,小可為社會行為的某種技巧。本文是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三要點關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如何處理問題視為策略問題,這是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大概念之下,屬于為戰略服務的從屬性概念;但又是特指對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制度設計、政策安排以及戰略部署、組織實施等更具有宏觀、全局指導意義等顯示戰略功能的一些重大因素,屬于戰略實施必須總體考量、定奪的宏觀因素,相當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方針、路線或原則等重大問題的研判,由于不是制度設計與政策創新的措施問題,因而也不屬于戰略實施的范圍。在戰略與措施之間的這種具有戰略功能的重大因素被視為策略問題,這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所固有的重要因素,是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化與解釋,是制度設計與政策改革所依賴的頂層策劃,這是不可缺少的戰略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因實踐任務、方式、政策的鮮活特性易被感知而當作重點予以突出,而此類策略分析問題因已有戰略框架所掩蓋,往往易于被忽視或被形式化、邊緣化,這是出現形式不適應內容甚至替代內容傾向的一種原因。內容與形式的顛倒是影響戰略實施效果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這在認識上屬于思想方法問題,在實踐上屬于作風問題。對于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過程的我國,注重從思想方法與實踐作風上進行學習、調整,注重策略分析的地位,是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首先應注重解決的重要任務。
(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策略問題的一般性
所謂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策略性問題,可以明確為創新驅動三要素關聯的形式如何適應其內容需求的問題。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中,策略性因素只能從三要點的關聯形式出發,進行邏輯分析,這種基于一般關聯形式引申而來的策略性因素,相對策略選擇而言,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客觀性的屬性特征。依據創新驅動三要點關聯形式不難發現,一般性策略因素包括:(1)戰略發展的效益前提性策略,核心內容是效益與舉措的關系如何處理;(2)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支撐點策略,核心是體現創新驅動效益的知識經濟發展的切入點如何判斷與選擇;(3)創新戰略驅動的創新能力策略,核心是創新能力的構成與作用發揮問題;(4)創新驅動的形式優化策略,核心是創新要素與生產資源如何整合展現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等。這四個策略性因素是此類策略問題的一般性表述,是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策略分析的基礎。
(三)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策略性選擇問題
如何思考與運用策略性因素,使其適應戰略的內容、達到戰略的效果,則是策略選擇的問題。所謂策略選擇是根據實際情況與現有能力對策略性問題進行研判與具體策略制定的過程。無論戰略與策略的選擇,都受到戰略主體的主、客觀條件與環境的制約。就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的戰略與策略選擇而言,取決于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與思想文化特征、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制度安排、社會發展狀態與國際競爭格局等。酌情而斷是策略選擇的重要原則。因而,策略選擇屬于戰略主體的主觀行為,具有主觀性、條件性、特殊性、多樣性以及發展階段的可變性特征。
例如美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較早,依賴其居于技術制高點的優勢與長于借助軍事獨統世界的戰略思維,創新驅動策略相應地運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策略、謀劃技術貿易策略以及創新領域選擇依賴軍事研發的策略等。日本較為善于運用人類的知識財產,經歷過善用世界知識進行貿易競爭、技術創新為主的階段,科技創新并重的階段,以及上世紀80年代日本崛起后發現原創不足的缺失而強化科學研究,優化創新價值鏈條的策略等。英國則具有知識創新的傳統與優勢,但弱于技術轉化與產品創新,知識運用能力不足成為發展的障礙,針對存在的以上問題,英國正在掀起技術創新、文化創意促進發展的策略。德國則基于科技發展的歷史基礎,一直采取先進制造、精選化工、環保等優勢領域重點發展策略,科學研究、技術發明、產品創新與市場經營競爭協同發展的策略等。不同國家的科技發展路徑顯示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內涵與實踐策略選擇是多樣的、演變的,都是基于國家實際與戰略意圖而進行的策略謀劃。
從研究策略選擇的角度,結合目前實際發生的問題,可將創新驅動的上述四類一般性策略因素展開,轉述為便于策略思考、策略選擇與策略實施的策略性選擇問題:(1)體現效益前提性的導向問題,即為政績考核、資源配置、監督獎懲、政策創新中的導向作用如何集中體現效益原則,對導向與舉措的制約關系如何處理;(2)體現創新驅動作用的創新成果的獲取與善用關系如何引導,即為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技術流通、產品創新與經營模式創新的關系問題,進一步而言,實質是創新價值鏈條的重點選擇問題與技術導向還是市場效益導向的關系問題;(3)體現創新能力優化的知識財產與發揮無形效應的知識文化雙驅動協同關系或者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的關系如何擺正問題。前者還包括技術創造、流通、獲取與擁有的關系,擁有與運用經營關系;后者包括知識成果發揮社會影響的渠道與方式創新的內容等;(4)知識財產運營中的物質產品創新經營與無形資產經營關系的處理,以及技術成果轉換為產品創新的技術創意過程(也稱產品創新過程)鏈條中,難點判斷、重點選擇問題;(5)體現創新驅動形式的國家創新體系優化的導向問題,包括創新要素關系與體系功能關系的結合優化問題、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的關系以及創新實體與國家宏觀治理之間如何協調改革的問題等;(6)進一步引申[13],還存在與國家發展條件、戰略布局相應的創新重點領域選擇與產業發展規劃互相協調配合的策略問題等。
四、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策略選擇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策略選擇,實質就是以適應創新驅動價值導向為前提,以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內外環境與條件為基礎,從策略層面探討戰略實施的設計依據,明確選擇實施路徑、內容、安排實施過程與形式、修訂實施政策與體制的基本規則。這是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本身所蘊含著的頂層管理創新必須先行的內在要求,體現為創新驅動的策略創新,這是不可繞行的重要環節。如此才能確保實施的措施更適應創新驅動的內容要求,達到我國創新驅動效益的最大化。策略創新將為豐富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豐富創新發展的中國模式添磚加瓦。
(一)我國創新驅動中一些基本策略性問題
客觀認識發展優勢、坦誠面對與深入挖掘發展的劣勢或短板,以利于揚長補短,是策略分析的基礎。
1. 警惕“形式化”的干擾
在我國,價值導向與舉措倒置的現象依然存在。首先,我國屬于迅速崛起、創造世界奇跡的發展中國家,傳統的社會發展模式深入人心、似成自然,傳統方式路徑依賴的傾向一時難以扭轉,因而對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新方向、新目標、新內容和新價值,易于采用傳統思維認識并從措施上把新問題納入到老模式中,難以避免以口號代替戰略、以行為代替內容,甚至出現翻牌應對的假象。其次,長期的計劃經濟以及以往的強勢政府干預,干部中重政令而輕本意、重過程而輕效果,行、效脫離的積弊已時日長久,并且長期的GDP導向、規模導向、任務導向、政績導向、任期導向,導致形象工程泛濫,“形式主義”一時難以轉變。再次,即使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所運用的政績考核、資源配置、監督獎懲、政策體系等,都來自不同部門,其中導向作用體現著部門特征,不利于具有國家效益導向的戰略實施。而如何將這一系列的導向因素,按體現創新驅動效益導向的原則統一設計、重新修訂、形成有效的價值導向體系,在認識上是個新難點,在部門協調上存在壁壘,在設計實施上是個復雜的大工程。沒有新的正確價值導向體系,也就很難確保創新驅動的高效益。另外,我國地域廣大,發展極不平衡,幅員廣大與發展問題多樣化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具有不同經濟發展基礎的區域,其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問題、任務、思路與舉措,從實際出發顯然是不同的,形成多種模式是必然趨勢,但現實存在著一個政令齊步走、一個口號唱到底,一刀切、模式化、左右看齊、互相攀比的現象。這些都值得特別關注、需要解決的價值導向性的問題。
2. 填平“創”、“用”脫離的鴻溝
無容置疑,我國科技創新的碩果累累,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已經做出巨大貢獻,這是值得引為驕傲的,然而目前依然存在著成果創造與善用脫鉤的問題。首先,在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技術轉移、產品創新與市場經營創新的價值鏈條中,我國論文引用率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專利申請位居世界第一位,成果形態的技術流通額迅速增長,產品生產與經營創造出無數的世界第一,支撐起制造業大國的贊譽。與其相背離的是,我國的產品創意、產品原創少得可憐。我國制造業產品大多屬于引進、跟蹤、山寨、仿制,這對于產業發展升級是必需的,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創新價值鏈條中“創”與“用”脫節所導致形成的“斷崖現象”。該現象的核心問題是知識運用中的技術使用價值挖掘能力不足。針對存在的該種問題,相關部門確實早已在科技成果轉化的理念下采取很多措施予以解決和應對,但是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其次,在知識創造、獲取與善用的關系中,存在著技術供給與需求拉動的關系處理問題。在國家總體科技政策中確實早已提出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的原則,但在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部署中是各自分離的,即使被多部門關注的產學研結合,依然是技術供給為主,產學研的組織結合為主,而體現市場導向真髓的是市場中的創新要素的流動與市場導向下要素的功能性結合的辦法卻很少被關注,市場導向的功能近似被湮沒,技術供給導向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這就是創新價值鏈條中用為重點的選擇問題與強化市場效益導向問題。再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成功實現崛起的新興國家,其經濟發展一般從善用知識切入,逐步過渡為以善用為基礎的引進與自創并重、自主創新為主,直至科學引領的高級階段。善于運用知識、追求知識的經濟價值始終是發展的基礎。我國經歷過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過程,科技體制改革重點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其方向是正確的,引導科學研究與技術發明、企業發展的措施是落實的,但唯獨對技術轉化、知識善用的環節措施不少,卻流于形式。科技經濟兩張皮的歷史印記與科技體制改革的路數并不完全對口,事實上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善用知識不足的局面,沒有形成善于挖掘技術內在使用價值的體制與運用市場手段拉動創新要素結合的機制。
3. 避免創新驅動“單腳跳”的跛腳態
創新驅動具有雙輪驅動的創新形態,因此雙輪協同是優化創新能力、實現高效創新的基礎,這也涉及到有形與隱形、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的關系如何擺正的問題。創新驅動的雙輪特點差異很大,其知識財產的硬生產力有形可識、有權所屬、有利可圖,具有社會關注的廣泛基礎;而發揮無形效應的知識文化軟生產力,屬于社會共有的精神力量,不易理解、不善把握、缺少現實利益的吸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視但是在實際中難以落實,從而容易導致雙輪驅動演變為“獨腳單跳”的危險。實質上,雙輪驅動問題本身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關系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極易出現強調“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卻往往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現象。解決以上存在的難題,重點在于解決知識成果發揮社會影響的渠道與方式的創新問題,不僅是科普問題,還是要素流通問題,特別是人才的流通機制以及全面創新的教育機制等。
通過對我國存在“單腳獨跳”現象進行分析,發現主要原因包括:其一、我國歷史上存在過急功近利價值觀的影響,至今還遠沒有走出急功近利的陰影。其二,我國的科普教育以及文化普及已經有較大發展,但是國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平均還較低,科技、創新意識更低。據中國科協發布的第九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2015年我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達到了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但是分布很不均衡。從城鄉分類來看,城鎮居民的科學素質水平提升幅度較大,從2010年的4.86%提升到9.72%,而農村居民僅從2010年的1.83%提高到2.43%。從年齡分類來看,中青年群體的科學素質水平較高,18-29歲和30-39歲年齡段公民的科學素質水平分別達到11.59%和7.16%。從性別分布看,男性公民的科學素質水平達到9.04%,明顯高于女性公民的3.38%。其三,在產業發展與互聯網緊密融合的背景下,我國知識產權管理與科技資源管理都有所創新,為知識流通、文化傳播提供了條件,但流通的知識需要能理解的人才去挖掘運用。目前,運用知識產權信息的人才不足、知識產權信息分析的工具缺乏,而且知識產權信息流通的范圍還比較窄,距離提高知識、文化、思想的精神生產力作用發揮與知財運營并重的要求,相差較遠。其四,人才的流動是實現知識、精神生產力效應的關鍵。目前,我國進一步加強解放科技生產力,加大對科技成果的轉化力度,但是在具體配套政策仍處于制定過程中,不利于科研人員的自由流動和科技成果的落地轉化,尤其是向基層、中西部流通的科技引導和支持政策。其五,我國教育規模不小,但學生所學與創新有距離,教育與社會需求的戰略彌合存在障礙。我國的教育思想、教育體制、教育模式都需要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教育再創新。
4. 彌補知財運營體系的缺失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物質產品創新經營與無形資產經營結合的知識財產運營的框架,但是運營體系還不完整,仍處于“破碎狀態”。其一,無形資產經營的經營模式很多,但我國僅僅初步開展技術交易、技術交叉許可等有限經營方式。技術信貸、作價入股、技術挖掘、標準戰略等已經發生卻沒有規范化,尤其是交易行為還沒有納入系統管理的范圍,缺少必要的引導政策,更無法列入統計范圍。其二,技術交易的價值在于技術的創意化,流通的技術商品形態重點不僅是技術,更為重要的體現在技術的應用思路與方案。近年來我國技術交易雖然發展迅速,規模遞增的好趨勢,但是列入技術交易的技術商品形態還是技術成果的初始態。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大多缺少原始技術的轉化能力,卻有極強的跟蹤、仿造能力,因此我國大多企業急需的是技術使用價值挖掘的技術商品形態,如技術使用價值的產品概念創新、解決產品概念技術原理的概念產品創新及技術的新產品結構設計、工程工藝等技術商品形態,這些重在技術運用模式的技術商品形態,便于企業吸納進行技術與要素整合,屬于技術交易的高級技術商品形態。我國技術市場具有各類型的技術商品,但真正能夠滿足需求的技術商品卻無法提供,仍處于不成熟的初級階段,遠遠脫離企業發展的現實特征。其三,目前我國技術服務體系也處于適應初級技術市場的發展狀態,規模龐大,發展迅速,但是缺少為技術商品形態創新的服務機構。現有的中介機構滯留于并不符合商品原理的技術價值評估的工作,還沒有對技術使用價值挖掘評估的方法,缺少技術創意服務的工具;與此相應的是缺少真正進行技術創意服務的機構,缺少善于技術創意服務的人才,也沒有對技術創新服務活動有效的引導政策。其四,在物質產品創新經營中,企業的制造能力強,專利產出能力強,但屬于運用知識進行產品創新的能力不足,依賴于山寨、仿造、跟蹤的產業體系自然處于產業價值鏈條的低端,這也是創新價值鏈條存在價值斷崖的一種表現。這些都是我國知財運營體系完善化所應解決的問題。
5. 防止管理創新滯后的拖累
管理創新不僅在創新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創新實踐過程中,還貫穿于創新驅動的三要點、四象限以及驅動形式等過程中。從創新的角度,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從創新驅動的角度,管理創新不是與科技創新并列的單獨的創新問題,而是融合在所有創新之內、引導創新驅動整體的關鍵問題。例如科學研究、技術發明依賴管理創新的保障,知識資產的獲取、知識精神效益的發揮取決于創新制度的設計,而且知財運營市場機制的構建、整合創新要素的驅動方式的形成,本就屬于管理創新的范疇。可以說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管理創新不僅重要而且必須先行,發揮先導作用。目前還存在著忽視管理創新地位的問題。其一,將創新驅動歸屬于科技創新驅動的認識不為少數,影響也較為廣泛。其二,以為創新驅動是企(事)業單位、基層組織、大眾的面臨的工作,存在忽視管理機構改革與管理創新的潛在危險。如在長期的科技體制改革中,改革的重點一直傾向于微觀科研組織的結構調整,缺少對管理機制的改革,機制的完善相對滯緩;有關科技管理的國家多部門的協調機制始終沒有形成根本性促動力。在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應引以為戒。其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價值實現的本質是以創新要素的創造、集聚為基礎,通過要素整合而實現。微觀的要素整合是知財運營的核心,中、宏觀的要素整合是國家創新體系優化的方向。然而目前在知財運營上側重強調創新要素的集聚與流通,但如何引導整合的相關措施少、音調低,有的甚至避諱創新要素整合的概念。在中、宏觀創新體系建設上,仍然停留在強調創新要素關聯的體系形式上,缺乏從創新要素整合而顯示的功能結構上的設計與引導政策。這是管理創新的一個難點。其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意義上的管理創新,已經涉及到國家科技、教育、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協調問題,因而包含了國家治理的因素或意義。從優化國家治理實現國家戰略的高度理解管理創新的地位,分析管理創新的內容,研判管理創新的方向,推動創新實體與國家宏觀治理之間協調改革等,是個極為重要而艱難的課題。顯然,管理創新已經成為國家中、宏觀層次的管理改革的關鍵內容。
(二)對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策略選擇的討論
依據上述的策略性問題分析,不難引申出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中策略性選擇的若干重點。這些重點的策略選擇問題,相互間具有密切的關聯性,還需進一步凝練、歸納,突出重中之重。旨在便于討論,將重點問題的建議進行如下分析:
1. “效益為本”策略
要將價值導向“鐵律化”,除解決認識與觀念問題之外,還需將人事、分配、考核獎懲、資源配置等所有與導向有關的政策以創新驅動效益為準進行重新修訂,形成國家新的導向制度與政策體系。該舉措能否順利實施,難在必須要打破部門利益、消除行業潛規則、調整干部盡職模式、轉變社會行為方式。與此同時,要進行行業、行政系統的戰略定位,以定位為價值導向,糾正創新實踐中錯位、越位、亂位、缺位的現象。
2. “知識善用拉動”策略
在效益為導向,以全面優化創新價值鏈為基礎,要突出以知識善用為創新價值鏈建設的戰略根基。知識善用拉動策略是市場導向的實現形式,是以“用”強化對知識創造、流通的拉動作用的主導因素,將為落實創新的市場導向、企業為主體的戰略導向機制發揮根本性作用。目前,無論創新管理、創新政策、創新獎勵以及創新統計等,都側重在論文數、專利數、生產經營額等創新價值鏈的兩端,而缺少對以用為重點創新活動的關注,阻礙了知識在流通環節的再創造和再傳播的功能。
3. “雙輪融合驅動”策略
堅持硬實力與軟實力融合、物質產品經營與無形資產經營并重的策略,積極推動雙輪融合,共同驅動創新。其中的難點是軟生產力的潛力挖掘,特別是知識、人才、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機制、創新與軟生產力要素分析工具的拓展、全民教育模式創新及其創新文化的建設。
4. “要素整合”策略
創新要素整合是技術財產化、產業化、價值化的根本途徑,是創新體系建設的基本方向。目前要素整合雖然認為是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但還是處于口頭禪階段,如何切實實現創新價值的要素整合卻被避諱于腦后。這恰恰是重規模而忘卻整合運用效果、重形式而忽略結果的“形式化”作風的表現。該策略不僅需要觀念的調整,更需要要素整合模式創新、整合工具創新、整合的組織形態創新以及整合的制度、政策創新。
5. 突出知財運營為“驅動重點”策略
在創新的價值鏈條上,知識善用為根基;在創新的功能結構鏈條上,與知識善用為基礎相對應的是要突出知財運營的驅動重點效應。這是從以資本為主導生產要素的傳統市場結構向以知識為主導生產要素的新型市場結構演變的必然要求,演化的難點在于技術產品化中的技術創意體系培育。這既是無形資產經營提升技術商品形態的基礎,也是物資產品經營中填平價值斷崖的措施。對此需要從知財運營的政策體系、組織體系、服務體系、技術創意的人才、工具、方法、理念等多角度進行培育、完善。
6. 積極制定“管理創新先行”策略
管理創新的地位、功能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滿足管理創新先行的要求,這不僅涉及創新驅動的政策體系創新、國家創新體系優化創新,甚至包括了與國家治理協調的創新。管理創新的任務是十分復雜艱巨,且十分必要的。為此管理創新先行可以采用先行先試的策略,先行創新示范的重點即為與效益為本策略、知識善用拉動策略、雙論融合驅動策略、要素整合創新策略以及知財運營為重點的驅動策略等相關問題做起,逐步深化。
7.重點實施“分類引導”策略
我國幅員廣大,區域的經濟發展形態囊括了要素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和創新驅動發展等多種發展類型。盡管各地都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引導推動各自發展,但由于社會經濟基礎差異、組織管理與科技文化條件不同,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思路、模式、措施應當有所差別。實施“分類引導”策略才符合實事求是精神與高效益的原則,在具體工作中,分類的依據可以從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知識創造、運用、流通的能力等因素進行選擇。
參考文獻:
[1]張順江. 決策科學原理:精神現象學[M].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3. 120-269.
[2]邁克爾·波特. 國家競爭優勢[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25-75.
[3]靳宗振,劉海波. 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議題:知財運營[J]. 中國軟科學, 2015(5):47-57.
[4]海邁來伊寧,海斯卡拉. 社會創新、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1:11-33.
[5]朱英明. 論創新驅動發展管理[J]. 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10):16-22.
[6]王玉民. 海西經濟區的超常發展與策略選擇—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的幾個戰略問題[J]. 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8(3):38-45.
[7]Roper, S., Dundas. N.H., Knowledge stock, knowledge flow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matched patents and innovation panel data [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1327-1340.
[8]Wang et al. The evolving nature of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sights from an exploration-exploitation approach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5(7):1-13.
[9]Ikujiro Nonaka, Noboru Konno. The concept of “Ba”: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8(3):40-53.
[10]張景安. 建設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總體框架的思考[J]. 中國軟科學, 2003(7):6-11.
[11]劉云等. 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政策概念、分類及演化特征[J]. 管理世界, 2014(12):62-68,78.
[12]王玉民,馬維野等. 專利商用化的策略與運用[M].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7:47-82.
[13]馬俊如、孔德涌、王玉民等. 2008國家創新體系發展報告:國家創新體系研究[R].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8: 28-79.
[14]王玉民. 產品原創的理念與策略性運用[J]. 中國軟科學, 2012(12):114-122.
[15]張來武. 論創新驅動發展[J]. 中國軟科學, 2013(1):1-5.
[16]黃寧燕,王培德.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制度設計思考[J]. 中國軟科學, 2013(4):60-68.
[17]魏江,李拓宇,趙雨菡. 創新驅動發展的總體格局、現實困境與政策走向[J]. 中國軟科學, 2015(5):21-30.
[18]Gordon, I.R., McCann, P.,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5(5):523-543.
[19]Rodríguez-Pose, A., Crescenzi, 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illovers,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genesis of regional growth in Europe [J]. Reg. Stud, 2008(1):51-67.
[20]Wathins, A. et al.,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intermediary rol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build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for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1407-1418.
(本文責編:辛城)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WANG Yu-min1,LIU Hai-bo2,JIN Zong-zhen2, 3,LIANG Li-he4
(1.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864,China;2.InstituteofPolicyandManagemen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90,China;3.ChinaNationalInstituteofStandardization,Beijing100191,China;4.ExchangeofDevelopmentandServiceCenterforScienceandTechnologyTalents,theMinist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100045,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he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ccomplishment the overstepping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basic issue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us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as ordinate and abscissa, the four-phase model are founded by considering the three important factors-driven objective, driven model and source of driving force. Thinking of strategy choice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re presente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some remaining obstacles, which have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four-phase model, strategy choice;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ration
中圖分類號:G3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6)04-0001-12
作者簡介:王玉民(1938-),男,河北豐潤人,中科院研究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研究方向:戰略管理與科技政策。
收稿日期:2016-03-02修回日期:2016-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