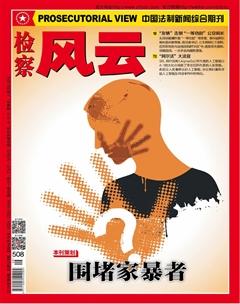錯案追責的法文化智慧
倪鐵,《青少年犯罪問題》雜志主編、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牛津大學法外治理中心兼職研究員、英國利茲大學客座研究員
隨著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的實施,司法改革的步伐越邁越大,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陸續推出了各自與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中央政法委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針對執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性規定,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但是,與公平正義、自由權利等司法追求的應然理想狀態不同,制度實踐中的冤案一直是司法揮之不去的夢魘——它使無辜者遭難、罪人逍遙、正義蒙塵,侵蝕著民眾對法律權威的信仰。“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們在媒體輿論中不時閃現,而最近亦不乏被業界熱議的呼格吉勒圖案和陳滿案,“冤假錯案”拷問著中國刑事司法體系的權威和公正。
錯案治理與追責機制
剝離那些看上去、聽上去高大崔嵬的司法公正夢想,我們發現:古今中外,任何一國的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杜絕錯案的發生。特定時期的犯罪行為人反偵查能力、司法人員認知能力、犯罪現場條件、法律規則、時限規定、刑事司法人員偏私枉法等因素,或刑求逼供、或湮滅證據、或錯捕人犯、或事實重構謬誤,最終鑄成錯案。
當前,針對刑事司法過程中的冤假錯案,主要是通過對公檢法三家具體辦案人員的錯案終身追責機制來進行。為了配合錯案終身追責機制的運作,還同時建立健全合議庭、獨任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明確冤假錯案標準、糾錯啟動主體和程序。針對冤假錯案的重要源頭——違法偵查、違法取證進行重點治理。對偵查程序運作的合法性和證據合法性的強調固然值得學界和實務界額手稱慶,但對于錯案責任追究提出的“終身追責”機制卻令不少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他們擔心在審委會、檢委會仍集體討論定案的當下,錯案終身追責能否與之切合,能否真正實現權責一致。
在傳統中國,雖然法律并沒有以刑事錯案治理為中心進行獨立篇章的制度設計,也沒有形成以刑事錯案治理為核心的系統體制,但是當我們透過紛繁的律法典籍、冤假錯案的治理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錯案治理法文化邏輯主線——針對刑事司法人員、當事人等的不同對象治理相結合,預防與懲戒相結合,并貫穿于主體適格、如實控告、及時偵審、依法調查、嚴懲違制等一系列刑事錯案治理機制中。
追究司法官員瀆職責任
中國刑事司法人員較早地擺脫了對神明裁判的盲目依賴,很早就關注犯罪現場所留之“形跡”。傳統偵查活動要求官吏在犯罪現場勘查必須做到迅速及時、客觀真實、細致全面,并且在現場勘查活動中做到權力節制。作為一項專門性的刑事調查活動,刑事司法權都是由官方壟斷的,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各級官吏、佐雜等人員才有權進行犯罪現場勘查。秦時的現場勘查往往由基層縣丞、令史、隸臣妾等負責實施。在遇到專門問題時,由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參加現場勘驗和檢查,如涉及流產的犯罪現場要由隸妾參加勘查。宋之后的現場勘查主體是州縣的司理參軍、縣令、縣尉、縣簿、縣丞、巡檢、都巡檢,還包括執行具體操作任務的仵作、手力、伍人等勘查人員。主官進行具體勘驗活動時,有權指揮仵作、手力、伍人具體實施。
為了防止佐雜官吏非違行為造成冤濫,宋以后的法律要求負有勘查之職的正印官必須親臨犯罪現場,主持勘驗檢查活動。宋朝法律明確規定了正印官必須親臨殺傷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現場進行勘查,受差驗尸的官員不得借故推諉。明清時期,重大疑難案件的現場勘查也由正印官帶刑書、仵作,立即親往勘驗。
傳統法律對刑事司法人員“檢驗不實”的違法行為設定了嚴厲的制裁機制。《唐律疏議》規定,對不實現場勘驗檢查行為區別故意和過失,并根據“實病死及傷”與“檢驗所得”之間的誤差,分別定罪處刑。宋時的規定較有代表性:負有現場勘驗檢查之責的驗官“不親臨視”犯罪現場的,“以違制論”。《宋刑統》沿襲了這一如實檢驗的責任規定,并具體化為:“檢驗不實同詐妄,減一等,杖九十。”《大清律例》規定:“不為用心檢驗,移易輕重、增減尸傷、不實定執、致死根因不明”,不同官吏分別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正官杖六十”,“首領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伍人”檢驗不實的,“罪亦如之。”清代強行要求州縣官親臨犯罪現場勘查,“不親臨(尸所)監視,轉委吏卒(憑臆增減傷痕),若初(檢與)復檢官吏相見扶同尸狀”,“正官杖六十,(同檢)首領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絕大多數正印官能夠依據“情”“理”“法”來偵審刑事案件,有力地壓縮了刑事錯案的空間。
追究現場保護不力的責任
在犯罪現場能夠提取到物證、書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等多種證據,它們能為重建犯罪提供第一手信息和線索。但犯罪現場又具有變動性,容易受到自然界、人為等多種因素影響而變化,必須在勘查進行前和進行中盡可能地保持犯罪現場原貌。秦朝已要求對犯罪現場進行“封守”,其實質上就是犯罪現場保護,該任務由典史、公士、里人等共同承擔。相關人員必須“以律封守”,嚴格劃定“當封者”的范圍,并執行相關的“封具”法律。犯罪現場保護的撤除,須由主司下令,不可隨意撤除保護。按宋時法律要求“血屬、耆正副、鄰人”保護犯罪現場中發現的尸體,“復檢官驗訖,如無爭論,方可給尸與親屬。無親屬者,責付本都埋瘞,勒令看守,不得火化及散落。”
傳統法律都要求官民保護犯罪現場,并對現場保護不力的相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秦時,對于“有它當封守而某等脫弗占書”的失職行為,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清朝規定,保護命案犯罪現場的“里長地鄰”,若將尸體“移他處及埋藏”,處以杖八十的刑罰。同時清朝法律規定:“凡五城遇有命案”,“金刃、自戕、投井、投繯等案”,必須進行現場勘查,“令該城指揮照例驗報,由該城御史審訊,轉報刑部核覆審結。”若刑事司法人員漏檢這些必須勘查的案件,法律要求“將該城官員指名參處”。 對重案疑案犯罪現場進行強制性勘查,可以有效地制止民間私和,也可以限制各級刑事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防止不法官吏上下其手、放縱犯罪、炮制冤獄,有利于勾連犯罪線索,佐證刑事案件偵審的正確方向,確保國家刑罰權的有效實現。
追究偵查延宕違限的責任
同其他刑事司法行為一樣,現場勘查這種綜合性偵查措施也必須遵循迅速及時的運作原則。歷朝法律都強調現場勘查措施的及時性,并為之設置了一系列時限制度。唐時對拷問死人犯的現場,要求有關官吏立即對拷問現場進行勘查。《唐律疏議》“拷囚不得過三度”條對“依法拷決,而邂逅致死”的現場勘查做出了規范,要求“長官以下,并親自檢勘”,“若長官等不即勘檢者,杖六十”。
宋之后的中國傳統法律對命案現場勘查做出了具體時限規定。南宋律法要求勘查官吏接到驗尸公文牒后,必須在兩個時辰內出發,若“受差過兩時不發,遇夜不計……各以違制論”。一旦獲知犯罪,法司官吏應“一面差拘兇首,勿使疏脫,一面傳集仵作刑書,單騎簡從,親經相驗”。現場勘查結束后,應“當日內申所屬”檢驗結果于驗尸當日向上司匯報。
在勘查時限責任制度中,以《大清律例》的相關規定最具代表性:“凡(官司初)檢驗尸傷,若(承委)牒到托故(遷延)不即檢驗致令尸變;……正官杖六十,(同檢)首領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通過懲治現場勘查官吏違反時限的非法行為,以防“為時愈久,滋弊愈多,死骨有蒸刷之慘,生命含覆盆之冤”。
以史為鑒
雖然,傳統中國在治理刑事錯案過程中,存在著“國家本位主義”“民刑不分”“等級身份色彩濃烈”等中華法系固有的局限,但是,為了防止案件偵審走入歧途,不同時期的中國法律也都規定了一系列犯罪現場勘查制度,并體現出了較為鮮明的刑事錯案治理法文化智慧:其一,針對不同群體采用不同法律規范。既治理正印官不親臨犯罪現場勘驗檢查的違法行為,也治理報案人不如實報案的“不實告”行為。其二,預防與懲戒相結合。中國傳統法律為犯罪現場勘查規定了較為發達的一系列機制,既設定了正印官親臨犯罪現場檢驗、如實報案、現場保護、及時勘查、全面勘查等機制,也設定了相應懲戒機制,包括:懲戒勘查主體不適格,打擊報案不實告,懲治勘查拖延推諉、嚴控勘查權肆意濫用、嚴懲勘查錯漏詐偽等治理機制。其三,民事補償、行政懲戒與刑事處罰相結合。如《大清律例》要求誣告者對被誣者財產性損失進行補償。對于違反現場勘查規則的違法行為,既有“指名參處”“ 稽查參奏”“交部議處”等行政懲戒治理方式,也有“杖”“徒”等刑事處罰治理方式。這些隱現于傳統中國豐富的律法典章和偵審實踐中的法文化,既是千百年來中國刑事司法實踐的經驗積累,也凝集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智慧的結晶,帶有相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即使是在現今刑事司法活動中仍有值得借鑒的價值。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