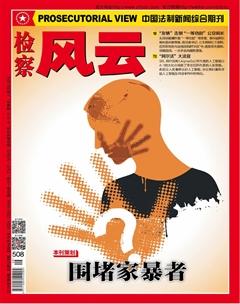官員讀書是好事
廖保平
近日,中央批準李書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員、常委和市紀委書記。這本是一個很正常的調整,卻引發了熱議。原因在于,李書磊一度被傳說為中央文膽,其傳奇經歷亦吸引眼球:李書磊14歲考上北大,被喻為“神童”,44歲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后又擔任福建省宣傳部長等職務。同時,李書磊是文化評論界的知名學者,曾出版《為什么遠行》《雜覽主義》《重讀古典》和《文學的文化含義》等專著、論文集及隨筆集,產生了較大反響。
我從網上找了一些李書磊寫的文章來讀,且不論思想如何,單是就文字而言,確實老道醇厚、有味耐嚼。我所佩服的文章大家余世存先生竟說,李書磊對他的寫作產生過影響,李書磊的不少篇章給他留下了印象,這不能不令筆者對李書磊刮目相看。
事實上,即便當今官場,做官而文章做得好的也不少,這不包括文聯作協那些“文藝官”,單以政府機關論,早些年就有山西省作家張平當選為山西省政府副省長,而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更是憑借詩集拿了魯迅文學獎。
現在,一些讀書人、文化人當官,不過是傳統遺風,正如李書磊在一篇舊作《宦讀人生》中所說,“古時候學而優則仕,做官的都是讀詩書的人”。是的,在過去,科舉制度不就是要選拔讀書人、文化人、作家去當官么?孔夫子說這叫做學而優則仕。要是文人墨客喝了一肚子的墨水,學成了文(武)藝,不賣與帝王家,那一輩子就差不多顆粒無收,抬不起頭來了。因此,無論自己的詩文如何了得,也要削尖了腦袋往仕途上沖(連李白都沖,誰不愿沖?),哪怕熬得頭發胡子都白了的范進,一舉中榜也是十分了得的。
所以,讀書人做官本無可厚非,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就算文盲當官也不應該大驚小怪。有文化背景的官員并不一定就有人文關懷,關懷與不關懷,要以人民的需求為準。
正如李書磊所說:“做官實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種復雜而危險的人際糾葛之中,往往是整日憂慮,滿心煩惱。”而人的時間精力總是有限的,魚和熊掌總是不可兼得。于是我們看到,很多讀書人、文化人做官后,今天要辦公務,明天要出席會議,后天要發言,大后天要剪彩……“日理萬機”的匆忙,哪里有時間精力讀書?
想當初,蘇東坡、白居易寫出傳世佳作,并非在朝廷為官之際,而是被貶之時。李書磊在《宦讀人生》中提到做官做得好,讀書也讀得好,且能留下文字財富的模范曾國藩,但這樣的人畢竟少數。讀書確實需要能靜下心來,如果還想寫出點有價值的文字,而不是秘書代筆的公文,更需要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寂寞。
不說官場里的欲望一定會吞噬一個人的心靈,但“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閱人最多的職業了”,用李書磊的話說,做官是一種大俗,讀書是一種大雅。從俗的、做官的立場上來看,這大雅對大俗是一種拯救;而從雅的、讀書的立場上來看,這大俗對大雅又是一種成就。
只是李書磊忘記了一點,人都是經濟理性動物,如果讀書是做官的敲門磚,一定有人要拼命讀書,可是一旦做了官之后,正是前期的努力讀書現在有回報的時候,他不將時間精力用在創造投資收益上,而是繼續苦讀,甚至因這樣的讀書而影響投資收益,他何苦來哉!
此時讀書想來各有所需,但“文恬武嬉,玩物喪志”,無論怎樣,讀書本身并不是什么壞事。應該鼓勵官員多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出得官場,入得書房。總比沉湎花天酒地,縱情聲色犬馬要好。習近平總書記曾諄諄告誡領導干部,“少一點應酬,多用一些時間靜心讀書、靜心思考”,這應該成為官員的座右銘。倘若在向學問道的過程中有所收獲,修身養性,并且還有益于治國安邦,那就再好不過。
圖:王恒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