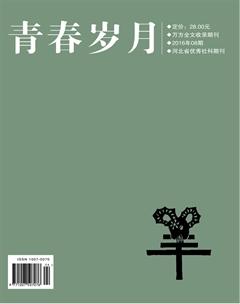論《燦爛千陽》中的生態女權主義
張海寧 李珊珊 黃亞超
【摘要】本文主要就文學作品《燦爛千陽》中的生態女權主義進行討論,具體介紹了作品《燦爛千陽》中自然與女性的特征,解讀了其中所體現的生態女權主義,并對自然與女性的和諧關系進行了深刻分析。
【關鍵詞】生態女權主義;自然;女性;《燦爛千陽》
對于《燦爛千陽》這一部優秀作品,我國學術界對該作品的研究更多的停留在人物塑造、表達技巧、人文主義、語言構思等方面,對于作品中展現的生態女權主義還沒有進行太多的探究。所以,筆者通過此文對《燦爛千陽》中的生態女權主義進行分析討論,以豐富該作品在我國的研究層次。
一、《燦爛千陽》中的自然與女性
《燦爛千陽》中體現的生態女權主義在很多情節中都反映了,女性和自然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女性天生就對自然有著一種超乎尋常的親近感。兩者同樣都是生命的孕育者,大自然賦予世間萬物以生命,我們一直稱其為“自然母親”,這與女性孕育、哺育生命的偉大形象重合;而女性性格中的善良、包容、溫柔等品格同樣也與大自然的特征相符,這種存在于女性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使兩者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甚至達到了休戚與共的親密程度。小說的兩位女主——瑪麗雅姆和萊拉,就是女性和自然相互認同,高度吻合的真實寫照。
以瑪麗雅姆為例,她是阿富汗富商和仆人所生的私生女,不受法律保護、不被社會認可,而這種排擠讓瑪麗雅姆與自然高度融合,她出生的地方山水清澈、鮮花遍野、綠草如茵、樹木高挺,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瑪麗雅母不斷成長,使她擁有了跟自然一樣純潔、善良、寬容、仁厚、感恩的品格。幼年時期她在山中小屋中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父親的偶爾到來也讓她倍感欣喜此時正如春天般讓人充滿希望;青年時期她跑去見父親,搬去與父親同住并沒有遭受到母親所說的排擠和厭惡,是她人生中短暫的夏日時光。之后母親自盡,她在父親和繼母的安排下嫁給了大她二十多歲的鞋匠,從此生活的悲劇拉開序幕,人生進入秋季,隨著一次次的流產,在失去生育能力后,她承受著丈夫無盡的謾罵和拳腳相踢,在最后的反抗中保護了萊拉殺死了自己的丈夫,生命以嚴冬結束。
二、《燦爛千陽》中的生態女權主義解讀
1、被父權壓迫的女性
生態女權主義堅決反對以父權為中心對自然和女性實施的雙重壓迫,并深刻的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父權中心主義。在胡賽尼的小說《燦爛千陽》中,瑪麗雅母和萊拉都是深受父權壓迫的女性代表。瑪麗雅母的父親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并擺脫累贅,將女兒嫁給了跟他年齡相仿的男人拉希德,親手將女兒推入了不幸的深淵,而像這樣的例子在阿富汗絕對不是少數。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還體現當瑪麗雅母嫁給拉希德后完全成為了丈夫的服侍者、附屬品,甚至是奴隸,按照丈夫的要求她每天全身上下包裹著布卡,不能與任何人來往,更在失去生育能力后遭受了丈夫無盡的謾罵和隨時的暴力相向,被徹底淪為了父權壓迫的犧牲品。同樣在萊拉為拉希德生下女兒而不是兒子后,遭受了與瑪麗雅母同樣的家庭暴力,相比于丈夫的冷酷無情更讓她們絕望的是統治時代廢除了女性權利,政府和父權制的狼狽為奸共同摧殘著女性的肉體和心靈。
2、被父權迫害的自然
在小說中,父權制對自然的迫害體現在人類對生靈和環境的破壞,父權主義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征服欲和占有欲,頻繁的發動戰爭,對自己的同胞進行屠殺。小說中萊拉在戰爭中失去父母、哥哥和愛人,在欺騙中被迫嫁給了拉希德從此只能在父權制的壓迫下苦苦掙扎。戰爭帶來的災難使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孩子們變成孤兒,士兵甚至將普通百姓當作練習槍法的靶子,動物和植物的生命便更不值一提,大街上遍地的動物尸體、樹木被戰火燒毀、房屋建筑被毀壞、水源也被污染。父權制下自然一直被視為征服統治的對象,讓美麗的大自然遭到了破壞和踐踏。
3、女性主義的覺醒
《燦爛千陽》中,兩位女性瑪麗雅母和萊拉的覺醒反映了女性主義的覺醒。萊拉和瑪麗雅母在同樣的生活處境中建立了深厚感情,并逐漸在此基礎上認識到反抗的必要性。萊拉的覺醒表現為她沒有一味地選擇忍耐,為了孩子和自己勇敢地對拉希德進行反抗,并創造機會進行逃跑。瑪麗雅母的覺醒是在保護萊拉和孩子時產生的,她用鐵鍬殺死了拉希德,雖然接受了制裁,但為孩子們和萊拉帶來了重生。總結小說中體現的生態女權主義,只有女性和男性擁有同等的精神和物質對待時,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和生態的平衡。
三、《燦爛千陽》中自然與女性的和諧關系
女性生態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之間有著神奇的默契,她們同樣肩負著孕育、滋養生命的神圣職責,女性與自然在內在聯系和相似之處,是她們本能的產生親近感,并能長久的和諧相處。小說中瑪麗雅母悲慘的人生總能在大自然中尋求到安慰,在于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讓她真正的體驗到幸福和快樂,自然與她而言是精神的寄托和心靈上的慰藉。而對于萊拉而言,自然則象征著幸福安寧的生活,戰爭開始前她與父親經常到郊外感受大自然的美麗,那是她人生中最平靜、快樂的時光,自然賦予的滿足讓萊拉對自然充滿熱愛和尊重。作者借助《燦爛千陽》表達了女性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并告誡人們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 楊彥清. 對胡賽尼的《燦爛千陽》的女性主義解讀[J]. 渭南師范學院學報, 2011(07).
[2] 尚必武, 劉愛萍. 托起“燦爛千陽”的“追風箏的人”——阿富汗裔美國小說家卡勒德·胡賽尼其人其作[J]. 外國文學動態,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