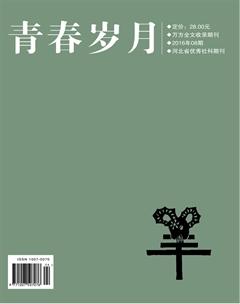從“種子移植”看《長干行》英譯
【摘要】詩歌是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譯詩之難,已是翻譯家們的共識。蘇珊·巴斯內特針對詩歌翻譯創造性德提出了“種子移植”理論,本文將結合該理論對比分析龐德和許淵沖對李白詩歌《長干行》的翻譯,并分析造成不同翻譯取向的深層原因,探討各自翻譯的優劣得失,進而為中國古詩英譯提供一些啟發。
【關鍵詞】種子移植;《長干行》;龐德;許淵沖;詩歌翻譯:對比研究
詩歌是是語言藝術的最高形式。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詩歌具有獨特的語言和形式。詩歌的獨特性,決定了譯詩之難。因為在詩歌翻譯時不僅涉及到將原詩的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還涉及到形式、音律、意象、情志等要素的轉化。由于不同語言文化存在很大的差異性,譯者在翻譯詩歌時很難把詩歌各要素完整地再現到另一種語言文化中,在詩歌翻譯實踐中,往往顧此失彼。鑒于此,美國詩人羅伯特·L·弗洛斯特也感嘆:“詩者,譯之所失也”(Poetry is w 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然而,有失必有得,蘇珊·巴斯內特創造性地提出了“種子移植”理論,她認為“詩者,譯之非所失也;詩者,恰為譯之所得也”。本文擬以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為基礎,通過對比分析《長干行》龐德和許淵沖的英譯本,探討二者在翻譯過程中各自采用的策略及產生的效果,挖掘深層次的理論機制,從而為歸納出幾點中詩英譯的啟發。
一、“種子移植”論
蘇珊·巴斯內特是英國著名的作家和翻譯理論家。1998年她與勒菲弗爾合作出版了《文化建構——文學翻譯論集》一書,巴斯奈特在該書的《種子移植:詩歌與翻譯》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她關于詩歌翻譯的見解。在文章一開始,她先批判了弗洛斯特“詩,譯之所失也”的觀點,認為這是極其愚蠢的論斷(immensely silly remark)。巴斯奈特認為這一論斷所包含的詩歌不可譯的主張是不足為道的。巴斯內特又引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P.B.Shelley)在其《詩辯》(1IIe Defense of Poesy)中的一段話:“要想把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輸入到另一種語言,就像把紫羅蘭投入坩鍋以探索其色澤和香味的構成原理一樣是不明智的。植物必須由種子中抽出新芽,否則它就不會開花——這都是巴別塔惹的麻煩。”巴斯奈特從新的視角解讀這段話,創造性地提出了“種子移植”的詩歌翻譯理念。巴斯奈特認為:作為“種子”的詩歌雖然不能從一種語言完整地再現到另一種語言,但卻可以移植。種子可以帶入新的土壤,在新土壤中會生長出新的植物。譯者的任務就是選擇在什么地方放入什么樣的種子并著手種子移植工作。在巴斯內特看來,詩歌不是在翻譯中失去,而是在翻譯中重生。這體現的是一種創造性地翻譯觀。本文將以“種子移植”為理論基礎,探討《長干行》兩譯本在不同程度上體現的這一“移植”觀念。
二、龐德和許淵沖其人及思想
艾茲拉·龐德是英美20世紀文壇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雖然不懂漢語,但他根據費諾羅薩的留下的手稿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和儒家經典,后出版詩集《華夏集》(也譯為《神州集》)。他的翻譯,不僅很好地譯介和傳播了中國文化,同時他也積極從中國古典詩詞和日本俳句中汲取靈感,開創了英語詩歌的新流派“意象派”。作為一名翻譯家,龐德也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的翻譯理論,尤尼·阿帕特(Ronnie Apter)在其著作《挖寶:龐德之后的翻譯》中對這些理論做了總結。他指出,龐德的采用的是一種“創意翻譯法”,主要體現三個方面:“1、拋棄維多利亞時期那種矯揉造作、生僻古澀的翻譯措辭;2、優秀的詩歌譯作可以看作是具有自身獨立意義的新詩作品;3、每篇譯作都有必要看成是一定程度對原作的評鑒。”第一方面主要是指用詞方面,龐德一般選取的都是比較生活化的詞。第二方面是龐德翻譯思想的核心,他強調的是譯者的主體性,龐德認為翻譯是一種改寫,在龐德的看來譯詩不應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重點傳達原詩的情感。這也是和蘇珊·巴斯內特所提出的“種子移植”理論是相吻合的。二者都強調發揮譯者的主體性,讓譯詩能夠在譯文文化的土壤中得到重生。
許淵沖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從事文學翻譯長達六十余年,譯作涵蓋中、英、法等語種,翻譯集中在中國古詩英譯,被譽為詩譯英法唯一人。出版的譯作有六十本余種,包括《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除了譯作等身,許先生在翻譯理論上也卓有成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翻譯理論體系。許淵沖的翻譯思想集中收錄在《翻譯的藝術》、《文學與翻譯》等書中。主要是有三個三論:三美論,即意美、音美、形美;三化論,即淺化、等化、深化;三之論,知之、好之、樂之。許淵沖先生在翻譯毛澤東的詩詞時提出:“要傳達意美,可以選擇和原文意似的絕妙好詞,可以借用英美詩人喜聞樂見的詞匯,可以借助音美、形美來表達原文的意美。要傳達音美,可以借用英美詩人喜見樂用的格律,選擇和原文音似的韻腳,還可以借助于雙聲、疊韻、重復等方法來表達原文的音美。要傳達形美,主要是在句子長短方面和對仗工整方面,盡量做到形似。”在“三美”原則中,許淵沖先生“重要的是意美,其次是音美,再其次是形美”。同時,他認為“有人說詩就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而我認為譯詩有得有失。如果‘所得大于‘所失,那就不能說譯詩得不償失;如果‘所創大于‘所失,那就可以說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由此可見,許淵沖先生主張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創造性地對詩歌進行“種子移植”。
三、“長干行”龐德和許淵沖量英譯本對比分析
《長干行》是李白的一首閨怨詩,該時以一位閨中女子回憶寫起,表達對遠行丈夫的深切思戀。龐德和許淵沖這兩位譯者由于所處文化背景及翻譯理論的不同采取了差異化的翻譯方式。本文將選取標題和有代表性的后四句來做分析。
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
龐譯: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許譯:The yellow butterflies in autumn pass,Two by two oer our western-garden grass。
“蝴蝶”這個意象一出現在中國人的面前,大家都會聯想到一個經典的愛情故事《梁山伯與祝英臺》,梁山伯與祝英臺生不能相愛,死后化成蝴蝶出雙入對,相愛到永遠。龐譯的“paired butterflies”和許譯的“two by two”都譯出了這一意象,各有千秋。
在原詩中,“蝴蝶黃”中的“黃”字是動詞,拋開上述時間錯位的翻譯不論,龐譯“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在試圖闡釋時令變化與蝴蝶變黃間的關系。許譯直接翻譯成“yellow butterflies”。兩者相較,龐詩更譯出“蝶因時黃,人因時老,蝶可雙飛,惟我孤身”的這種孤寂之感。
龐譯把“八月”翻譯成“august”,初看之下是與原文對等,但是譯者忽視了一個問題:中國古代歷法與現代西方現代歷法是有區別的。古代中國采用陰歷,“八月”在古代稱“仲秋”,如果用現代西方的陽歷來翻譯把八月翻譯成“august”,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的是“盛夏”和“酷暑”。表面上的忠實,實則是意義上的偏離和不對等。而許譯翻譯成“autumn”,充分理解了這一時間概念的深層含義。
“西園”,這和古代的建筑布局有關,北屋(坐南朝北)是主屋,通常住家長,東邊住兒子,西邊住女兒,旁邊通常會辟出一塊院子做綠化。在古代文化中,去西園和小姐們幽會是一個千年話題,所以有關愛情、思念或是失戀的怨念往往會有西園一詞的出現,這是一種固定的“意象”。比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龐德翻譯大寫,表具體地名。許淵沖小寫,泛指西部方位的一個院子。許淵沖的理解更正確。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龐譯:They hurt me。I grow older。
許譯:The sight would break my heart,and Im afraid。Sitting alone,my rosy cheeks would fade。
龐德在翻譯這兩行時,僅僅使用了簡單基礎的詞匯來描寫妻子在丈夫離家后的悲痛及感傷之情。“They hurt me。I grow older。”這是在原文基礎上的創譯,得其神而忘其形。從這句可以看出龐德不拘泥于原文的具體詞句,而是在原文基礎上的改寫。這受到他的翻譯觀的影響。
許譯無論是押韻的角度看都處理得更恰當。“紅顏”指“年輕女子的容顏”,翻譯“rosy cheeks”,形象貼切。“afraid”和“fade”押韻。這是這里有一個誤譯,“坐”我查了漢典,在古詩詞中可做副詞,“深,非常”的意思。而不是許淵沖的“sitting alone”。所以從這個層面講,許淵沖先生也沒有完全忠實于原文。語言風格上,龐譯口語色彩更濃,更接近于敘述性的散文,正如龐譯標題“a letter”。而許譯韻律感更強。
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龐譯: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
許譯:Sooner or later,youll leave the western land。Do not forget to let me know beforehand。
“三巴”,地名,指巴郡、巴東、巴西,均在今四川省東部,相當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東的大部。早晚下三巴,“三巴”是男主人公回家必經的路,也籠統地代指家的方位。“三巴”龐譯為“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narrows”牛津字典解釋為:“a narrow channel that connects two larger areas of water”。“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泛指長江上的大小峽谷,龐譯體現出夫君歸途之艱難以及女子對丈夫的擔憂。而許譯把“下三巴”處理為“leave the western land”,避開“三巴”不譯,而談夫君離開之地“西部”,更多得傳達的是一種期盼夫君早日歸來的迫切心情。
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龐譯: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As far as Cho-fu-Sa。
許譯:I will walk to meet you and not call it far,To go to Long Wind Sands or where you are。
“長風沙”長風沙在今安徽安慶市東長江邊上,離開今天的南京已經有數百里之遙。商婦實際上不可能真到那么遠去迎接丈夫,但這樣的夸張對于表現她此時此刻的心情是十分有力的。詩人寫出了女子對于會面的渴望,對于丈夫熱烈的愛,寫出了蘊蓄在她心底的奔放的熱情。龐譯采用音譯的方法,把“長風沙”翻譯成“Cho-fu-Sa”。龐譯詩的人名地名譯音來自日文,這點不足取,應該“名從主人”。許淵沖采取與“長干里”相似的譯法,把地名逐字意譯,首字母大寫,使讀者很容易辨別出地名。讀者借助“not call it far”、“where you are”等語句能夠推測出該地離家很遠,從而理解少妻盼夫歸的心情。
四、總結
綜上所述,盡管龐德和許淵沖在對《長干行》進行“種子移植”的時候,都發揮了譯者的主體性,進行了創造性地翻譯。但由于兩者由于生活背景不同,受到的教育及翻譯目的的不同,兩人有著各自不同的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在策略方面,盡管兩者都注重意象的表現,但龐德在具體的翻譯中大多采取異的翻譯手段,而許淵沖則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同時,兩者的“改寫”也有不同,龐德的改寫是通過對于意象的重新選擇實現的,而許淵沖則是采取意象轉換的方式來達到自身的翻譯目的。在詩歌韻律上,龐德采用的是無韻詩、自由體的形式,而許淵沖先生翻譯過程中基本上保留了原詩的節奏和音律。總之二者都實現了詩歌翻譯“種子移植”。
【參考文獻】
[1] Susan Bassett, Andre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 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1.
[2] Apter, Ronnie. Digging for the Treasure: Translation after Pound [M]. New York: P.Lang, 1987.
[3] 許淵沖. 意美、音美、形美——如何譯毛主席詩詞[J].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79.
[4] 許淵沖. 翻譯六論[M].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1.
【作者簡介】
李小瑩(1991—),女,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學與比較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