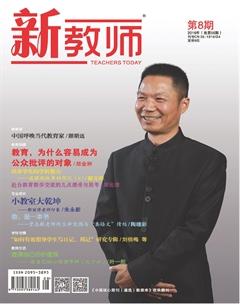擠出空隙,走出盲點
陳六一
很多時候,學生的課堂生成與教師的預設發生矛盾,往往是由于學生存在著概念空隙與認知盲點所引起。換句話說,課堂中,師生需要通過最近發展區的互動,將新知同化到自己已有的知識結構中去,或將原有的知識結構進行重新組合,舊知順應新知,才能達成數學實現。
一、尋找邏輯與概念間的空隙
【教學片段1】感知一億。
師:同學們,剛才的故事中提到了一億粒米,(板書:100000000)一億,看到這個數你有什么感覺?你能描述一下一億有多大嗎?
生:1億相當于10個一千萬。
生:1億相當于100個一百萬。
生:1億就是100000000個一。
師:看來大家對一億已經有些了解了,那同學們猜一猜,數一億粒大米可能需要多長時間?
生:30分鐘。
生:也許3個小時。
生:我想可能需要3天吧。
【賞析】
柯老師的問題一經提出,學生便接力賽似的答著:“一億相當于10個一千萬。”“一億相當于100個一百萬。”“一億就是100000000個一。”似乎學生對一億的大小挺有感覺,可當柯老師接著詢問:“同學們猜一猜,數一億粒大米可能需要多長時間?”學生對一億的“無知”,一下便暴露了。原來,學生不會把數學知識拉到自己身邊,一億的“邏輯”與一億的“概念”便產生了空隙。
兒童的概念主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抽象化階段,兒童對有關對象確認出某種屬性;二是類化階段,兒童對這些屬性進一步抽象,只考慮屬性的相似性,忽略其他屬性的差異性;三是辨別階段,兒童不僅認同共同屬性,同時還能區分不同屬性,初步形成分類能力。為了填補“一億多大”的“概念空隙”,幫助學生一步步豐盈表征,使得抽象的數字形象化,形象的情景抽象化,終而識別“一億多大”。所以在接下來的課堂教學中,柯老師組織下列活動便成了必然:第一步,數100粒大米,再根據數100粒大米用的時間,推算出數一億粒大米要多久;如“教學片段2”。第二步,轉化數一億粒大米的秒數為天數、年數,如“教學片段3”。第三步,先稱出100粒大米有多重,再推算出一億粒大米的重量。以及第四步,課堂現場捕捉學生“數一億”的素材,開展“數一億本數學書有多厚”“數一億枚硬幣疊起來有多厚”“一億個同學手拉手有多長”等研究。
二、順應已知與新知間的落差
【教學片段2】聚焦于數。
師:老師欣賞你們的大膽猜測,不過這樣的猜測缺乏依據。那我們有什么辦法能比較確切地知道數一億粒大米要多長時間呢?
生:數一數并計時。
師:不錯,實踐出真知。不過根據同學們剛才的猜測,數一億粒米需要的時間可不少啊!那我們這節課都用來數大米嗎?
學生搖頭。
師:是的,這可不行啊,那我們該怎么數呢?
生:先看看數100粒大米要多長時間,再根據數100粒大米用的時間,推算出數一億粒大米要多久。
師:哦,推算,聽上去是個好方法,你準備怎么推算?
生:知道了數100粒米的時間,就可以先推算出數1000粒米的時間,再推算出數10000粒……10000000粒米的時間,最后推算出數一億粒米的時間。
【賞析】
學生并非帶著空空的腦袋走進課堂,即使將要學習的內容他們聞所未聞,但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總有過去的解題方法、數學經驗、思維策略等,悄然影響著新課的學習。建構主義指出:對數學問題的理解,是一個以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為基礎的建構過程。
學生的這些數學現實是繼續學習的基點,但也是繼續學習的障礙。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過在一個單位時間里數多少東西的經驗,于是四年級的學生自然會生出這樣的思考路徑:“可以先看1分鐘數多少粒大米,然后再算數1億粒大米需要多少時間。”這種思維不但不是本節課將要學習的知識點,反而干擾了學生對新方法的習得。本節課的主旨應是掌握“先數100粒米,利用數100粒米的時間推算出數100000000粒米的時間。”其實在教學前測與第一次磨課中,學生的第一反應都是前述思維策略,可見,教材的主旨思維是學生的盲點。
因此,教學中,柯老師針對“怎么幫助學生快速聯想到先數100粒米”這一數學現實中的盲點,著力組織了兩個問題:“數一億粒米需要的時間可不少啊!那我們這節課都用來數大米嗎?”和“那我們該怎么數呢?”這樣把思維的重心聚焦在“怎么數”上,而不是算時間來完成題目,于是學生的正確推理得以實現。“教學片段3”的教學也就從“實然”狀態趨向了“應然”結果。
【教學片段3】推理。
師:依我們班數得最快的速度計算,數1000粒大米要480秒,怎么想的?
生:1000粒是10個100粒,也就是要數10個48秒。
師:照這樣推算,(板書:推算)數10000粒呢?
生:4800秒。
師:好,剩下的請同學來推算,誰的小手舉得最快,老師就喊誰回答。
生1:48000秒。
生2:480000秒。
生3:4800000秒。
生4:48000000秒。
教師依次板書學生反饋的時間。
師:原來數一億粒大米要48000000秒!剛才這位同學猜測數一億粒大米可能需要3天,那我們就來計算一下數一億粒大米到底要多少天?
生5:先把秒變成分,再把分變成時,接著把時變成天。
生6:48000000÷60=800000分。
生7:60分鐘就是1小時,看800000分里有多少個60分,就是800000÷60約等于13333時。
生8:因為一天有24小時,13333÷24約等于556天。
師:556天大約是多少年?
生:差不多1年半。
師:原來照剛才那樣的速度,數一億粒大米不吃不睡大約要1年半啊!同學們,現在想一想老師能給大家帶來一億粒大米嗎?為什么?誰愿意幫老師做一下解釋?
三、搭建空隙與盲點間的腳手架
蘇聯教育家維果茨基提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為數學教師的問題設計提供了路徑:啟發時,我們問得太難,學生會感到局促茫然;問得簡單,則又挫傷了學生挑戰的欲望。其實,課堂中我們也時常發現,如果一節課順風順水,學生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所有的課堂問題,貌似掌握了課堂知識,實質上這節課的教學對于學生思維品質的提升幾乎沒有幫助。只有一路磕磕絆絆,看似全明白了,但一深究,卻漏洞百出,學生再千方百計自圓其說或者自我否定,才能收獲真正的成長。
比照理論,回頭審視“教學片段3”的教學過程,柯老師提供的“腳手架”具有空間彈性,加之讓學生對比自己本有的“30分鐘”“3個小時”“3個月”的原始起點,使得學生對真實的答案應該是多少產生好奇。
其實,在日常教學中,也不乏教師待學生推算出“數一億粒米需要大約48000000秒”后,會立即提出問題:“48000000秒等于多少分鐘?”隨后緊接著提問:“800000分等于多少時?”“13333時等于多少天?”
兩種教法,做了同樣數量的題目,學生思維的發展卻不一樣。讓學生計算“48000000秒等于多少分鐘?”“800000分等于多少時?”“13333時等于多少天?”之類連串的問題,學生能順勢一下子列出算式,但是“腳手架”過于短促,思維的空間就狹窄。而柯老師提出的“想不想計算一下數一億粒大米到底要多少天?”學生不能一下子列出一個具體的算式,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學生就得自己搭建一些輔助的“腳手架”,思維的空間便能得以延展。這樣的好處無疑是學生通過教師的組織,實現了基爾帕特里克的教學愿景:“問題并不是由別人給你的,因為,你必須構建出你自己的問題。”
綜上所述,教學中通過探尋學生的數學起點,及時捕捉學生的概念空隙與認知盲點,組織具備一定彈性空間的腳手架,引領學生看見思維的陽光,方是教師角色作為。
(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市陽山實驗小學校 責任編輯: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