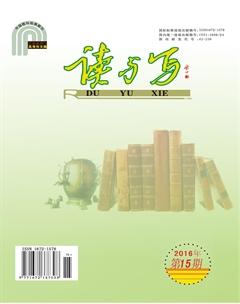生態視閾下的鄉村呈現及想象
趙亞平
摘要: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時代背景下,在精神生態的理論視域下,新時期以來的中國鄉村電影對于鄉村的書寫和想象表現為人們對精神家園的不懈追求,并且在不同時代呈現出批判和眷戀、懷念和追憶、回歸和反擊等不同的特征。
關鍵詞:新時期以來;中國鄉村電影;精神家園中圖分類號:G648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2-1578(2016)08-0004-01自中國電影誕生以來,鄉村始終是一個被關注的對象,以鄉村為敘事背景的電影不斷發展,成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一個重要類型,豐富和完善了中國電影的藝術形態。新時期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物質上的豐厚滿足卻并沒有給人們的精神世界帶來富足,反而讓人們陷入到對物質的臣服中難以自拔,人性異化、價值失衡、生存意義迷失等精神焦慮癥接踵而至,曾經鮮活的個體生命無形之中就被拋進了一個相互間情感越來越隔膜的精神荒原。現代人急需擺脫物役所累,規避情感隔膜的侵襲。而新時期以來的中國鄉村電影中對鄉村的書寫和想象,正契合了這種文化訴求,為人們找到了生命中的精神家園。本文在精神生態的視域下,試論述新時期以來中國鄉村電影中人們對精神家園的追求與想象。
1.80年代:批判和眷戀
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巨大的變化也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古老的農村。新時期的中國社會,其核心命題由政治轉向了經濟,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實現我國的現代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以"新啟蒙"為代表的意識形態成為 80 年代中國思想領域的主流,落后、保守、封建的鄉村成為被批判和急需被解放的對象。所以在這一時期的中國鄉村電影中,鄉村往往是以一副窮困蕭索的景象出現在銀幕上的,代表著傳統和愚昧。雖然此時的鄉村書寫是一個愚昧、落后的集散地,但同時也是一個人們寄予理想的田園牧歌式的所在,所以當人們在批判鄉土社會蒙昧落后的鄉土文化時,往往又流露出對質樸鄉土的迷戀。
其中謝飛導演的電影《湘女蕭蕭》對湘西山區蒙昧的封建婚俗進行了深入的批判與反思。但是謝飛在批判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同時,又基本保留了原小說對鄉土社會唯美詩意地描繪,通過一系列鏡頭導演構筑了一個民風淳厚、鄉民質樸的"世外桃源"。導演對傳統封建文化的反思無疑是深刻的,但是他對鄉土詩意地描繪又表明了他的矛盾心態。這種復雜的心態讓他在批判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同時,又夾雜對古老傳統文明的眷戀。
2.90年代:懷念和追憶
進入 90 年代,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新時期所期盼的現代化并沒有帶來想象中的一片光明,市場經濟和商品化帶來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等許多新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逐漸淡漠,現代文明帶來的人情匱乏、人性迷失、精神失落等負面影響蔓延在高樓林立的城市中。人文思想界展開對現代性的反思,呼喚重建理想信仰和價值規范。在這個時期,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懷舊思潮,迷茫失落的人們開始懷念穩定質樸、單純溫情的鄉土社會帶給人精神上的安全感,通過懷念與追憶找尋內心丟失的家園般的歸屬感。"人們開始反思自身的生存狀態,不再一味地陶醉在物質的盛宴中,而開始追尋失落的精神家園,世紀末的懷舊情緒悄然彌漫在'城市'的上空"。
90 年代的中國鄉村電影開始質疑昔日批判鄉村的啟蒙話語,反思鄉村的現代性訴求,從生態整體意識來審視鄉村,把鄉村看作生態視域下的精神家園。此時的鄉村不僅僅表現為一種鄉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而是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寄托,是現代人迷失的心靈可以詩意棲居的地方。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等電影中的鄉村都呈現了一幅詩情畫意的生態景觀,成為導演對過去懷舊和追憶的空間。在電影《那山那人那狗》之中洋溢著生態之美,父子郵路之旅充滿了親情之美、人性之美、獸性之美、風情之美。相對于《那山那人那狗》在自然之美和人文精神之美中所表達的對鄉村的崇拜,電影《暖》則在破敗的自然生態中張揚人性之美,傳達出對鄉村精神生態的向往。電影中的鄉村巧妙回避了直視現代社會的墮落,呈現了想象中鄉村的審美意境,體現真正東方以及強調了隱忍的哲學思想,使得田園牧歌般的鄉村成為電影藝術家一種有意識的追尋。
3.新世紀以來:回歸與反擊
新世紀以來,現代化的腳步進一步往前邁進。在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的同時,孕育古老傳統文化的鄉村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鄉村文明也遭受重創。在許多新生代青年導演那里城市成為被表現的中心,城市文明的表達成為許多電影的創作主旨,"鄉土"這一文化景觀在當代電影的表述中被擱置到了邊緣位置。這在一定程度上對鄉土電影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造成了電影銀幕上家園圖景的失落。但是,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人們陷入了對物質的極度追求中,隨之而來的是人情冷漠、人性迷失、價值觀錯位、道德淪喪等心理問題的加劇。現代社會的功利化和碎片化帶來了現代人精神上的無家可歸感,于是,人們渴望找一個寄托個體美好理想的地方,回歸樸實單純的理想生命狀態,而此時,溫情脈脈、至真至純的鄉土社會自然成了他們想要回歸的家園。因此,在新世紀的電影中,電影人在離開"鄉土"投進"城市"的懷抱之后,又重新選擇了歸來。
電影藝術的每一次革新都離不開技術的演進,尤其是近年來,當下社會對技術的依賴已越來越明顯,致使技術主義的橫向滲透成為電影工業化后的普遍征候。而在今天這樣一個視覺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技術與藝術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使得當代電影呈現出"泛美學"傾向,即影像修辭奇觀化、審美更為游戲化和娛樂化。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對技術的過分迷戀和依賴正在影響著當代電影的審美創作心態,有些國產影片為了吸引眼球和展示影像奇觀,盲目追求視聽震撼效果的傳達而忽略了影像的敘事合理性和文本內涵,致使故事空洞、人物形象單薄而遭觀眾的戲謔和批評。
針對技術化、數字化帶來的"泛美學"化指向,新世紀的中國鄉村電影進行了有力的反擊。郝杰《光棍兒》《美姐》對鄉村生活的生鮮展示,韓杰《hello,樹先生》對農民生存問題的關照,李睿珺《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對農民生命信仰的探討,都極其真實地展露了中國當代鄉村,平常卻深邃。楊瑾、萬瑪才旦等導演都分別從個體角度講述了屬于他們的鄉村故事。青年導演們所普遍涉及的鄉村影像讓人們看到了真正的中國鄉村,他們關于記憶時光的講述溫暖了現實中失落人們,他們對現實的魔幻表現讓我們看到了現實表達的眾多可能性。新世紀的中國鄉村電影正是以這種姿態彰顯了被遮蔽的鄉村景況,削弱了觀眾的視聽娛樂和游戲化享受,揭示了粗糲影像下的鄉村生存真相,強化了觀眾對鄉村電影文本內涵和意義的深層認同,縮短了影片故事與觀眾現實生活的距離,加深了影片的人文內涵和深度。參考文獻:
[1]李道新.《中國電影文化史》(1905-2004),[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2]曾繁仁.《當代生態美學觀的基本范疇》,[J]《文藝研究》,2007年第4期.
[3]楊遠嬰.《中國電影中的鄉土想象》,[J]《電影藝術》,2000年第1期.
[4]凌燕.《回望百年鄉村鏡像》,[J]《電影藝術》,2005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