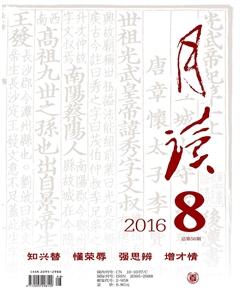學學唐僧的定力
朱華賢
五歲的外孫女愛上了《西游記》,而且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吃飯時,她一定要把那只播放著“侃叔講故事”的收音機放在旁邊,睡覺時也一定要邊聽邊睡,直到睡著為止,有時半夜起來小便后,也吵著要聽,不聽就沒法重新入睡。有時,她在做手工、搭積木或玩游戲,以為她沒聽,悄悄地把收音機關掉了,她立即就會提出抗議:“我要聽的,我要聽的!”你不得不重新開啟。有些故事,她至少聽了十遍甚至二十遍,可她還是要聽,邊聽邊學樣,邊模仿。她說自己是觀世音菩薩。聽的結果,就是對故事中的情節和人物非常熟悉,什么哪吒、紅孩兒、托塔李天王、東海龍王的來龍去脈都清楚。這樣,我就常常要她講給我們聽,她呢,好多故事都能講得頭頭是道。聽著,講著,自然就會提出一些問題:唐僧為什么要去取經呀?為什么孫悟空會變,唐僧不會變?神仙和妖怪都會變,他們有什么不一樣?等等,許多問題,我常常被問倒。
其實,我對《西游記》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比較清晰的只有“三打白骨精”了。回想一下,我大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末期讀的《西游記》,差不多有四十年了。為了避免糊弄外孫女,今年暑假,我花了一個月時間,仔仔細細地重新閱讀了一遍。這次閱讀,使我對小說中的人物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對唐僧。
在《西游記》的四個主要角色中,最被公眾看好的是孫悟空和豬八戒。孫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廣大,總是戰無不勝;豬八戒雖嘴饞貪色,但憨厚樸實、有趣可愛,是天神中的凡人;至于師父唐僧,普遍不被喜愛,主要是他人妖不分、是非顛倒,手無縛雞之力,雖然總是正襟危坐,但動不動就哭鼻子、掉眼淚。大眾的這一認識,也許是受“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情節的影響。其實,仔細閱讀全書,縱觀他們十四年取經歷程,可以發現,唐僧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優秀品質,就是他的堅守,他磐石般的定力。
取經途中,他們所遭遇到的九九八十一次生死磨難中,不全是險些被害和被吃,有好多次,他們的磨難,是被權、利、色強烈誘惑。如果說被害被吃這些“正磨難”靠的是悟空等人的本領來戰勝,那么,戰勝誘惑這些“反磨難”靠的就是唐僧的定力了。面對誘惑,豬八戒是最經受不起的,他好幾次想留下來入贅,好幾次嚷嚷著分掉行李,各奔前程;孫悟空也有幾次態度曖昧;而沙僧,大多是“跟跟派”,缺少主見。唐僧比三個徒弟受到的誘惑都大,因為他有更多獲得權、利、色的機會和條件。然而,唐僧初心不變,始終不渝,沒有動搖過一刻,也沒有一絲雜念。在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試禪心》中,普賢、文殊等幾位神仙故意設局,演化成驚艷絕倫的一母三女,并說有良田千頃,家資萬貫,還主動提出要招四人為夫,一一配對,許諾“與舍下做個家長”。八戒聞得這般富貴和美色,“心癢難撓,坐在椅子上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悟空洞察秋毫,已經看出其中的微妙;而三藏本來就是凡夫俗子,一點也沒有覺察,他聽到婦人的要求,“便似雷驚的孩子,雨淋的蝦蟆,只是呆呆掙掙,翻白眼兒打仰”。對巨大財色之誘,唐僧只是害怕和擔憂,一點欲望都沒有。幾度春秋之后,在西梁女國,經歷了同樣的誘惑。女國王那個主動,那個真誠,那個殷勤,簡直無以復加,但唐僧拒絕的態度依然是非常堅決。《西游記》中還有這樣一個情節:悟空在菩薩協助下,降伏了已經霸占烏雞國三年的假國王獅子精,真國王的尸體由八戒從深井里馱出,悟空從太上老君那里討來一粒還魂金丹,使國王起死回生。在金鑾殿,國王哭哭啼啼,跪在階心對唐僧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師父救我回生,怎么又敢妄自稱尊?請那一位師父為君,我情愿領妻子在城外為民足矣。”三藏哪里肯受。后來,國王“又將鎮國的寶貝、金銀、獻與師父酬恩。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換關文,催悟空等背馬早行”。你看,面對一國之君的權力,面對鎮國的寶貝,唐僧連想都沒想,拒絕得那么果斷。他的目的就是早早地取回大乘教法,不辱唐王使命。
在十四年的取經路上,唐僧得過一次病,那是在第八十一回。他“頭懸腦脹,渾身皮骨皆疼”,可能是“半夜起來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風吹了”。此時,他最擔心的仍然是不能完成使命,他囑咐悟空找來筆墨,給唐王寫信,要悟空送去。信的最后四句是:“僧病沉疴難進步,佛門深深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啟奏當今別遣人。”沉疴難愈之時,他念念不忘的還是取經,希望有人來繼承大業。這里既有無奈和遺憾,也顯現出他的赤誠與擔當。
這個師徒四眾的取經團隊,應該說是最優組合。如果說除妖降魔靠的是孫悟空他們,那么,抱定信念,形成合力,則靠的是唐三藏這個領導核心。假如沒有唐僧,這個取經團隊不知早已散伙多少次了。玄奘在出發之前,對唐王發過這樣的誓:“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到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誓不回國,永墮沉淪地獄。”這是他的最初承諾,也是他恪守始終的信條。正是因為唐僧的執著和堅持,最后才取回真經,也使得四眾一一皈依釋門。
從唐僧身上,共產黨人是不是也可以獲得這樣的啟示:只要不改初心,抱定信念,必定能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