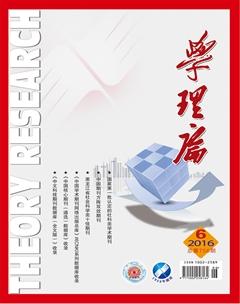試論中國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開發問題
朱陸民 鄧陳潔
摘 要: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是指在國際體系的不同層次、領域中,那些能夠對國際社會的相關領域產生重要性、實質性影響,有利于實現行為體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訴求的位置和空間。目前中國可以開發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主要存在于地緣政治層面、國際體系結構層面和大國互動的動態資源層面。在對可供開發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對中國的意義,并提出了開發的措施建議:加強周邊區域整合,提供國際經濟領域的公共產品;加強制海權建設,實現藍色“海洋夢”;發揮國際體系維護者和協調者的作用;合理處理與大國關系。
關鍵詞:中國;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地緣政治;國際體系;開發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6-0049-04
國際政治資源是指“國際政治主體在國際競爭中用來實現自身利益、貫徹戰略目標所使用的物質和精神資源。”[1]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作為國際政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在國際體系的不同層次、領域中,那些能夠對國際社會的相關領域產生重要性、實質性影響,有利于實現行為體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訴求的位置和空間。”[2]這種空間和位置,既包括地理上的,也包括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占有的位置和戰略空間。對一個國家而言,有效地開發和利用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對實現既定的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中國要成功實現和平發展,必須獲得有利的國際環境和保持良好的對外關系,因此開發利用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一、當前中國可供開發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
隨著國際政治不斷朝著全球政治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中國越來越需要開發一定數量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作為發展支撐,以實現進一步發展。這就迫切需要對中國潛在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從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出發,結合當前國際局勢,中國可供開發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地緣政治層面
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對這個國家的政治行為和國家戰略會產生重要影響。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認為從西亞、南亞、東南亞到東亞整個沿海地帶都屬于邊緣地帶,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戰略性資源、具有經濟發展優勢,而且是陸海權進行爭奪的關鍵,對掌控世界命運具有重要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則正好處于“邊緣地帶”的核心區域,因此應該被賦予豐富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首先,由地理位置而產生的地區影響力。中國地處東南亞、南亞、中亞、東北亞的交匯處,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中國在亞洲事務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歷史上很多亞洲問題的解決,如朝核問題、印巴爭端、南海問題等,都離不開中國的一般性或主導性參與。因此,中國的影響力遍及南亞、中亞及廣闊的亞太地區。雖然這種影響力的大小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中國自身實力的強弱,但其來源卻在于中國所處的獨特地理區位。故而由于中國的地理區位所產生的在地區事務中長期、廣泛存在的影響力便是可供中國開發的首要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這種資源的有效開發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參與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并有利于構建更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地區權力結構,為深入開發其他國際政治資源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次,陸海復合型國家①的天然優勢。將陸海復合的國家特點作為一種結構性政治資源,其原因在于這種“與生俱來”的特點為國家戰略的制定提供了優厚的條件,使國家戰略避免單一化,代之以多元化的生存發展戰略。具體言之,“當國家實力相對衰落時,即使喪失了制海權,亦可以以大陸為依托成為安身立命的歸宿,發揮陸權優勢與敵較量;在國家力量強大時或和平發展時期,則能通過海洋順利地走向世界,發展經貿,在公海謀求、實現自己的利益。”[3]這一資源的開發最大的效用在于使我國具有多元的戰略基礎和維持相對良好的戰略態勢。
(二)國際權力體系結構層面
在國際社會中,主要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決定了國際權力體系的基本結構,權力的多少,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國際政治資源的數量和進一步開發國際政治資源的能力。最能對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產生作用的是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而結構性權力本身也是一種最重要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對結構性權力給出了最具影響力的描述:“決定行事方法的權力,塑造國家間、國家與民眾之間以及國家與公司間互動框架的權力”[4]。就目前的現實而言,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結構性權力擁有者,但隨著中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提升和越來越多的更好地參與國際事務,中國仍能夠在國際互動中獲得一定的結構性權力。
首先,地區層面上,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的緊密聯系,是中國獲得結構性權力的主要來源。目前,中國已連續四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從中國與東盟之間貿易的現狀來看,中國對東盟國家所具有的結構性權力主要有生產的結構性權力和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兩種:生產方面,中國廣闊的消費市場以及中國作為東盟第一大出口對象的事實使得東盟國家創造財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影響,而這種權力也成為中國在處理與東盟國家其他領域關系的一種選擇。例如2012年中菲黃巖島沖突激烈之時,中國宣布加大對菲律賓進口香蕉的檢疫力度,致使菲大量香蕉出口貿易遭受重大損失,此舉的間接效果就是菲方在黃巖島問題上的態度趨于緩和并最終停止進一步惡化事態的行為[5]。金融方面,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人民幣的堅挺,以及近年來國內政治經濟的穩定局面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使得人民幣成為東南亞地區的國際流通貨幣。這一現象背后是中國金融的結構性權力的顯現。
其次,在全球層面上,冷戰結束后,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作為多極中最重要一極的中國擁有較多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在當下,全球治理是中國參與全球事務、獲得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最有效的途徑。由于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問題上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有共同的立場,并且在處理相關問題時能夠不受到利益集團的牽制,在有必要時充分動用國家力量,使得中國能夠更加有效地參與這些事務并發揮積極的作用,并因此而獲得在國際事務中更大的影響力,亦即“軟權力”。例如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上,相比起部分西方國家,中國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并做出更多的努力,也取得了更多的成果:2013年與2005年相比,中國碳排放強度下降28.5%,相當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億噸;在2014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中國表示將從2015年開始在現有基礎上把每年的資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國還將提供600萬美元資金,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6]。之所以將這種影響力作為一種結構性政治資源,是因為其能夠使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更多信任,以及對中國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張、規則安排的認可和追隨,降低敵對性同盟出現的概率,使國際體系結構能夠朝著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發展,進而為中國進一步推行自己的發展戰略提供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
(三)與大國及國際組織互動產生的動態性資源
國際體系的基礎是國際力量結構(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而國際力量結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大國戰略關系[7]。目前,全球范圍內仍主要有五大力量中心:中、美、俄、歐、日。②在中國與其他四大力量所構成的雙邊或多邊關系中,最具有戰略互動價值的是中美俄三角戰略關系。在這三角關系中,相比較于美俄(蘇)之間長期的總體上的對立關系,中國與雙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更大的靈活性:雖然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但是雙方同時也在諸多方面存在相互依賴,不可能完全走向完全的敵對和同盟兩個極端;中俄之間總體上合作大于對抗,而且在近年來雙方的關系進一步密切,合作進一步深化。盡管如此,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雙方也不可能走向結盟,畢竟是兩個地理上接壤的大國,在地緣政治層面上,尤其在中亞,或多或少會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正是由于中美、中俄之間都存在的既沖突又合作的基本關系模式,讓中國能夠根據自己切身的利益需要來靈活調整與二者之間的距離。在不同的三邊關系狀態下,中國會獲得不同的戰略位置和空間。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和產生邊界沖突之時,中美的接近對蘇聯產生了巨大的戰略壓力,進而使中國在當時的國際力量結構中,獲得了對蘇相對優勢的戰略地位。2013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中,中國采取不干預的態度,在保證了中美關系不受其影響的同時,也與俄羅斯簽訂了大量能源進口的協議。這些都是特殊國際環境下大國互動所產生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但是由于國際環境是不斷變化的,因此這種互動產生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具有動態性、時效性。
進入21世紀,國際組織日益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行為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尤其一些政府間國際組織,是構成當前國際機制的主要框架。與國際組織的互動也是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一個重要來源。“(國際機制)帶動行為體內部的革新。國際機制能帶來資源和能力的重新分配,導致新集團的創立或一些團體、次團體變更力量平衡關系;國際機制在合法化過程中能使外部原則內在化,從而對國內制度或有關規則提出變革要求,并導致相應調整或轉變。”[8]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只有參與國際組織、融入國際機制,才能在國際組織中發展、實現國家的利益。中國與國際組織的互動,使中國更加全面地融入國際社會、走向世界,為中國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未來發展空間;同時,通過進入國際機制和推動國際機制改革,中國能夠積累豐富的經驗,為將來參與制定新的國際機制和規則創造條件。
二、中國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措施
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不同于一國所擁有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資源,它是一種外生性的資源,需要行為體通過自身的運作來獲得。結合對當前中國可供開發的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分析,筆者認為中國可采取以下措施來對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進行開發。
(一)加強周邊區域整合,提供國際經濟領域的公共產品
“中國是一個亞洲國家,中國的出路在亞洲。”[9]中國地緣政治環境復雜,鄰國眾多,而且鄰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差異巨大,對中國的戰略空間形成了限制和擠壓,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一大難點。因此,中國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首要措施就是突破地緣政治上的限制,獲得生存空間。
一方面,對中國來說,要實現加強區域整合的目標,必須加快中國—東盟自貿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與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及加入東盟條約的重大舉措,一舉三得:一是可以增進互信,提高相互依存度,減輕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恐懼心理;二是軟化東盟將南海問題擴大化和國際化的意圖;三是打破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與使南海爭端國際化的圖謀,從而有利于我國的國家利益[10]。而“一帶一路”的實施,將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實現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是實現區域整合的基礎性工程。通過區域整合,中國的周邊環境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都將得到改善,彼此間相互依賴加深,避免地緣政治環境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對中國獲得良好的戰略生存空間乃至實現全球戰略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提供國際經濟領域的公共產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內經濟的高速發展、國內經濟的總體穩定使中國具有了提供經濟領域公共產品的能力,而中國與周邊國家巨大的貿易往來量、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為中國提供國際經濟領域的公共產品提供了契機,就目前現狀而言,中國提供公共產品主要有以下兩條路徑:一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擺脫美元對地區經濟貿易的影響;二是為地區發展提供援助資金,推動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整體發展。
(二)加強制海權建設,實現藍色“海洋夢”
作為一個陸海復合型國家,開發海洋資源,加強海權建設是中國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國目前應主要通過以下幾方面著手來加強海權建設:第一,樹立海權意識。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中國政府在大部分時間里重陸地而輕海洋,導致我國海權建設發展緩慢,幾近停滯,最終導致在面對來自海洋上的堅船利炮時,山河破碎,國之不國。因此,加強海權建設的第一要務是樹立海權意識。第二,加強海軍建設,提高開發海洋資源的能力。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保衛海上國土、從近海走向深藍的雄兵利刃,也是中國在日益激烈的海洋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的堅強后盾。同樣,加大科技投入,提升我國開發海洋資源的能力,是我們充分利用海洋資源的基礎和前提。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去開發,再豐富的海洋資源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不能發揮其服務國家利益的作用。第三,加強海洋立法,科學管理海洋。科學合理的海洋制度有利于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規范海洋行為、構建海洋秩序。歷史上的海洋大國,如美國,日本等,在發展海洋權力的過程中,都十分注重政府主導下的與海洋發展相關的法規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這種做法在法理上維護他們自身海洋權益的同時,也加強了其本身海洋行為的合法性。我們在開發海洋過程中,應積極學習歷史上的成功經驗,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為導向,科學合理的規劃海洋開發,完善海洋法的制定,為構建海洋強國提供戰略層面的指導和法理上的支撐。
(三)發揮國際體系維護者和協調者的作用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是中國的現實需要,也是中國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的重要手段。中國要想在國際體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首先必須是國際體系的堅定維護者。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也只有在國際體系總體穩定的基礎上,中國才能獲得發揮作用的空間。當前國際體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中國在總體維護國際體系的基礎上應積極推動國際體系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如推動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建立和完善對貧困地區發展的援助機制,積極參與聯合國的議題和行動,增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推動國際政治民主化等。另一方面,中國應充分利用“經濟實力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身份,在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出現利益分歧時,充當利益協調者,從而獲得更多話語權,提升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為參與制定新的國際規則提供機會。
(四)頭腦冷靜,穩住陣腳,合理處理與大國關系
大國關系目前仍然是國際格局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中國作為大國之一,處理好與其他大國如美、日、俄、歐之間的關系對中國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理處理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應注意以下兩方面。
首先,妥善處理雙邊關系。對中美、中日這兩組關系,雖然近年來彼此之間矛盾發生頻率提高,發生的范圍擴大,但由于這兩組關系直接影響到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因此面對當前所發生的一些沖突,中國應穩住陣腳,堅持通過外交手段管控、處理這些沖突,避免被拖入戰爭的深淵。對中俄之間,應繼續推動雙方的政治互信和經貿合作,深化推進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但與此同時,中國應時刻保持冷靜,防范和規避被卷入到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對抗當中,從而損害自身的國家利益。中歐之間雖然經貿往來頻繁,但意識形態、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也是顯著的。因此處理與歐洲關系,中國應積極推動經貿關系發展,以經濟關系的發展促進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
其次,積極利用多邊合作機制促進雙邊關系發展。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多邊合作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明顯,這些多邊合作機制不僅能促進多邊關系的發展,而且往往超越其本身,為成員間雙邊關系的發展提供機遇和平臺,例如2012年釣魚島事件后,中日關系急速降溫,高層互訪中斷,直到2014年在北京召開APEC峰會的機會中日領導人才實現了釣魚島事件后第一次見面,也為中日關系回暖創造了基礎。因此,中國應積極參與多邊合作,利用多邊合作的平臺,增強彼此間的了解與互信,在多邊合作中發展雙邊關系。此外,中國應通過在多邊合作中積極充當大國利益的協調者,構建有利于自身的多邊大國關系。
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是一國發展的基礎性工作,對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國,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更是有著重要意義。合理有效地開發結構性國際政治資源,將極大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終實現。
參考文獻:
[1]傅菊輝.論國際政治資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5):81.
[2]傅菊輝.國際政治資源論[M].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0:7.
[3]楊勇.發揮海陸兼備優勢是大型海陸復合國家的必然選擇[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4(3):26.
[4][英]安德魯·海伍德.全球政治學[M].白云真,羅文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07.
[5]張燕,鮑豐學.菲律賓商界憂慮“黃巖島影響”發酵[N].第一財經日報,2012-05-15(A06).
[6]成珞.聯合國氣候大會見證中國擔當[EB/OL].解放日報,(2014-09-25)http://www.jfdaily.com/guoji/bw/201409/t20
140925_805826.html.
[7]夏立平.當代國際體系與大國戰略關系[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72.
[8]王杰.國際機制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217.
[9]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10]陳峰君.加強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意義[J].國際政治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