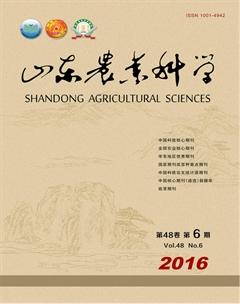起壟溝播種植對濱海鹽堿地土壤微生物區系的影響
張寧 郭洪海 王梅 王學君 王振



摘要:土壤微生物區系是研究土壤的重要生物指標。針對起壟、堆肥、綠肥對濱海鹽堿地微生物的影響,采用平作、起壟、起壟+堆肥、起壟+綠肥、起壟+堆肥+綠肥5個處理展開試驗,研究其對微生物區系的影響。結果表明,5種處理對細菌、真菌、放線菌影響效果基本相似,均表現為:起壟+堆肥+綠肥>起壟+堆肥>起壟+綠肥>起壟>平作,且5種處理中細菌的增幅最大,其次是放線菌,真菌的增幅相對較小;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土壤細菌、真菌、放線菌的數量及總菌數與土壤鹽分含量呈負相關,與有機質、水分呈顯著或極顯著正相關,與pH值無顯著正關系。本研究為今后濱海鹽堿地改良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濱海鹽堿地;起壟溝播;堆肥;綠肥;改良;微生物區系
中圖分類號:S154.37+S156.4+2文獻標識號:A文章編號:1001-4942(2016)06-0062-04
土壤微生物是構成土壤微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土壤微生物區系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地區的土壤微生物生態系的特點及土壤內部生態環境的變化對土壤微生物的生長活動規律的影響,為采取合理的農業措施提供土壤微生物學方面的理論依據[1]。國外對鹽堿地土壤微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耐鹽堿微生物的分離純化及極端鹽堿微生物的生態特征等方面,國內研究主要包括鹽脅迫、不同改良措施及植被對鹽堿地土壤微生物的影響等[2]。在鹽堿地改良措施中,客土法在短期內能改善土壤微生物各項指標,其次是排水法、生物法,排水法對土壤微生物不利,生物法改善土壤微生物生態狀況的速度相對較慢,但因其克服了客土法、排水法的缺點,因而有更好的應用前景[3]。受鹽分和pH值的脅迫,鹽堿地微生物區系和肥沃的糧田菜田土壤微生物區系有很大不同,其微生物總量一般在10-5~10-7cfu.g-1,比正常土壤的數量級低很多[4,5],而且研究表明,高鹽度會降低微生物數量,尤其是放線菌數量。因此,土壤微生物對鹽脅迫極為敏感,可以作為土壤鹽脅迫過程中的重要指標[6]。鹽堿地起壟提高壟溝的表層土壤含水量,降低壟溝的土壤電導率,壟臺土壤EC升高,土壤表面出現積鹽現象,壟溝、壟臺的土壤物理狀況得到改善,增加了地表植被生物量和植被蓋度[7]。基于此,本試驗在起壟溝播小麥、玉米兩個輪作季的基礎上,研究了微生物數量區系與土壤其他理化性狀的相關性,為起壟改良鹽堿地提供科學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地概況
實驗基地位于東營渤海農場,地理坐標為東經118°07′~119°10′,北緯36°55′~38°12′;地處暖溫帶,四季溫差明顯,年平均氣溫11.7~12.6℃,年平均降水量530~630 mm,地下水埋深2~3 m,地下水礦化度10~40 g/L,受高礦化度地下水的影響,土壤極易返鹽退化[8,9]。試驗前土壤pH值8.4,全鹽3.8 g/kg,有機質11.38 g/kg,全氮0.43 g/kg,全磷0.562 g/kg,全鉀17.9 g/kg,速效氮19 mg/kg,速效磷8.3 mg/kg,速效鉀112 mg/kg。土壤質地砂質中壤,前茬種植棉花。
1.2試驗設計與布局
試驗設計:①CK(平作);②QL(起壟);③DF(起壟+堆肥);④LF(起壟+綠肥);⑤DL(起壟+堆肥+綠肥)。
起壟工程標準:壟溝寬60 cm,壟背為梯形,底寬40 cm,頂寬10 cm,高20 cm。
小區設計標準:每個試驗小區30 m2,東西寬5 m(5壟),南北長6 m。重復3次,每個重復單元設置1.5 m的保護行路。
在試驗布設前,進行一次深翻、平整土地。堆肥選擇牛糞充分露天發酵,綠肥選擇鼠茅草、三葉草。
1.3測定指標及方法
分離計數培養基:牛肉膏蛋白胨培養基、馬丁氏孟加拉紅瓊脂培養基和高氏一號培養基,分別用于細菌、真菌和放線菌的分離與計數。
方法:稱取10 g鮮土樣置于已滅菌的裝有玻璃珠的三角瓶中,加入90 mL無菌水,振蕩 30 min使土樣分散成為均勻的土壤懸液,進行梯度稀釋,取合適的稀釋度涂平板,一般稀釋度好氧異養細菌采用 10-5~10-3,放線菌采用10-4~10-2,真菌采用10-3~10-1。將涂布均勻的平板倒置于30℃培養一定時間(細菌1~5 d,放線菌5~14 d,真菌3~6 d),進行 CFU(Colony Forming Unit)計數。
計算結果以每克烘干土中的微生物數量表示,計算公式為:每克干土中菌數=菌落平均數×稀釋倍數/干土質量。
2結果與分析
2.1不同改良措施對鹽堿地土壤微生物區系的影響
從整體來看(圖1),細菌在6月數量達到最多;隨著季節的變化,8、10月數量明顯下降;等到來年春季4、5月數量慢慢回升。
與對照(平作)相比,起壟能夠顯著增加土壤細菌數量,增幅在4、5、6、8、10月分別為50.81%、35.62%、31.30%、64.29%、45.27%,起壟+堆肥處理同期增幅分別為104.76%、63.21%、38.39%、116.64%、84.89%,起壟+綠肥處理同期增幅分別為63.48%、48.28%、31.30%、73.79%、54.67%,起壟+堆肥+綠肥分別為128.57%、77.00%、72.73%、135.71%、99.94%。可見,不同改良措施對土壤細菌數量的影響:起壟+堆肥+綠肥>起壟+堆肥>起壟+綠肥>起壟>平作。
2.2不同處理微生物區系差異
由表1可知,各處理對細菌、放線菌和總菌數的影響效果基本相似,對真菌的影響有所不同。各處理細菌、放線菌數量和總菌數為起壟+堆肥+綠肥>起壟+堆肥>起壟+綠肥>起壟>平作,4個起壟處理之間均差異不顯著,但均顯著高于對照(平作),各處理真菌數量亦為起壟+堆肥+綠肥>起壟+堆肥>起壟+綠肥>起壟>平作,其中起壟+堆肥+綠肥、起壟+堆肥與對照差異顯著。
2.3土壤微生物區系與微生物多樣性、土壤理化性質之間的相關關系
由表2可知,土壤細菌、真菌、放線菌的數量及總菌數與土壤鹽分含量之間呈負相關關系,與有機質、水分之間呈顯著或極顯著相關關系,與pH值無顯著關系[15]。這表明鹽堿地鹽分、有機質、水分是土壤微生物區系最直接的影響因子,而且其中有機質影響作用比較顯著。
3討論與結論
鹽堿地微生物數量一般要少于普通農用土壤,一般認為是鹽度導致的微生物生存適宜環境改變的結果[16]。土壤微生物群落是一個組成復雜的群體,不同微生物種類所要求的營養元素不盡相同[17,18]。施用有機肥能夠顯著增加土壤細菌、放線菌和真菌數量,說明施用有機肥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較多的能源與養分,特別是有機碳源為微生物生命活動提供所需能量,且有機肥本身也含有大量活的微生物,促進了土壤微生物大量繁殖,使土壤微生物的新陳代謝加快,施有機肥更有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以及維持土壤營養元素的良好循環,這與陳梅生等研究的長期施有機肥與缺素施肥對潮土微生物活性的影響結果一致[19];孫文彥等[20]研究綠肥與苗木間種改良苗圃鹽堿地,認為種植翻壓耐鹽綠肥作物(毛葉苕子和二月蘭)可提高鹽漬土細菌、放線菌、真菌數量,改善鹽堿地土壤質量狀況。
本研究結果表明:起壟和堆肥、綠肥相結合的各種處理對提高鹽堿地細菌、真菌、放線菌數量有良好的影響效果,5種處理對細菌、真菌、放線菌影響效果基本相似,均表現為:起壟+堆肥+綠肥>起壟+堆肥>起壟+綠肥>起壟>平作。從各種菌類增幅看,5種處理對細菌的增幅最大,其次是放線菌,對真菌的增幅相對來說較少。說明起壟溝播種植和地力提升技術(堆肥、綠肥)相結合具有良好的鹽堿地土壤改良作用,可以減緩由于鹽堿導致的土壤肥力損失,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樣性。
同時各種土壤理化性質與微生物區系也存在相關關系。鹽堿地土壤鹽分含量及水含量限制了土壤微生物活動[10],尤其對細菌的生長活動有重要影響[11]。有研究表明,土壤含水率的變化對土壤細菌多樣性影響不顯著,而對真菌多樣性影響差異顯著。此外,土壤含水率與鹽分的交互作用對細菌多樣性不顯著,對真菌多樣性的影響顯著。而有機質也是微生物最主要的影響因子,已有研究結果表明,土壤有機質含量是影響土壤微生物量的一個重要因素[12,13]。土壤有機碳對土壤微生物量起關鍵作用,有機碳控制著土壤中能量和營養物的循環,是微生物群落穩定的能量和營養物的來源,有機碳越高,土壤微生物量就越大[14]。本試驗結果表明,微生物量與土壤鹽分含量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與郭永忠等研究不同改良措施對銀川平原鹽堿地土壤微生物區系的影響結果一致[21],與有機質、水分之間呈極顯著或顯著相關關系,與pH值沒有顯著關系。
參考文獻:
[1]王梅,江麗華,劉兆輝,等.石油污染物對山東省三種類型土壤微生物種群及土壤酶活性的影響[J].土壤學報,2010,47(2):341-346.
[2]李鳳霞,郭永忠,許興.鹽堿地土壤微生物生態特征研究進展[J].安徽農業科學,2011,39(23):14065-14067,14174.
[3]康貽軍,楊小蘭,沈敏,等.鹽堿土壤微生物對不同改良方法的響應[J].江蘇農業學報,2009,25(3):564-567.
[4]康貽軍,胡健.灘涂鹽堿土壤微生物生態特征的研究[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07,26(增刊):181-183.
[5]孫佳杰.天津濱海鹽堿土壤微生物生態特征的研究[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2010,34(3):57-60.
[6]周玲玲,孟亞利,王友華,等.鹽脅迫對棉田土壤微生物數量與酶活性的影響[J].水土保持學報,2010,24(2):241-246.
[7]關法春,苗彥軍,Tianfang Bernie Fang,等.起壟措施對重度鹽堿化草地土壤水鹽和植被狀況的影響[J].草地學報,2010,18(6):763-767
[8]劉岳燕,姚槐應,黃昌勇.水分條件對水稻土微生物群落多樣性及活性的影響[J].土壤學報, 2006, 43 (5): 828-834.
[9]李東坡,武志杰,陳利軍.有機農業施肥方式對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響研究[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5,13(2):99-101.
[10]林學政,陳靠山,何培青,等.種植鹽地堿蓬改良濱海鹽漬土對土壤微生物區系的影響[J]. 生態學報,2006,26(3):801-807.
[11]趙勇,李武,周志華,等.秸稈還田后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變化的初步研究[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05,24(6),1114-1118.
[12]Powlson D S, Boroks P C, Christensen B T. Measurement of soil microbial biomass provides an indication of changes in total soil organize matter due to straw incorporation[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1987, 19: 159-164.
[13]Lovell R J S, Bardgett R. Soil microbial biomass and activity in long-term grassland: effects of management change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1995, 27: 969-975.
[14]劉秉儒.賀蘭山東坡典型植物群落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沿海拔梯度的變化特征[J]. 生態環境學報, 2010, 19(4):883-888.
[15]王世強,胡長玉,程東華,等.調節茶園土壤pH對其土著微生物區系及生理群的影響[J].土壤, 2011, 43(1): 76-80.
[16]張瑜斌,林鵬,魏小勇,等.鹽度對稀釋平板法研究紅樹林區土壤微生物數量的影響[J].生態學報, 2008, 28(3):1288-1296.
[17]鄭華,歐陽志云,方治國,等.BIOLOG在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研究中的應用[J].土壤學報,2004,41(3):456-461.
[18]時亞南.不同施肥處理對水稻土微生物生態特性的影響[D].杭州:浙江大學,2007:37-41.
[19]陳梅生,尹睿,林先貴,等.長期施有機肥與缺素施肥對潮土微生物活性的影響[J].土壤,2009,41(6):957-961.
[20]孫文彥,孫敬海,尹紅娟,等.綠肥與苗木間種改良苗圃鹽堿地的研究[J].土壤通報,2015,46(5):1222-1225.
[21]郭永忠,李鳳霞,王學琴,等.不同改良措施對銀川平原鹽堿地土壤微生物區系的影響[J].河南農業科學,2012,41(11):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