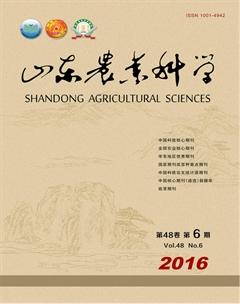我國(guó)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水平與水資源流轉(zhuǎn)關(guān)聯(lián)性的實(shí)證研究
范小艷



摘要:隨著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深化,城鎮(zhèn)規(guī)模的不斷擴(kuò)張需要大量的資源作為發(fā)展的物質(zhì)基礎(chǔ),產(chǎn)業(yè)間對(duì)資源的惡性競(jìng)爭(zhēng)會(huì)愈發(fā)凸顯。水資源作為重要的投入要素,城鎮(zhèn)化的高速發(fā)展面臨著水資源利用率低下、水資源配置與管理機(jī)制不完善等問(wèn)題。本文搜集了2004~2014年10個(gè)河域一級(jí)分區(qū)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運(yùn)用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分別在截面與時(shí)間序列上對(duì)水資源流轉(zhuǎn)與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水平的關(guān)聯(lián)性進(jìn)行了探討與實(shí)證研究,并提出了相關(guān)結(jié)論。
關(guān)鍵詞:城鎮(zhèn)化;水資源流轉(zhuǎn);面板數(shù)據(jù);優(yōu)化配置
中圖分類號(hào):TV213+F291.1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號(hào):A文章編號(hào):1001-4942(2016)06-0168-05
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促進(jìn)了屬地原本單一的農(nóng)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向多元化經(jīng)濟(jì)體制的轉(zhuǎn)型與資源的再分配,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的多樣性擴(kuò)張與推動(dòng)新型產(chǎn)業(yè)的規(guī)模性發(fā)展,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多元化發(fā)展,有利于縮小農(nóng)村與城市的收入差距,逐步實(shí)現(xiàn)公平與正義的時(shí)代主題。
水資源涉及到全產(chǎn)業(yè)鏈的各個(gè)方面,也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口流轉(zhuǎn),從而作用于城鎮(zhèn)化進(jìn)程。2002~2014年,我國(guó)城鎮(zhèn)化率以年均1.35%的速度發(fā)展,2014年城鎮(zhèn)化率達(dá)到了54.1%,預(yù)計(jì)到2020年將達(dá)到60%,其背后對(duì)于水資源的需求總量與用水結(jié)構(gòu)與規(guī)劃勢(shì)必發(fā)生重大變化,兩者的內(nèi)在邏輯成為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
1文獻(xiàn)綜述
關(guān)于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與水資源流轉(zhuǎn)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問(wèn)題,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做了大量研究。Allan(1999)[1]、Zoebl(2006)[2]對(duì)正處于高速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所在國(guó)的水資源配置與可持續(xù)利用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為城市水資源短缺問(wèn)題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Merret(1997)[3]將城鎮(zhèn)化發(fā)展中對(duì)水資源的利用情況大致劃分為三個(gè)階段,分別是需求快速增長(zhǎng)階段、需求滯留階段與需求負(fù)增長(zhǎng)階段。Meinzen-Dick等(2002)[4]認(rèn)為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的水資源配置問(wèn)題的解決應(yīng)集中在城鎮(zhèn)水資源供給量的增加、產(chǎn)業(yè)部門間的水資源合理配置與城鎮(zhèn)節(jié)水三個(gè)方面。Boberg(2005)[5]的研究表明,人均水資源消耗水平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城鎮(zhèn)化進(jìn)程速率,人口聚集效應(yīng)會(huì)加強(qiáng)水資源短缺的困境。毛戰(zhàn)坡(2014)[6]論證了水資源管理與規(guī)劃的重要地位,建議完善水資源全過(guò)程管理,以區(qū)域水資源為著眼點(diǎn),形成節(jié)水、水資源優(yōu)化配置、系統(tǒng)治理的解決方案。
學(xué)者們也從實(shí)證角度對(duì)水資源與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分析。許廣森等(1989)[7]分析了我國(guó)超過(guò)300個(gè)城鎮(zhèn)的水資源供需情況;陳永奇(1997)[8]對(duì)黃河流域水資源緊缺城市的水資源供需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定量研究,進(jìn)而對(duì)相關(guān)城市的城鎮(zhèn)化程度與缺水程度做出了全方位的深入評(píng)價(jià);鮑超等(2006)[9]基于河西走廊區(qū)域的面板數(shù)據(jù)對(duì)其水資源需求總量與城鎮(zhèn)化水平做了實(shí)證研究,認(rèn)為河西走廊區(qū)域的城鎮(zhèn)化水平與水資源需求總量呈正相關(guān),且每年的遞增速率不斷提升;都沁軍等(2009)[10]對(duì)河北省城鎮(zhèn)化率與水資源利用情況做了量化分析,認(rèn)為城鎮(zhèn)水資源的供給不足與分配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城鎮(zhèn)化發(fā)展;張曉曉等(2015)[11]對(duì)寧夏2000~2012年的城鎮(zhèn)化率、水資源結(jié)構(gòu)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做了動(dòng)態(tài)演化分析,結(jié)論顯示:農(nóng)業(yè)用水總量仍居高,但總體比重在不斷下降,工業(yè)與生活用水總體比重隨著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呈現(xiàn)明顯的遞增趨勢(shì)。
但相關(guān)研究多針對(duì)單一區(qū)域的截面數(shù)據(jù)或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基于此,本文選取了我國(guó)10個(gè)河域一級(jí)分區(qū)2004~2014年的面板數(shù)據(jù)為研究對(duì)象,建立面板數(shù)據(jù)回歸模型,分析了水資源利用、用水結(jié)構(gòu)與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關(guān)聯(lián)性及其內(nèi)在影響機(jī)理,從而為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水資源的合理利用與配置提供依據(jù)。
2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與水資源流轉(zhuǎn)配置的關(guān)聯(lián)假設(shè)
2.1假設(shè)1:城鎮(zhèn)化發(fā)展對(duì)水資源可持續(xù)利用的脅迫性影響
通過(guò)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與集聚效應(yīng)推動(dòng)生產(chǎn)效率大幅提高、資源優(yōu)化配置是城鎮(zhèn)化的核心目的。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初期,城鎮(zhèn)供水基礎(chǔ)設(shè)施和管理與調(diào)度水資源的水平較低,水資源的利用效率低下,無(wú)法滿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變化。隨著產(chǎn)業(yè)規(guī)模與城鎮(zhèn)規(guī)模的擴(kuò)大,經(jīng)濟(jì)總量的增長(zhǎng)對(duì)于水資源的依賴越來(lái)越大(表1),因而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對(duì)水資源可持續(xù)利用具有一定的脅迫作用。
2.2假設(shè)2:水資源可持續(xù)利用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呈現(xiàn)階段性影響
2.2.1水資源利用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支撐作用工業(yè)是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核心產(chǎn)業(yè),從制造、加工到冷卻、洗滌,水資源作為極其重要的生產(chǎn)資源直接或間接參與工業(yè)過(guò)程。工業(yè)化過(guò)程會(huì)帶來(lái)產(chǎn)業(yè)大規(guī)模興起、人口集聚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多元化,進(jìn)而對(duì)城鎮(zhèn)化起到穩(wěn)固的支撐作用。
2.2.2水資源利用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制約作用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發(fā)展速率無(wú)限逼近甚至超過(guò)區(qū)域本身的水資源荷載后,城鎮(zhèn)水資源無(wú)法滿足日益增長(zhǎng)的工業(yè)與生活用水的需求,會(huì)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起到制約作用,這些制約因素會(huì)體現(xiàn)在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生活、生產(chǎn)等諸多方面。另外,城鎮(zhèn)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也面臨著排水和水污染等相關(guān)衍生問(wèn)題。此時(shí),水資源的稀缺性就會(huì)隨之凸顯出來(lái),相對(duì)于城鎮(zhèn)整體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和生活系統(tǒng)日益旺盛的需求,兩者的矛盾會(huì)不斷加劇,從而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深化產(chǎn)生制約作用。
3水資源配置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影響的實(shí)證分析
3.1指標(biāo)、數(shù)據(jù)及模型的選擇
3.1.1指標(biāo)的選擇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動(dòng)與水資源需求結(jié)構(gòu)變化最為明顯的兩個(gè)部門是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為簡(jiǎn)化計(jì)量過(guò)程,使結(jié)果更具準(zhǔn)確性,本文主要考察水資源在上述兩大產(chǎn)業(yè)間流轉(zhuǎn)調(diào)配的變化對(duì)于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影響。
Urbtion(自變量):城鎮(zhèn)化率。按照各省、市、自治區(qū)所屬一級(jí)河域分區(qū)的城鎮(zhèn)化系數(shù)的加權(quán)平均所得的各一級(jí)河域的城鎮(zhèn)化系數(shù)。
Watl(因變量):水資源流轉(zhuǎn)率[12]。各一級(jí)河域分區(qū)城鎮(zhèn)工業(yè)用水與農(nóng)業(yè)用水比值,用于反應(yīng)工農(nóng)產(chǎn)業(yè)間水資源利用情況,以便說(shuō)明水資源的利用方向。
3.1.2數(shù)據(jù)的來(lái)源與處理《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與《中國(guó)水資源公報(bào)》中以各省市為統(tǒng)計(jì)單位的水資源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缺損較為嚴(yán)重,但按河域一級(jí)分區(qū)的統(tǒng)計(jì)較為完整,因此選取10個(gè)河域一級(jí)分區(qū)為研究對(duì)象(表3)。但這樣會(huì)出現(xiàn)河域分區(qū)的城鎮(zhèn)化率無(wú)法找到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因此,本文按照各省、市、自治區(qū)所屬的分區(qū)城鎮(zhèn)化率,按面積的加權(quán)平均計(jì)算,得出10個(gè)一級(jí)分區(qū)的城鎮(zhèn)化率(Urbtion)。樣本區(qū)間為2004~2014年。
3.1.3實(shí)證模型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
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Panel Data Model)兼有截面數(shù)據(jù)模型與時(shí)間序列模型的特征,既能反映某個(gè)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各特征數(shù)據(jù)的規(guī)律,也能描述單個(gè)個(gè)體特征在時(shí)間區(qū)域上的變化規(guī)律。由于水資源流轉(zhuǎn)與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數(shù)據(jù)樣本較少,為凸顯數(shù)據(jù)的擬合度,采取面板數(shù)據(jù)較為合適。
3.1.4統(tǒng)計(jì)量描述表2顯示,樣本個(gè)體的Urbtion的差異性較大,最小值39.76%,最大值52.64%。這符合我國(guó)當(dāng)前城鎮(zhèn)化發(fā)展較為迅猛,但區(qū)域間差異性較大的現(xiàn)狀。
樣本個(gè)體的Watl的差異也較大,最小值為0.024,最大值為0.813。這說(shuō)明我國(guó)各區(qū)域間產(chǎn)業(yè)類別與產(chǎn)業(yè)規(guī)模差別較大,水資源利用方向存在較大差異。
可以看出,除了遼河區(qū)、東南諸區(qū)、珠江區(qū)的水資源流轉(zhuǎn)系數(shù)(Watl)與城鎮(zhèn)化率(Urbtion)呈現(xiàn)負(fù)相關(guān)性(β′i的變動(dòng)值與截距項(xiàng)的和為負(fù)值),其余河域分區(qū)均呈現(xiàn)出正相關(guān)性。總體來(lái)看,水資源從農(nóng)業(yè)部門流轉(zhuǎn)至工業(yè)部門是有利于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發(fā)展,但局部區(qū)域也會(huì)呈現(xiàn)相反的發(fā)展邏輯。松花江區(qū)、長(zhǎng)江區(qū)、西南諸區(qū)、西北諸區(qū)、黃河區(qū)、海河區(qū)與淮河區(qū)的水資源流轉(zhuǎn)拉動(dòng)效率較為顯著;而像珠江區(qū)這樣本身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中工業(yè)化進(jìn)程步伐較快地區(qū)水資源的非農(nóng)轉(zhuǎn)化卻帶來(lái)相反的副作用。由模型擬合結(jié)果舉例,長(zhǎng)江工業(yè)部門從農(nóng)業(yè)部門水資源每流轉(zhuǎn)1%,則該區(qū)域的城鎮(zhèn)化系數(shù)上升2.986%;珠江區(qū)工業(yè)部門從農(nóng)業(yè)部門水資源每流轉(zhuǎn)1%,該區(qū)域的城鎮(zhèn)化系數(shù)下降0.612%。由此可見(jiàn),水資源利用對(duì)于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影響在截面上依照區(qū)域不同而在工農(nóng)業(yè)部門中產(chǎn)生不同效果。
3.2.2時(shí)間序列估計(jì)以10個(gè)河域分區(qū)在第n年的全部觀測(cè)值為一組序列進(jìn)行估計(jì),假定時(shí)間序列上的結(jié)構(gòu)參數(shù)只隨著時(shí)間的變化而變化。對(duì)Urbtion與Watl兩個(gè)變量分別取對(duì)數(shù)以消除異方差性的影響,其效應(yīng)模型為公式3。選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進(jìn)行擬合,回歸結(jié)果如表4。
從表4中可得,R2為0.914427,調(diào)整后的R2=0.913337,表明水資源在工農(nóng)業(yè)部門之間的流轉(zhuǎn)率與城鎮(zhèn)化水平存在高度相關(guān)性。另外,β′t代表在時(shí)間序列上水資源流轉(zhuǎn)率(Watl)對(duì)于城鎮(zhèn)化水平(Urbtion)的彈性,β′t的數(shù)值越大,就說(shuō)明水資源從農(nóng)業(yè)轉(zhuǎn)向工業(yè)對(duì)城鎮(zhèn)化影響就較大。從表4可得,2014年的β′t最大,2005年的β′t最小,且從2004年至2014年β′t值呈現(xiàn)出上升趨勢(shì),表明在時(shí)序上水資源從農(nóng)業(yè)部門流轉(zhuǎn)至工業(yè)部門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有推動(dòng)作用。另外,從∝t來(lái)看,其數(shù)據(jù)隨著年份的變化較小,說(shuō)明除水資源流轉(zhuǎn)外,其他因素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影響較為穩(wěn)定,更加凸顯水資源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影響的重要性。
4結(jié)論與展望
伴隨城鎮(zhèn)化引起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水資源在產(chǎn)業(yè)內(nèi)部的使用效率不佳是引起水資源重新配置的核心動(dòng)因,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的興起與水資源供給的不足必然會(huì)引起部門間對(duì)水資源的惡性競(jìng)爭(zhēng)。這些問(wèn)題是由于我國(guó)水資源配置的管理機(jī)制不完善與水權(quán)制度的缺失所導(dǎo)致的,也體現(xiàn)了水資源在我國(guó)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必須建立完善的水資源調(diào)配管理機(jī)制與健全的水權(quán)制度,為我國(guó)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提供堅(jiān)實(shí)的資源保障。
水資源流轉(zhuǎn)調(diào)配的關(guān)鍵在于最大化地激發(fā)水資源作為生產(chǎn)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
雖然城鎮(zhèn)化的核心是工業(yè)化,但城鎮(zhèn)化發(fā)展過(guò)程中不能將農(nóng)業(yè)水資源無(wú)節(jié)制地調(diào)配至工業(yè)部門。需要根據(jù)不同區(qū)域和該區(qū)域城鎮(zhèn)化的程度進(jìn)行特定研究與分析,構(gòu)建一套復(fù)雜且全面的水資源調(diào)配管理機(jī)制。
2004~2014年正處于我國(guó)城鎮(zhèn)化初期階段,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引起的水資源競(jìng)爭(zhēng)的惡性程度尚未體現(xiàn),在這個(gè)階段,時(shí)間序列估計(jì)結(jié)果顯示水資源從農(nóng)業(yè)向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流轉(zhuǎn)對(duì)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起到積極的正向作用。但隨著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發(fā)展,資源的有限性無(wú)法匹配產(chǎn)業(yè)規(guī)模擴(kuò)展需求時(shí),矛盾就會(huì)出現(xiàn),是否跟本文假設(shè)2相吻合還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xiàn):
[1]
Allan T.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why better water management may not solve the problem[J].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1999,40(1):71-75.
[2]Zoebl D.Is water productivity a useful concept in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J].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2006, 84(3):265-273.
[3]Merret S.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London:UCL press, 1997.
[4]Meinzen-Dick R,Appasamy P P. Urbanization and intersectoral competition for water[J].Urbanization and Water,2001:27-51.
[5]Boberg J.How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water management policiesaffect freshwater resources[M].Santa Monica,CA:Rand Corporation,2005.
[6]毛戰(zhàn)坡.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農(nóng)村水資源保護(hù)相關(guān)問(wèn)題思考[J].環(huán)境保護(hù),2014(15):25-27
[7]許廣森,彭嘉堡.中國(guó)城市水資源系統(tǒng)分析[J].中國(guó)給水排水,1989,5 (3):33-34
[8]陳永奇.黃河流域與缺水城市水資源供需預(yù)測(cè)[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7.
[9]鮑超,方創(chuàng)琳.河西走廊城市化與水資源利用關(guān)系的量化研究[J].自然資源學(xué)報(bào),2006 (2):301-310
[10]都沁軍,馮蘭剛,田亞明. 基于VEC模型的河北省城市化與水資源利用關(guān)系研究[J].石家莊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32(3):39-42
[11]張曉曉,董成鎖,李澤紅,等.寧夏城鎮(zhèn)化與水資源利用關(guān)系分析[J].資源與環(huán)境,2015(6):696-699
[12]來(lái)晨霏,田貴良.我國(guó)二元經(jīng)濟(jì)中水資源流轉(zhuǎn)模式研究[J].中國(guó)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2(8):9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