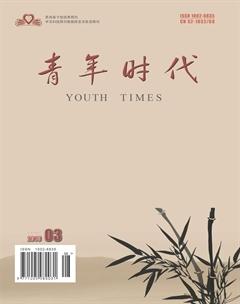一地梨花
張婧
摘要:“梨花體”諧音“麗華體”,因女詩人趙麗華名字諧音而來。梨花派詩歌有些作品相對另類,引發爭議,被網友戲謔為“口水詩”。在本文中,筆者以趙麗華詩作《一個人來到田納西》和《我終于在一棵樹下發現》為例,分析梨花體本身的審美價值以及對于當代詩壇的影響。
關鍵詞:梨花體;新詩;解構;行為藝術
走過了唐詩的器宇軒昂,嘗過了宋詞的婉轉清麗,感受了朦朧詩派對于內心的執著探索和迷茫苦楚后,當代詩壇卻走進了—個尷尬的境地:不乏創作大家,更不缺少創作嘗試,可這些嘗試卻屢屢將詩人推上風口浪尖,趙麗華便是如此。
行為藝術派的詩人在詩歌朗誦的過程中一件件地將自己的衣服脫下,看似表演般戲謔嘲諷,卻是表達為詩歌減負的希冀。當面對如潮水般涌來的流言蜚語時,民眾是歡愉的,他們在嘲笑聲中獲得了快樂,詩人群體卻是無奈的。
自2006年8月之后,網絡上開始出現了惡搞趙麗華的詩歌事件,網友以嘲笑的心態仿寫了大量的口語詩歌,更有好事者取“趙麗華”名字諧音成立“梨花教”,封其為“教主”;文壇也出現了“反趙派”和“挺趙派”,引起詩壇紛爭。趙麗華的詩歌究竟有何魅力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呢?各個大學的教授、詩歌研究專家、詩人都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而主要的分歧仍在于“詩歌的口語化寫作”這一核心問題之上。詩歌究竟應不應該口語化,如果口語化了,那么詩的魅力又在何處?
《一個人來到田納西》
毫無疑問
我做的餡餅
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這是趙麗華的一首代表作品,將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森的《田納西的壇子》做了調侃式的解構后產生的作品。白話式的語言,就其詩歌本身內容來看十分簡單,然而結合趙麗華當時孤身一人前往田納西的境況,本詩卻有更多的解讀意味了。在田納西,并沒有什么中國餐館,即便有也無法做出家鄉的味道,自己做的餡餅可能在客觀上并不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然而對于當時的自己來說,卻是代表了家鄉的味道,是自己成長的記憶。短短三行詩,看似口語化,甚至“口水化”沒有任何意義,然而結合作者自身經歷去看,卻成了最意味深長、最長情的一段對家鄉的告白。
《我終于在一棵樹下發現》
一只螞蟻,另一只螞蟻,一群螞蟻
可能還有更多螞蟻
初讀這首詩時,難免想到魯迅先生的名句:我家門前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從語言本身來說,這是不規范的表達,然而不同的語句放置在不同的語境下可能會產生相應的文學效果,是不是在尋求藝術突破的時候,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突破規范的束縛呢?
再回到詩歌本身,看似無聊的一次發現,背后有什么隱含的意義呢?我在樹下發現了什么?一只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會有更多螞蟻。我的發現到最后可能都只是螞蟻,只不過我的見識由少數的螞蟻變成了更多的螞蟻。回想我們的一生,有誰能說我們真的認識了這個世界,明確了種種道理嗎?可能我們的所見也不過只是螞蟻罷了,只不過我們的見識越來越多,由一只螞蟻的驚奇,變成了習慣一群螞蟻的存在,甚至會猜想是否還有更多的螞蟻。人類的認識也不過如螞蟻般渺小。
經過了這般的引導,再來看李麗華的詩歌創作本身,梨花體不是李麗華詩歌創作的全部,曾經的她也寫過許多婉轉含蓄又意蘊深遠的詩歌,梨花體只是她近年來的一次嘗試而已。梨花體不同于以往的朦朧詩,不同于席慕蓉等人寫作的抒情詩,它沒有玩味的意象,沒有幽遠的意境,它短小精悍,讀完后甚至也感受不到那種朦朧幽遠或是明白暢達的意境,它更像是一種“挑逗”的“線索”。讀完第一遍,不知其所云,讀完第二遍,覺得荒唐可笑,卻難以丟開,再讀第三遍,這—遍讀過后仿佛才有了些模糊的感覺,知道了努力的方向,將詩中的線索一樣拼起,將現實中的感悟一點點結合,才有了這最后的玩味。
然而梨花體畢竟是趙麗華自己的一次嘗試,可以說她是希望突破自己過去詩歌創作的桎梏,為詩壇注入一絲活力。然而身為一個詩人,創作可以是大膽的,但是創作之后的選擇卻應該是謹慎的,趙麗華將自己不成熟的詩歌拿出來與大家共同評判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將本就被受爭議的口語化詩歌張貼在網絡上,勢必會引起一些對詩歌了解不多、或者說堅守傳統詩歌流派的人的強烈反對,更有好事網友也參與到這場大討論中來惡搞現代詩歌,杜撰出《誰動了我的花內褲》這樣的詩歌,并聲稱這是趙麗華的新作。給詩人本身帶來困擾與壓力的同時,也讓社會大眾、網絡媒體開始懷疑這種詩歌創作。本意是為詩歌減負,然而在網絡環境下,網民的關注點早就不再是當下我國詩歌發展現狀以及方向展望,已然變成了對于“口語化”詩歌的狂歡式吐槽,對于代表詩人的人身攻擊,對于低俗作品的肆意模仿濫造,用娛樂至死的精神,將詩壇文壇攪亂。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一個不尚夠包容、不夠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每一步的前進都會面臨巨大的阻力,承擔無盡的非議。我們鼓勵這樣的前進,但我們也必須照顧到時代的境況、考慮到民眾的承載能力,避免不進而退的結果,避免給本就備受爭議的脆弱的詩歌壓上更為沉重的包袱,這是每—個詩人在這個時代的責任。這也是每一個想要讀詩,愛好湊詩的人應有的承擔。我們都應該學會包容,讓梨花也能有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