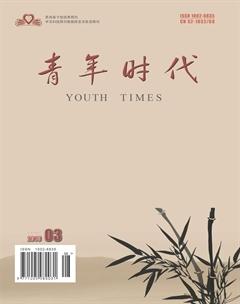淺談東漢時期觀音雕刻藝術在現代古沉木
邢建國
摘要:我國東漢時期時期多種雕刻術手法與造型結合的觀音雕刻藝術,為現代古沉木雕刻提供了“他山之石”,借鑒和運用傳統的雕刻手法與藝術,為現代雕刻藝人在古沉木材料觀音形象的雕刻領域提供了廣闊的創造力。
關健詞:東漢時期;觀音特征;古沉木;雕刻;藝術
一、觀音造型形態隨時代而變化
觀音造像就能反映各個時代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從各個時代的觀音造像的演變可以證明這種情況。在我國歷史上,觀音一直是受人們追捧的,各個時期造型特征明顯,各不相同。古代藝匠在這方面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對佛教中的各種人物在不違背佛教造像儀軌又極力符合統治者的意圖與要求,不同的歷史時期,從面相、特征、衣飾、表現技法、使用材料、體態造型等方面有著不同的演變,有著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格。
東漢時期,是我國觀音雕刻與造型最有時代印記的特殊時期,觀音造型被稱為是“犍陀羅樣式”,在當時特別流行。在東漢時期時期,由于時代的變遷,和受外來佛像藝術的影響,這時期的觀音造型藝術有了較為明顯區別,按其造型風格與造型特點,這時期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各不相同。
東漢早期觀音造型顯男性容貌,面部豐滿、眼大而凸、眉長而平、鼻深高隆與額齊平、耳長齊肩、頭戴寶冠,寶冠上還雕花髻,通身顯貴族富人的裝飾,此外還有發髻冠,化佛冠,冠兩旁裝飾猶如翅膀的寶僧,袒上身,頸部有懸鈴的圓領式,胸部掛瓔珞和作為兩蛇形的飾具兩臂著釧,下著羊腸大裙,衣紋表現技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漢代流行的陰線刻法;一種是一道道的凸起線條,猶如犍陀羅雕塑的技法,有的在凸起線條中間刻陰線一條,另一種為直平階梯式的刻法。
中期觀音造型除原有的裝飾外,又發展出中國流行的外面搭載臂上的披帛,披帛兩肩下垂交叉于兩腿間,然后上卷至肘部,再向外飄、上卷處顯露折角。頭著花瓣式冠或發髻……東漢中期觀音造像衣紋的表現技法,在早期的基礎上,除保持原有的陰線條與凸起的線條外,在犍陀羅式的基礎上新發展出直平階梯式的衣紋。
晚期,觀音造型由瘦長的臉型轉化成半圓的臉型,觀音的花髻冠與化佛冠上的寶僧不再外飄、而向下垂肩的披帛下垂交叉處多不用環,發展為一飾物。下裙上緣密褶整齊,系裙的絳帶寬大如紳,有的還用直平極淺階梯式衣紋,有的發展出新的突起線條,下部作稀疏的衣褶。
從以上所談的東漢時期時期觀音造型藝術上來看,它與漢代雕刻藝術有著明顯不同,在技法上吸收了印度犍陀羅的藝術,而有了新的創造,與東漢時期的觀音造型有著跨時代、在技法上有著顯著的直平刀法的變化,裝飾上的漢民族形式的變化為后期觀音造型奠定了基礎。
二、浮雕、圓雕成為古沉木觀音雕刻常用等技法
古沉木,又稱烏龍木、烏蛀木、沉木、炭化木、東方神木等,系古時沉于水土之中,現代采砂石挖出的木材。據可靠資料分析,遠古時期,原始森林內密度重的大片名貴木材林,受地震、山樸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災害侵襲之后,木材被深埋于江河、湖泊、近海底。上檔次的古沉木根雕,具有很多雕刻工藝品所沒有的大氣與收藏價值。烏木在市場上較為珍貴,素有“家人黃金萬兩,不如烏木一方”之說,更推動了當代古沉木根雕朝“犍陀羅樣式”發展的趨勢。
現代古沉木觀音藝術品,造型與雕刻同等重要。特別是頭、臉部位最為重要,深、淺浮雕的刀法應用要得心應手。從傳統來分,浮雕在業界包括淺浮雕和深浮雕兩種。淺浮雕,在雕刻過程中,首先通過依照材料,構畫出圖案,然后用平刀刻出輪廊線,打好底稿,再將輪廓線的外圍刻低并平整,也就是把需要表現的對象凸出之后,再加上細部雕刻,例如刻發絲和耳部較細薄部位,表現技法用淺浮雕比較適宜,淺浮雕具有流暢的線條及清淡、雅凈的藝術效果。深浮雕:深浮雕是介于鏤雕和淺浮雕之間的一種表現形式,深浮雕和淺浮雕的區別在于深浮雕突出平面的高度較大,也可看作是淺浮雕的基礎上加強深度,所以有人把深浮雕稱作為半立體雕。例如刻一件薄衣衫可用淺浮雕,而雕刻出一件棉大衣就加大深度,這樣才能表現出棉大衣的層次感與厚重感。
圓雕:也稱立體雕,圓雕作品隨著觀看角度的不同而改變形態,每一個角度都具有立體感,古沉木觀音中的圓雕作品,一般取材于宗教人物。如觀音、八仙、彌陀佛、十八羅漢頭像等;也有歷史人物,如關公、孔子等。圓雕的制作先是從上、下、四周的表里逐層深入進行雕刻,雕出對象的粗坯后再進一步刻細膩,使用刀之氣勢雄渾,恢恢乎游刃有余,易若庖丁之解牛“神遇而不以目視”。
鏤雕:鏤雕又稱通雕,是核雕藝術中的常用技法,它吸收了圓雕,浮雕和繪畫的優點,鏤雕是無底子通體穿透,也是多層次的鏤空。鏤雕可分為立體和平面兩種,立體鏤雕實質上是圓雕的四面表現手法。例如雕刻觀音的手部、花瓶整及胸部的花飾,基本以圓雕為主(即立體雕)。
西方人稱“古沉木”為“東方神木”,它是有生命的。“自然,自在已然得大存在”是范曾先生對自然的定義。藝術則是摹品的摹品,現代古沉木的觀音雕刻藝術品,借鑒東漢以來的歷代變化,再根值于當下的藝術創作之中,把天真的、樸素的古沉木造型巧妙借用,使作品本身在意象上、神韻上、性靈上體現的淋漓盡致,生拙和鮮活并在,懵懂和靈慧齊飛,從他神秘的古沉木雕作品中可以看出來自亙古天籟的真誠。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描繪的“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的神性意境。古沉木雕藝術與其他當代藝術表達的媒介載體有所不同,它是運用自然造化所形成的自然本身和人創想融合,是一個天工和人工匯合的語境,這語境不僅僅是藝術家對自然形象的描摹,也是對自然作理性的歸納,更有助于把古沉木觀音作品走向高雅藝術的殿堂
參考文獻:
[1]鄭劍夫:<古沉木與古沉木雕>、<中國古沉木雕的藝術特征>
[2]孫布衣<如何區分“慈航道人”與“觀音菩薩”>
[3]張亮宗:<嵊州古沉木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