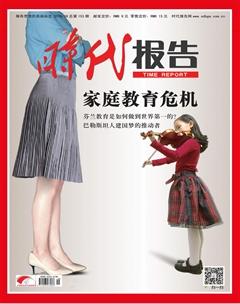陳光中:立言致公
林迪
直到今天,陳光中還會滿懷深情地唱起那首他少年時代在戰火中學會的抗戰名曲《松花江上》。
然而,陳光中卻不是東北漢子,而是地地道道的江南書生。上個世紀30年代,他生于浙南永嘉縣白泉村,家門前也有一條江,溪曲峰疊,潭澄沙凈,喚作楠溪江。但未及小學畢業,侵華日軍攻占溫州,打碎了他少年生活的平靜。
“滿門忠烈,熱血報國。”言及那段歲月,陳光中有些激動。陳家是當地的開明士紳,家族的耳濡目染,加上目睹日軍暴行,使救國的激情郁結在他的心中。
“法律救國,年輕時我有種朦朧的感覺,這是使國家振興的道路。”陳光中說,“慮及條件與志趣,當年便立志要做個‘立言者。”
遲來的黃金時代
人生總是充滿無數的意想不到,立志做“立言者”的陳光中,在他的機遇來臨之前,竟等了數十年。
陳光中少時天資聰穎,開蒙甚早,一邊白天在校學習,一邊晚上回家隨得過前清功名的堂伯父讀“四書”、誦古文。初中畢業后以第一名的成績升入高中,而后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陳光中的求學生涯可謂順風順水。
北大畢業后,陳光中因學業優秀留校任教。恰逢此時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法律系和政治系,燕京大學的政治系以及輔仁大學的社會系合并,成為今天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陳光中便隨北大法律系的全體師生調整到那里,參與了學校的創建。
正是在北京政法學院,陳光中被分配從事刑事訴訟法學的教學工作,自此與之結下一生的不解之緣。
然而,此后幾年間勤于鉆研的陳光中,剛剛在學術上嶄露頭角,卻于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被錯誤定性為犯嚴重“右傾”錯誤,人也被調離了政治性強的法律業務教研室。
陳光中在此后數年先后教授過法制史、中國通史和近代史,“幸好我古文有功底,又愛好歷史,倒也自得其樂”,但畢竟壯志未酬,心中戚戚難安。
1982年秋,當陳光中重返法律教研崗位,擔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任刑法室主任時,此時的他已過知天命之年。在本是守成的年紀上,陳光中卻幸遇了他實現“立言者”理想的時代機遇:國家經過撥亂反正已經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一片欣欣向榮,法制建設更是百廢待興,亟須人才。
“時不我待,只能夜以繼日地工作,恨不得把前20年蹉跎的歲月都彌補回來。”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成立,陳光中調回該校任研究生院副院長;1992年,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2001年,被聘任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期間,主編或合著出版了50余部著作,發表200余篇文章。如今陳光中已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
建議“疑罪從無”入法
陳光中提起他一生治學值得銘記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為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鼓與呼,另一件是晚年對訴訟價值的韌性堅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家急需制定基本法律以結束當時“無法可依”的局面,而1979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正是當時最早開啟法治化歷史進程“閘門”的法律之一。但由于制定時間的倉促和歷史條件的局限,其理念與模式已落后于時代,因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呼吁盡快修改完善這部法律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
“當時,我與博士生合寫了一篇刑訴法修改的論文,論文要點上報后,得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的重視。”陳光中回憶道。不久,當時身為校長的陳光中組織起學校里的骨干力量,在調研、考察的基礎上,起草出了《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送立法部門參考。
1996年,經過各界反復討論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被八屆全國人大順利通過。新的刑訴法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更突出了人權保障,在審判模式、強制措施、律師辯護制度等方面都較前法有了重大突破。
然而,這樣的進步卻來之不易,陳光中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疑罪從無”原則入法背后的曲折。
據陳光中回憶,全國人大法工委向專家學者征求意見時,他起初主張一步到位確立“無罪推定”的原則。但是這樣的重大轉變當時面臨著巨大的阻力,難為實務部門接受,導致后來連讓了一步的“疑罪從無”原則也遲遲沒寫進修改草案中。
1996年,刑訴法成功修改后,國內外對這部法律高度贊譽。
作為一位研究刑訴多年的法學大家,陳光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民主法治國家,這是我年輕開始學法律時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我一生治學的指針。我力圖通過自己的法學學術活動,促進我國的民主更加發展,法制更加健全,人權更有保障。經過反‘右斗爭和‘文化大革命,我更深切感到中國要繁榮富強,必須加強民主法制建設,走依法治國之路,在維護人權方面下大力氣。這種歷史的使命感推動著我、鞭策著我不斷地為改革開放、民主法制作不懈的努力。”
“立言者”的堅持
陳光中的學生、如今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的張建偉,曾這樣撰文評價他的老師:“陳光中先生在訴訟法學界聲望極高,但他的學術觀點卻并不都占主流。”
“法學家做學問不能只在書齋中坐而論道。”陳光中堅持刑訴法是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不該一味追求理論的新奇,理論“失之毫厘”,司法貿然行之就會“謬以千里”,甚至會錯枉無辜。
陳光中的獨特之處,就是對程序正義和客觀真實的認識。
我國刑事訴訟立法、司法乃至學術研究,曾長期忽視程序正義對于保障人權的特殊價值。后來學者為糾其偏,又極力推崇程序正義的價值。陳光中同樣也是程序正義的支持者,但他卻敏銳地意識到,過分貶低實體公正、拔高程序公正,就要埋下以程序正義掩蓋實體正義、為實體不公尋找遁詞的隱患。
“實體目標不存,程序過程何往?”他看到當事人耗時費力打官司,并非只求感受“有人做主”,也看到當事人上訴、申訴、上訪,通常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在中國,司法不重視實體公正,將成為社會不和之源,民眾怨府之所在。”
在陳光中看來,學界對于客觀真實的否定也將帶來類似的后果:他承認民事訴訟中法律真實的空間更大,但刑事訴訟事關財產、自由與生命,應當將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如果只滿足于訴訟的表面功夫,而不再以努力發現案件真相、實現司法公正為尺度,訴訟將淪為比拼玩弄法律技巧的競技場,不合于司法規律。
陳光中如今更多思考的是,中國的法學該如何對待本國的實際國情與文化傳統。他心中理想的模式是將西方法律制度的有益因子引入中國并與中國本土資源相融合:“我喜歡梁祝協奏曲,中國故事與東方旋律,卻由西方的小提琴來演繹,這樣的中西合璧不能給我們法學研究與司法改革一點啟迪嗎?”
如今,年已86歲高齡的陳光中,依然在為“立言”而忙碌。去年7月,陳光中受邀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法律學科的主編,詞條要求比第二版擴充2倍以上。對于擔任主編,陳光中說,“擔子很重,但也很有意義,我將盡最大努力把它做好。”
編者:陳光中,1952年7月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之一,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和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2016年5月7日雷洋案發生后,陳光中接受采訪時表示,受到質疑的公安機關自己發布信息違背法治原則,建議此案由更高級別的檢察機關——北京市檢察院來主導調查,最高檢察院應督辦此案。在雷洋案中發聲的法學界人士不少,但是像這樣高齡的法學泰斗仍然關注小人物而且發言的并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