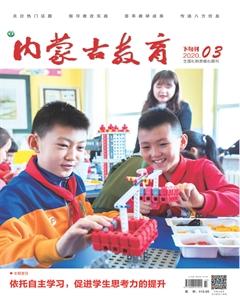探究小學數學問題意識的可持續性發展的培養策略
郁留紅
摘 要: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其對小學數學學科的教學要求不斷提高,傳統的小學數學課堂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現階段的教育改革發展需求,無法為小學生提供科學、合理、高效的教學服務。在此種背景下,小學數學教師要認識到數學學科的探索性與邏輯性,有計劃地培養學生的問題思維,幫助他們持續發展問題意識,從而提高小學數學教學質量。本文結合實際教學經驗,對小學數學問題意識可持續性發展的培養策略進行了深入探究。
關鍵詞:小學數學;問題意識;可持續發展;培養策略
現階段,小學數學課堂教學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學生問題意識可持續發展的培養,不利于提高小學生的數學綜合能力,其主要體現為:學生缺乏獨立思考意識、缺乏數學學習興趣,課堂教學模式較為落后。
針對這些問題,小學數學教師要正確認識到問題意識對于小學生今后發展的重要價值,認識到其對于小學生學習數學的重要意義;還要積極轉變課堂教學觀念,創新課堂教學方法,引導小學生的思維發展,培養小學生的問題意識,鍛煉小學生的提問能力,從而實現問題意識的可持續性發展。
一、問題意識在小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過去的小學數學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是課堂教學活動中的“主人”,是學生思維的“主導者”,由教師負責提出問題、布置任務,學生負責學習教師講解的知識,完成教師提出的任務。這種教學形式與我們所提倡的“以學生為本” “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等教學理念背道而馳。
小學數學教師要勇于面對現階段教學中存在的不足,踐行先進的教學理念,“活化”課堂教學,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成為課堂的主要活動者,因此,培養學生形成良好的問題意識,是必然的選擇。小學數學教師要在掌握學生實際情況之后,結合教學內容,優化課堂教學設計,讓小學數學課堂教學活動更加生動、有趣,讓小學生敢于提出問題,有空間提出問題,愿意提出問題。
二、小學數學問題意識的培養情況分析
首先,在當下的小學數學課堂教學中,由于數學知識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缺乏直觀、具體性的參考,小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無法理解數學語言、無法掌握數學知識的情況,無形之中加大了學生學習數學的恐懼心理,不利于學生提出數學問題。
此外,一些數學教師沒有真正理解“新課改”教學理念的含義,在課堂教學中生搬硬套教學形式,導致課堂教學內容雜糅,教學手段單一,不利于學生吸收數學知識,還會進一步加大學生的學習困難,導致學生產生“知識點混淆”的情況,降低了課堂教學水平。
其次,教師仍然無法完全擺脫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沒有在教學活動中凸顯出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小學數學教師更加關注班級學生是否認真聽講、是否認真做筆記、是否能夠集中注意力、是否能夠執行教師的指令等問題。落后的傳統教學思想束縛了小學數學教師的教學思維,導致小學數學教師在課堂教學活動中的態度過于嚴厲,長此以往,小學生會形成“老師說的都對”“老師說不對就是不對,雖然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對”的錯誤思維,對教師產生較為嚴重的依賴性,缺乏自主思考能力。
最后,隨著年級的變化,小學數學的學習難度逐漸增加,數學知識愈發抽象化,小學生正處于思維發展時期,具備較強的感性思維,缺乏邏輯思維與理性思維,無法很好地理解數學知識。若教師不能夠進行有效的引導,則會引發學生產生厭學心理,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導致學生數學學習熱情不高。
三、小學數學問題意識的可持續性發展的培養策略
(一)構建輕松的課堂學習氛圍,引發學生質疑
小學數學教師要想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就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為學生營造學習環境,讓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學習數學知識,引發學生的疑問,促使學生積極主動提出問題。
在現代社會中,傳統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小學生的學習需求,要想幫助小學生盡快成長,促使其進步,就要調整教學方法,讓小學生心甘情愿地投入數學學習中,引導小學生主動思考,在思考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提出質疑,邁出形成問題意識的第一步。
在《認識除法》的課堂教學中,教師需要結合相關事例,引導學生理解、掌握除法的含義,認識除法算式中各個部分的名稱與作用,能夠初步運用除法解決問題。若教師僅僅是針對教材知識點進行講解,這需要學生具備較強的聯想能力與抽象思維能力,然而,二年級的小學生并不具備這些能力。因此,小學數學教師要引進“數形結合”理念,將蘋果、梨等物品引入課堂,吸引小學生的注意力,避免小學生產生學習緊張心理。此外,教師還要通過輕柔、溫和的聲音引導小學生思考,讓小學生感受到教師的善意,舒緩小學生的心理,為小學生營造一個有趣、輕松的課堂環境,從而引發小學生的思考,引導小學生提出“減法和除法不是都可以運算嗎”等質疑。
(二)結合實際生活,培養小學生形成問題意識
小學數學教師要想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就要善于發現小學數學知識中的特點,發現數學知識點與實際生活的密切關聯,充分利用二者之間的關聯,建立生活化教學情境,讓學生在熟悉的場景中展開思考,從而提出學習問題。
在《認識分米和毫米》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小學數學教師要結合本節課的教學內容——長度單位,引進相應的生活元素,將較為抽象的數學概念直觀地展現在學生的眼前,激發小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促使小學生積極主動地進行數學探索。
教師可以分別引進鉛筆盒、桌子、書本、黃瓜、硬幣等不同的生活元素,讓學生利用手中的直尺分別測量這些物品的長度,并且進行回答,此時學生會回答:“鉛筆盒大約長20厘米、硬幣的厚度大約為1毫米”。教師要進一步引導:“請同學們結合手中的皮尺,量一量同桌的身高,并且大聲說出來。”此時班級內部就會出現各種“小明身高一米三”“小紅身高一米五”等不同的聲音,這時教師要抓關鍵點,通過“請同學們對比身高與硬幣厚度之間的單位與具體數字,并發現其中的相同與不同”等問題引發學生的思考,促使班級學生主動提出“為什么身高就是‘米,而硬幣就是‘毫米呢”的問題,從而引出各個度量單位之間的進率,讓學生在思考、探索、提問、回答的過程中獲取知識,掌握知識。
這種教學方法不僅能夠讓學生自主探索教學內容,還能夠不斷啟發學生的問題思維,刺激學生的感知,讓學生自覺產生問題,提出疑問,有助于培養小學生形成問題意識。
(三)創建教學情境,讓學生感受“提問”的樂趣
要想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小學數學教師要結合具體教學內容,創建問題教學情境,充分發揮小學生好奇心強、求知欲強的特點,創建有趣、新穎的問題情境,刺激小學生的思維,激發小學生的數學提問興趣,讓小學生感受到探索問題的樂趣,為問題意識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在《認識角》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小學數學教師可以通過故事情境進行導入:小朋友們,大家知道五星紅旗中的“五個星星”吧,這五個星星中有好多調皮的“角”,他們藏起來了,沒有讓我們發現。一天,小熊看到了“五個星星”,他說“五個星星”中,每一個星星都有5個角,小山羊聽到了之后就笑話小熊,認為小熊是錯誤的,小山羊說:“每一個星星都有10個角。”你們說,是小山羊的說法正確,還是小熊的說法正確呢?同學們,你們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嗎?通過這種情境導入引出了本節課中的“角”,利用故事情節將班級小學生的情緒調動起來,讓小學生主動投入到“數角”的過程中,并且腦海中不斷出現疑問:為什么小熊說有5個角,而小山羊卻認為有10個角,隨之產生想要提問、樂于提問的心理,并且在提問、探索、驗證問題的過程中體會到樂趣,從而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意識。
(四)精心設計教學問題,促進問題意識的可持續發展
在小學數學課堂教學過程中,小學教師要注意科學提出問題,精準引發問題,將小學生引入不斷的思考問題、發現問題、進一步提出新問題的過程中,鍛煉學生的問題意識,培養學生形成良好的獨立思考能力,促進小學生問題意識的可持續發展。
一方面,小學數學教師要結合小學生的心理特點與年齡特征,從教學內容的角度出發,引進能夠滿足小學生心理需求的元素,設計出具有趣味性的情境,促使學生主動融入情境中,讓小學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展開思考,享受學習的樂趣。
在《認識圖形》的課堂教學中,小學教師完全可以將籃球、鉛筆盒、三角形的飯團、魔方等通過多媒體展現出來,讓學生結合這組事物,列舉出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引導小學生進入圖形探索的情境中。經過思考之后,小學生會積極回答問題,如“桌子是長方形的”等,教師要對學生的回答給予肯定,并進一步提出問題:“列舉了這些事物,你們還有什么疑惑嗎”,讓班級小學生展開交流,并不斷提出“為什么正方形沒有更長的邊”等問題,進一步強化學生的問題意識。在這一過程中,小學生會提出很多并不具備價值的問題,教師不可以表現出不耐煩或輕視的神色,而是要始終保持態度溫和,對學生提出的問題耐心解答,鼓勵學生不斷提出問題,將“提問”變成課堂教學的常態。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問題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對于小學生數學學習之路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小學數學教師要將問題意識的培養貫穿于小學數學課堂教學全過程,有意識地引導小學生提出問題,逐步培養小學生形成問題意識,從而具備獨立思考能力,進而能夠自主發現問題、探索問題、解決問題、提出新的問題,為今后的數學學習生涯奠定堅實的基礎。小學數學教師要主動構建輕松的課堂學習氛圍,結合實際生活,創建相應的教學情境,精心設計并提出問題,從而引發小學生提出質疑,讓小學生感受到提出問題、探索問題的樂趣,促進問題意識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戴國雄.淺談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J].學周刊,2019,(29).
[2]李天紅.培養學生數學問題意識的策略研究[J].中國校外教育,2019,(26).
[3]陳金蓮.培養問題意識? 發展數學素養[J].課程教育研究,20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