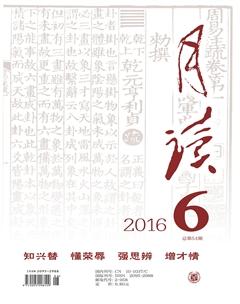小人物背后的大歷史
翦伯贊
王昭君在過(guò)去的史學(xué)家眼中是一個(gè)渺小人物,在現(xiàn)在的史學(xué)家眼中還是一個(gè)渺小人物;然而在這個(gè)渺小人物身上,卻反映出西漢末葉中國(guó)歷史的一個(gè)重要側(cè)面,民族關(guān)系的這個(gè)側(cè)面。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紀(jì)下半期漢與匈奴之間關(guān)系的全部歷史。
比起歷史上的大人物來(lái),王昭君確實(shí)是一個(gè)渺小人物,她在當(dāng)時(shí)不過(guò)是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gè)宮女。但是歷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著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個(gè)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為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gè)宮女,王昭君不過(guò)是封建專(zhuān)制皇帝腳下踐踏的一粒沙子;但作為一個(gè)被漢王朝選定的前往匈奴和親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個(gè)王朝、一個(gè)帝國(guó)、一個(gè)民族,并且承擔(dān)了這個(gè)王朝、帝國(guó)、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識(shí)得到或意識(shí)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根據(jù)歷史記載,自從漢高帝接受婁敬的建議與匈奴冒頓單于締結(jié)和親以后,他的繼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貫地奉行這種和親政策,先后與匈奴冒頓單于及其子孫老上單于、軍臣單于結(jié)為婚姻。在漢初70余年間,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lián)盟統(tǒng)治集團(tuán)之間,始終保持親戚關(guān)系。但是到了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由于馬邑地方的邊境沖突,這種世代的親戚關(guān)系,便宣告中斷。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到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昭君出塞之年,其間整整一百年,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lián)盟統(tǒng)治集團(tuán)之間,長(zhǎng)期處于戰(zhàn)爭(zhēng)狀態(tài)之中,而這種由雙方統(tǒng)治階級(jí)發(fā)動(dòng)的相互掠奪的戰(zhàn)爭(zhēng),不論誰(shuí)勝誰(shuí)負(fù),對(duì)于兩族人民來(lái)說(shuō),都是災(zāi)難。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絕和親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復(fù)中斷了一百年的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
在一個(gè)多民族國(guó)家的歷史中,兩個(gè)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說(shuō)不是一個(gè)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而王昭君在這個(g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說(shuō)不是一個(gè)重要角色。應(yīng)該指出,昭君出塞這件事,對(duì)于漢王朝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政策的轉(zhuǎn)變,即從戰(zhàn)爭(zhēng)政策回到和親政策。
和親政策,在今天看來(lái)已經(jīng)是一種陳舊的過(guò)時(shí)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會(huì)時(shí)期卻是維持民族友好關(guān)系的一種最好的辦法。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條件下,要維持民族友好關(guān)系,主要地是通過(guò)兩種辦法,或者是質(zhì)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后者就是和親。西漢王朝對(duì)匈奴的政策主要地是和親政策,只有在這種政策不能發(fā)生效果的時(shí)候,才采取戰(zhàn)爭(zhēng)政策。因此,他們對(duì)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視的。史載漢元帝為了紀(jì)念這次和親而改元竟寧,就是最好的證明。應(yīng)該指出,為了和親而改元,在西漢王朝的歷史上,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另外的資料也證明漢王朝對(duì)這次和親的重視。1954年在包頭附近麻池鄉(xiāng)漢墓中發(fā)現(xiàn)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wàn)歲”“長(zhǎng)樂(lè)未央”等文字的瓦當(dāng)殘片,據(jù)考古工作者判斷,這些瓦當(dāng)是屬于西漢末葉的。還有傳世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wàn)歲長(zhǎng)樂(lè)未央”等文字,這些單于和親磚,雖然沒(méi)有制作年代,但和瓦當(dāng)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屬于同一時(shí)代的。如果對(duì)這些遺物的年代判斷不錯(cuò),那么,這些印有“單于和親”的磚瓦,只能認(rèn)為是為了紀(jì)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yàn)樵谖鳚h末只有這一次和親,而王昭君則是最后出塞的一個(gè)姑娘。
事實(shí)的發(fā)展是符合于漢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后,漢與匈奴之間有50年左右沒(méi)有戰(zhàn)爭(zhēng)。一直到王莽執(zhí)政時(shí)期,由于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種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又要把大漢文明強(qiáng)加于匈奴人(如強(qiáng)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特別是為了確立他的政府對(duì)匈奴的政治從屬關(guān)系而更換“匈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才受到損害。
50年的和平,在歷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這50年的和平是與昭君出塞有密切關(guān)系的。當(dāng)然這種和平的出現(xiàn),不完全是王昭君個(gè)人的作用。作為一個(gè)個(gè)人,不論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論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轉(zhuǎn)移作為一個(gè)部落聯(lián)盟的匈奴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政治方向,至多只能從匈奴單于獲得對(duì)她個(gè)人的寵愛(ài)和信任。西漢初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diǎn)。在西漢初,盡管漢王朝不斷地與匈奴單于和親,但并沒(méi)有因此而免于匈奴部落貴族的侵襲,只是沒(méi)有使這種侵襲發(fā)展成為真正的戰(zhàn)爭(zhēng)而已。
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的恢復(fù),是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到公元前一世紀(jì)所形成的客觀形勢(shì)的必然趨勢(shì)。當(dāng)時(shí)的客觀形勢(shì)是:一方面匈奴已經(jīng)由于部落貴族之間的分裂而趨于衰落;另一方面,漢王朝也進(jìn)入了它的全盛時(shí)代的末期。在這種形勢(shì)下,雙方都無(wú)力發(fā)動(dòng)侵略對(duì)方的戰(zhàn)爭(zhēng),特別是雙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甚至一部分匈奴貴族也由于內(nèi)部矛盾的尖銳化而感到必須與漢王朝和解才能穩(wěn)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統(tǒng)治地位。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決定款塞入朝,和漢王朝恢復(fù)友好關(guān)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貴族左伊秩訾王為首的主和派的意見(jiàn)。
和平是歷史的必然趨勢(shì),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說(shuō)的“和親無(wú)益”的結(jié)論。不可想象,假如當(dāng)時(shí)的漢王朝拒絕與匈奴和親,單靠歷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動(dòng)地發(fā)展出50年的和平。
史實(shí)證明,在昭君出塞以前,這種形勢(shì)是存在的,但并沒(méi)有因此而導(dǎo)致和平,甚至在呼韓邪單于兩度入朝以后,漢王朝還不得不在它的西北邊境線(xiàn)上保持相當(dāng)?shù)能娛陆鋫洹?/p>
和親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史載漢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單于歡喜,“上書(shū)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wú)窮,請(qǐng)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雖然漢王朝沒(méi)有接受呼韓邪單于的建議,但從此以后,雙方都從思想上撤銷(xiāo)了仇恨的堡壘。燃燒了一個(gè)世紀(jì)的烽火熄滅了,出現(xiàn)在西北邊境線(xiàn)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煙。
一直到王莽執(zhí)政時(shí)期,漢與匈奴雙方還在利用王昭君的關(guān)系來(lái)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史載漢平帝時(shí)(1—5),王莽曾邀請(qǐng)王昭君長(zhǎng)女須卜居次云訪(fǎng)問(wèn)長(zhǎng)安。天鳳五年(18)匈奴單于又派遣須卜居次云及其婿須卜當(dāng)、兒子須卜奢,還有王昭君次女當(dāng)于居次的兒子醯櫝王(醯櫝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長(zhǎng)安。王莽把他的庶女陸逮公主王捷嫁給須卜奢。在漢王朝方面,也曾于天鳳元年(14)派遣王昭君的侄兒和親侯王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王颯出使匈奴,賀單于初立。天鳳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所有這些活動(dòng)都是通過(guò)王昭君個(gè)人的關(guān)系進(jìn)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這個(gè)歷史事件是標(biāo)志著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guān)系的恢復(fù),而王昭君在友好關(guān)系的恢復(fù)中起了很大的
作用。
〔節(jié)選自《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shuō)到昭君出塞》,載《歷史問(wèn)題論叢》(合編本),中華書(shū)局。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作者為我國(guó)著名史學(xué)家,中國(guó)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xu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