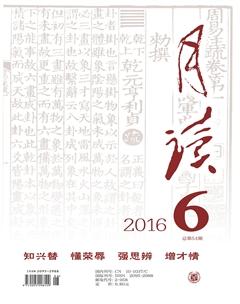南京城墻下的腳步聲
劉策
南京城的嚴月,也不比北方溫暖多少,伸出袖筒的手同樣會讓寒風咬得生疼,屋子里更是干冷極了。尤其是日落以后,這一分寒冷,更是“雪上加霜”。每到這個季節(jié)的傍晚時分,位于青溪與秦淮匯流處的淮青橋附近,那里的居民,就常常聽得見一陣陣紛亂沉重的腳步聲響起來;腳步聲是由三四個人混合奏響的,由那主人吳敬梓寓居的秦淮水亭里響出來,一路朝著南京城南門的城墻而去。
是的,那腳步聲里透著太多沉重的無奈,絕不是像有些人所說,是浪漫的、詩意的(因為吳敬梓等人行走在路上,唱過歌,吟過詩)。這顯然是寫作者的臆想。大概他們以為,作為文人的吳敬梓,和他身邊的那些個文人雅士,一定每天都應(yīng)該是浪漫的、詩意的。然而,歷史卻不是這樣。那時候的吳敬梓一貧如洗,有時常常缺油斷糧,連填飽肚子都困難重重,哪里還有多余的銀子沽酒取暖,圍爐小坐?于是,吳敬梓只好邀上幾個友人,走出秦淮水亭,走向位于南京城南方的城墻,一路徒步行走,只是為了能走出一身熱汗,走暖冷得不是滋味的兩只腳。這是當時貧窮的吳敬梓和他的朋友們,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能夠讓自己寒冷的身體暖和起來的方法了。不是也許,事實上正是這樣的。事后吳敬梓曾十分風趣且無奈地將這一段生活,稱為“暖足”。
當時,經(jīng)常與吳敬梓徒步“暖足”的有:江寧年青詩人嚴東有、徽州鹽商程晉芳。程晉芳雖說是當時的大鹽商,但卻酷愛詩文書畫。用現(xiàn)在時尚的話講,是個“文化商人”。對此,程作過這樣的文字記載:“壬申春,就試金陵,敏軒(吳敬梓字敏軒)偕東有來訪。其氣凝以深,叩所讀書,無不有。索所為詩,則謙讓不肯出。獨愛余詩,為作駢體序千余言。風晨雨夕,吾三人往來最密也。”
不錯,他們暖足的一路上,也時常會吟詩、歌唱、說笑。可是,這些依然與詩意、與浪漫無關(guān)。挨餓受凍的人哪來的這種心境和情調(diào)?所以,一讀到有人詩情畫意地描寫吳敬梓于南京這個時期“詩情畫意”的生活,我就會一閃念想起時下的某些矯揉造作的小資文章。真是滿紙的“虛情假意”!難怪讀者不堪卒讀。
吳敬梓在南京的那段歲月,其實是清苦的。正是這清苦的歲月,有助于他更加清醒地讀懂自己生活的那一段歷史與人生,寫出了千古不朽的經(jīng)典名著。
作為吳老先生的皖籍鄉(xiāng)人,對老先生的敬慕之情,常讓我的心里暖暖的。
每每偶讀這段歷史,或去南京出差、旅游時拜謁吳敬梓的故居,不由就會感覺到自己的雙足也會驀然間冰寒木然得難以名狀,就會既天真又幼稚地想:那時候秦淮水亭里要是有一臺空調(diào)該多溫暖呀!即使只有一個烈烈燃燒的火爐也是好的呀!現(xiàn)在細細想來,這實在是一種太淺薄的同情和感情了。倘若吳老先生那時的生活是富足的,真是有了這樣優(yōu)越的環(huán)境,也許我們就讀不到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儒林外史》了。
是“也許”嗎?
文學與人生的意義實在讓人琢磨不透——這大概便是她們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