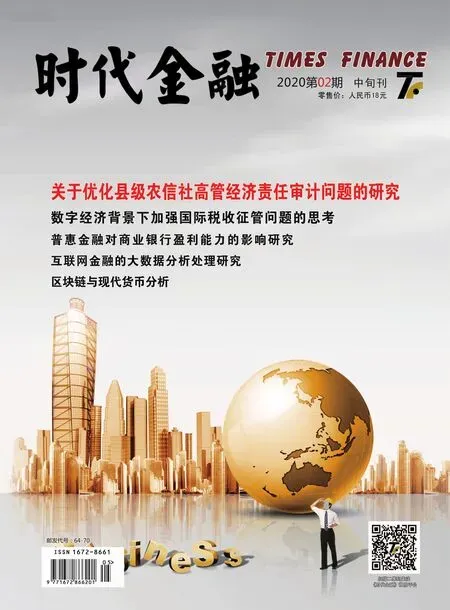中國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后的政策取向研究
【摘要】從2008年至2014年美國連續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應地作出了調整。本文從分析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期間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選擇出發,并結合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提出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能取向。
【關鍵詞】量化寬松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一、前言
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至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美聯儲正式開啟了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聯儲于2010年11月3日宣布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2012年美聯儲宣布啟動新一輪“開放式”的資產購買計劃(QE3)。三輪量化寬松對刺激美國經濟復蘇可以說成效顯著。美國的最新經濟數據較之最差的2008、2009年有了明顯的好轉,已于2015年12月正式決定結束QE,開始加息。本文試圖從分析QE對中國經濟影響因素入手,指出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取向。
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美國發動印鈔機應對危機的時候,中國等新興市場成為發達國家流動性泛濫的蓄水池,廉價的資本從發達經濟體肆無忌憚的流向新興市場,在帶來了不可持續的增長的同時,也吹高了資產價格泡沫。從GDP增長率來看,中國從2007年至2014年分別為:14.16%、9.63%、9.21%、10.45%、9.3%、7.65%、7.7%、7.4%。中國的經濟增長盡管也存在國內經濟結構不合理、增長模式單一、各種體制改革滯后等內部因素,但美國推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是重要的外部因素。由于中國是大宗商品的主要進口國,美國QE政策的推出,導致國際市場上石油及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暴漲,并很快會傳導至我國市場,從而對成品油價格及大宗商品價格造成上漲動力。從國際原油WTI價格變化完全可以看出這一點:2008年99.3美元/桶、2009年61.92美元/桶、2010年79.53美元/桶、2011年98.25美元/桶、2012年94美元/桶、2013年98.02美元/桶。
從實行貨幣政策來看,我國一直在推進的“穩增長”目標對國內現行的貨幣政策也形成了壓力。實際上,貨幣政策是繼續執行從緊政策還是適當放寬,央行表現得很謹慎。如果放寬貨幣政策,很可能實體經濟未曾受益,資產泡沫卻先行泛濫起來,通貨膨脹就會卷土重來;如果緊縮貨幣政策,又會對實體經濟帶來傷害。正是由于這樣的擔心,因此盡管經濟下行的壓力很重,但是央行卻未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以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來向市場釋放資金,而是以高頻的逆回購手段來增加市場資金的流轉。但總體上應保持足夠的流動性,亦就是偏松的貨幣政策。
從實行財政政策來看,利用財政補貼、減稅、放松市場準入等措施,降低進口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出口增速下滑對中國經濟供給面帶來的負面沖擊。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實施新型工業化戰略,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等方面發揮政策作用。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看,預期明確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發揮了積極作用。可以說,只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才能更好地消除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經濟的消極影響。
三、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宏觀經濟政策取向
筆者以為,應從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出發,在明確國內穩增長、調結構、去除金融杠桿,避免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維護匯率穩定,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的基礎上,采取更為務實和靈活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在當前情況下,應積極采取寬松的政策。首先,應以審慎和偏松為原則。要考量國際金融形勢的復雜性,既有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升值和美元回流的影響,也有日本、歐元區實行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作用。鑒于資本流出是未來的主要趨勢,要保持合理的流動性(M2的適度規模),支持經濟穩定增長。其次,要確保匯率在一定彈性下穩定。匯率穩定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前提條件。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是貶值,但同時相對于歐元和日元是升值,考慮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長期看,人民幣應處于不斷升值的過程中。在分析出口企業承受力的基礎上,維持人民幣匯率在一定區間內的波動,為人民幣國際化(成為世界性的儲備貨幣)創造條件。第三,適時運用各種金融工具,穩定市場預期。當前,人民幣貶值趨勢明顯,經濟增長乏力,主要經濟指數仍處于下滑之中,經濟增長有步入通縮的風險。為應對美國QE退出和日版、歐版新一輪量化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的沖擊,央行啟動降準、降息周期勢在必行。同時,利用多種金融創新手段加強常規調控,增強市場信心,確保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在當前的情況下,應繼續采取積極的策略,立足促進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與貨幣政策保持同方向的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首先,財政政策應在促投資、擴需求、強出口上積極作為。積極籌措資金,支持推進重大投資工程包建設;大力推廣PPP模式,引導社會資本加快進入公共設施領域;用好預算內投資,統籌預算內投資專項,繼續向農業水利、中西部鐵路、保障性安居工程、重大基礎設施、生態建設、民生、老少邊窮等領域和地區傾斜。優化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注重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大力支持養老健康家政、信息、節能環保、旅游休閑、住房、文化教育體育等領域消費工程建設,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利用有效的財政手段,大力支持和鼓勵勞動密集型、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利用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優勢,加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的進口,加大海外投資力度,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的有利時機,加快國家戰略物質儲備。其次,加快實施結構性減負計劃。在穩定宏觀稅負的基礎上,及時對進出口關稅進行調整,改革出口退稅制度,加快推進“營改增”和資源稅改革,做好開征房產稅準備,控制非稅收入過快增長。第三,支持培育新的增長點和重大戰略的實施。支持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引導產業集聚發展;支持以增強核心競爭力為重點加快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制造業競爭新優勢;支持加快培育新興產業,支持云計算與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工業設計、融資租賃等生產性服務業。支持“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新的增長極和支撐帶,整合建立統一規范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推進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促進沿線地區互聯互通、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馬紅霞,嚴洪波,陳革.《美國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武漢大學出版社.
[2]馬榮華.《人民幣與港幣雙向流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上海金融出版社.
作者簡介:李鶴為,內蒙古自治區財政科學研究中心,研究方向:財政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