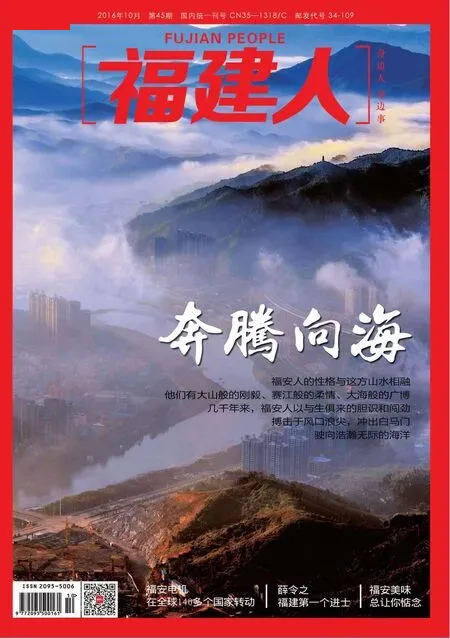唐代帝師薛令之:福建第一個進士
鄭琦琦
唐代帝師薛令之:福建第一個進士
鄭琦琦

薛令之回鄉后隱居于靈谷草堂,過著窮研經書、抱甕灌園的生活。但其志不移,他放棄功名利祿的舉動也并沒有影響到后人對他的敬仰。每年中考、高考時,廉村周邊學子都會被父母拉著在“后湖宮”薛令之的神像前祭拜許愿,希望得以“金榜題名”。
薛令之(683—756),福安市溪潭鎮人,唐代八閩進士第一人,朝中為官30余載,官至太子侍講,以清正廉明著稱,與謝翱、鄭虎臣并列“福安三賢”。 現存詩作有《自悼》《靈巖寺》《太姥山》《草堂吟》《唐明皇命吟屈軼草》《送陳朝散詩》等6首,前3首收錄在《全唐詩外編》中,《全唐詩》錄其《自悼》和《靈巖寺》二詩,后3首存錄于《高岑薛氏宗譜》。
科舉制度誕生100年后,福建終于出現了薛令之文破八閩之荒。得遇明主,使得薛令之的仕途生涯節節上升,可惜他忠心事主、清正廉明的作風,卻招致旁人所妒。
與古代大多數清官的遭遇相同,有所作為的仕途理想終究是要破滅的,在朝為官三十多載,薛令之最后不得不選擇離開政治舞臺。他與范仲淹、海瑞、鄭板橋等人一樣,歸隱山野,不問朝政。
薛令之是開閩第一進士,也是中國古今官員們廉潔為官的楷模,他留下的廉政思想影響至今。
一夜成名,文破八閩之荒
自科舉制度實施,100年間,福建竟然沒有人出仕為官,中原人士諷為“蠻夷之地”,直到薛令之登科及第,史稱其“文破八閩天荒”。
唐神龍二年春,薛令之北上京城長安應試科舉。同年年底,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回福建:23歲的福安人薛令之,通過了省試和殿試,皇榜高中了。
從隋朝大業二年至唐中宗神龍二年,自科舉制度實施以來,整整一百年間,偌大的福建地區竟沒有一個人“躍入龍門”,出仕為官,被中原人士嘲諷為“蠻夷之地”。直到薛令之登科及第,中國古代政壇才有了福建人的身影和聲音,史稱其“文破八閩天荒”。
“禮圍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劉禹錫這首描寫放榜之日情景的詩句,就反映了當時唐朝社會艷羨及第進士的盛況。
薛令之及第,得益于家庭的影響。他出生于世代官宦書香之家,他的先祖薛賀曾被南朝梁武帝授予“光祿大夫”之銜,后來為了逃避戰亂,舉家由中原南遷到福建,定居于當時溫麻縣西北的鄉村石津磯(今日的廉村)。
家族發展到薛令之這一輩的時候,已是家道中落,但并不影響他承襲祖風,以學為業的理想志向。廉村附近山間,曾經有一間十分簡陋的茅草屋,卻有一個儒雅的名字叫“靈谷草堂”,此處就是薛令之苦讀十載的書房。

薛令之號明月,廉村村口的明月祠便是為了紀念他而建(攝影/阮丹萍)
官至太子侍講
薛令之被提拔兼任太子侍講,從七品一下子升至四品,與著名詩人賀知章一起,擔任太子李亨的老師。
在唐朝,中進士只是拿到了做官的資格而已,若想真正獲得官職,還必須經過一番歷練。由于年代久遠,史料匱缺,關于薛令之入仕的具體細節,現在已經無法得知。
后人根據史料分析:按照唐朝的“辟署制”(后名“守常選”)制度,及第后的薛令之可能是先入幕府或漫游山川,然后通過吏部考試才入朝為官。
唐開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恢復諫官議政制度,一時之間朝野從諫如流。脾氣耿直忠厚、敢于諫言的薛令之因此得到了朝廷重用,被授予“左補闕”諫官之職,手握規諫皇帝、糾正朝政、彈劾百官的權利。開元十六年七月,朝廷舉行“冊太子”典禮,薛令之被提拔兼任太子侍講,從七品一下子升至四品,與著名詩人賀知章一起擔任太子李亨的老師。
唐玄宗當政時期,國家雖然呈現出一派盛世繁榮的景象,但宮中卻暗涌著一批奸佞之臣。以宰相李林甫為首的群黨,利用唐玄宗的信任,欺上媚下,專權誤國。對于李林甫的所作所為,薛令之更是十分憤慨。
有一天,唐玄宗命薛令之作一首關于“屈軼草”的詩,意在鼓勵大臣們直言諫諍。“屈軼草”相傳是諫官的象征,可以指出奸佞,又名“指佞草”。于是,薛令之便乘機在詩中借題發揮,斥責以李林甫為首的群奸,以盡諫官之責。
這首詩就是后來被收入《全唐詩》的《唐明皇命吟屈軼草》,詩中的“綸言為草芥,臣為國家珍”至今仍被后人廣為傳頌。
東宮吃牧草,直言觸怒君顏
到了開元中后期,唐玄宗終日沉迷于雞犬聲色,助長了李林甫等人的囂張氣焰,惹得朝野怨聲載道。
由于太子李亨與李林甫不和,薛令之又任職于太子東宮,因此經常受到李林甫排擠。李林甫看見薛當眾作詩影射自己,對其懷恨在心,想方設法處處刁難,薛令之的俸祿被一再削減,生活十分清貧。
一日用餐,薛令之發現所有人的盤中菜肴,竟是由苜蓿所制,不禁百感交集。苜蓿是喂牛馬的牧草,若非貧困至極,極少有人拿來制成菜羹。想到李林甫變本加厲地故意刁難東宮,一向耿直的薛令之憤慨之下,在東宮墻上題了《自悼》一詩:“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
唐玄宗在一次巡視東宮時,偶然看到此詩后大怒,認為薛令之是在嘲諷他昏庸無能,便在詩旁寫下:“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并“復題”四個字——“聽自安者!”意思是,既然你已經對朝廷心懷不滿,那么就不必留在此處了。
至此,薛令之對官場徹底心灰意冷,隨即托病辭官返鄉。臨行之前,他擔心官場風波險惡,讓在江西安福當縣令的兒子,也辭官回歸故里。薛國進聽從父命,與薛令之一同回到了福安。
后來,薛令之與苜蓿的這段故事,被陸游用到詩句“苜蓿堆盤莫笑貧”里面。而“苜蓿盤”一詞,也被歷代文人墨客們,形容官員清貧卻廉潔不阿的高尚品格。

一生清廉,故里被唐皇賜名“廉村”
為了嘉許恩師一生不畏權貴,清廉節儉,唐肅宗特賜他的故鄉石磯津為“廉村”。
薛令之能夠被世人懷念千年,除了“開閩第一進士”的功名之外,最主要的是他一生清正廉潔。
據史料記載,薛令之在京城長安為官長達30余年,直到最后離開京城,也沒有從宮中帶走一金一銀。辭官之后,從長安回福安老家的路程長達數千里,年邁的薛令之硬是靠著自己的一雙老腿,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回了家鄉。
唐至德元年,唐肅宗李亨即位。他感念昔日師生情誼,下旨召薛令之回朝復官。只可惜圣旨來得太晚了,薛令之早在幾個月前,就已溘然離世了。
為了嘉許恩師一生不畏權貴,清廉節儉,唐肅宗特敕史稱“三廉”,即其故鄉石磯津為“廉村”,溪為“廉水。”山為“廉嶺”,“首登黃榜自古八閩無雙士,帝賜廉名至今華夏第一村”。薛令之故里廉村,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以“廉”字命名的村莊。
受到薛令之的影響,從唐代到清代,廉村先后出了30多名進士,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進士村”。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