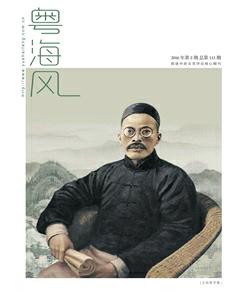批判是向上的助推器
蔡毅
早年讀到尼采說:“沒有一個藝術家是容忍現實的”時,[1]我似懂非懂不太認同。后來讀到薩特說:什么是創作?創作就是對生活的反抗。他還提出了“作家的責任及其對讀者的特殊使命就是揭露不公正”,“文藝應當介入生活”等戰斗口號,逐漸理解文藝不光是為了發出火光照亮生活,還是為了批判丑惡反抗生活,總之都是為了人類能夠更加有尊嚴、更加自由而美好地生活時,覺得心悅誠服了,并相信對社會現狀、現實生活的反抗與批判是文學的一項重要功能、神圣使命。
尤其是當聯想起魯迅先生是第一個揭露幾千年中國歷史雖然寫滿的是“仁義道德”,而其實全是“吃人”的歷史,他將一部中國歷史分成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兩種狀態的反復循環。他說:“……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2]先生不愧是具有最硬骨頭的勇士,是敢于向一切社會黑暗勢力、丑惡現象展開殊死搏斗的猛士,他用如椽巨筆,獨自挑戰整個世界,與世間一切愚昧、昏庸、貪腐、欺詐、瞞騙、虛偽、懦弱、茍且展開不屈不撓的鏖戰。其超越時代的清醒,永不妥協的尖銳,無可比擬的犀利,將文學的批判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讓我想到文學之一大功能是揭示歷史和社會真相,用文字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醫治昏聵、麻木、盲從與恥辱健忘癥,幫助民族健康成長。
顯而易見,在文學價值的建構中,批判性是整個系統工程中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一維。批判是讓所有價值元素活潑運轉起來,介入歷史、文化,介入現實生活的強大助推器。幫助文學針砭時弊、指斥丑陋、懲惡揚善、糾正世道人心。是的,批判是與肯定、贊美、歌頌相反的方法路徑,它通過否定一切惡的、壞的、病態的、中庸的、鄉愿的東西,而呼喚一切美好的、健康的、明朗的、自主的東西。青年作家葉舟說得好,他認為:文學的使命和道義在于:“道出真相,把全世界的耳朵都喊醒……讓自己變成一枚尖銳之針,刺破那一層虛妄的薄膜和外衣,怒放,突兀,長嘯,孤身犯險地漫唱一回。”
批判性出自批判性思維,即以否定性為主的思維。倘若把人類思維分為肯定與否定兩種或兩極,那么兩極思維相連相通,有時平行運演有時交叉作用,既互為補充又相反相成,缺一不可,從不同方向推動著人類思維的運動發展。肯定性思維是以贊同、鼓勵為武器,承認、支持和維護現狀;否定性思維則是以懷疑、質問、揭露、批判為武器,號召人們要打破現狀,求取更好的命運。若一味肯定或一律否定,就容易走向偏頗極端,走上荒謬之途。唯有依據對象和實際情況,對癥下藥,在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不斷依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思維,才能事半功倍與時俱進。關于批判性,法蘭克福學派有過比較精深的研究。這個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哲學學派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批判的基礎上。他們主張:文學或者理論“更多的是批判性而不是肯定性的”。馬爾庫塞說:“只有當形象活生生地駁斥既定秩序時,藝術才能說出自己的語言”。[3]在他們看來,作家天然就有對生活的反叛精神。其中的代表人物阿多諾堅持真藝術應表現社會的不公與人類的痛苦,以及人類的暴行給大自然帶來的災難。為此,他要求藝術保持一種否定與顛覆的能力,成為社會的“一種救贖”。他針對黑格爾“整體是真實的”命題提出“整體是虛假的”的口號,以摧毀社會強加于個體身上的總體性枷鎖,反抗社會對人性的禁錮。按照他們的理論,作為人的一種精神存在方式,文學幾乎從來就是站在生活的反面,監管與糾正生活的。這個過程始終需要否定,需要批判。只有通過否定與批判,才能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張揚人性的良善與純美,使社會保持高蹈的理想,成就其獨特而不可湮滅的價值。
過往的時代不談,僅論當下之中國,那也是正處在一個善惡并存、問題成堆、文化觀念多元混雜的時代。全球化、現代化的推進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人們物質生活的貧困,但“一切以經濟為中心”也帶來了金錢至上,物欲至上,急功近利見利忘義等多種弊端。盲目追求經濟指標,使得我們的大地山河飽受創傷,環境污染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喪失信仰,使一些黑心惡膽的不法之徒將食品、藥品、教育、衛生變成牟利工具,坑人害人。道德迷失,使得很多人顛倒是非、善惡不分,重當下輕未來,喪失生活目標。不少人沉迷浮淺娛樂,告別閱讀,再也不會抬頭仰望星空。人人都對現狀不滿,可又少有人起而反抗,從改造自身做起,投身棄舊圖新的事業。身處這樣的環境,需要批判的東西實在太多。比如批判貪腐猖獗,在嚴重毀壞我們社會的根基;批判奢靡浮華的風氣,在毒害銷蝕著我們民族的斗志;批判得意洋洋的消費主義,在操縱時尚操控人們的欲望;批判公權的濫用,在傷害著民眾的信任;批判日益膨脹的私欲,在吞噬著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批判沒有原則的虛無主義、批判毫無責任感的犬儒主義、價值相對主義。批判不求進取的庸人哲學,批判碌碌無為的蒙昧主義,批判一團和氣的世故習氣,批判“審美欲望化”、“藝術娛樂化”、“趣味低俗化”等文壇的惡風濁浪……問題如山,多不勝數。對于中國和文壇所有這些存在的毛病,批判像一把利劍,刺向一切欺騙、虛假與謊言。批判像一根鞭子,在嚴厲抽打著人類的劣習,督促著人們改過自新。批判像一記警鐘,在告誡狂妄自大的人們,多反思自省,別驕縱妄為。因此批判與質疑既是一種必須倡導的工作方式與思維習慣,亦是一種良好的精神品質。
1、批判藐視一切“非法的暴君”,敢于向威權發出挑戰。
批判需要以一種否定性態度質疑現實,分析社會,挑戰人生,因此其真正的工作就是:“揭示、論證、暴露真相,把神話和偶像統統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4]這需要非凡的勇氣、膽識與睿智。勇氣膽識是一種藐視一切權勢、權威及一切不合理現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猛精神。不畏懼權貴,不依附資本,也不尾隨體制,對一切現象、事件,都具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獨立見解。“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5]他掀開人肉的筵席,走出“瞞與騙的大澤”,為尋找事實真相,探究社會規律,表達真實感受,而投入長久的戰斗。劉醒龍說過:“面對泥沙俱下的種種潮流,敢于激浪飛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職。”[6]因為批判痛恨一切丑惡的現象和行為,藐視一切非法的暴君,批判是一種除惡劑。
勇氣和膽識是批判的基礎,但批判最根本的要靠見識與睿智。認得清識得透加上智慧的表述及應對方式才能保證批判的精準、正確和有效。惠特曼的詩句:“毫無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繁華的城市卻充斥著愚昧”一讀便縈繞胸懷,讓我想到自己怎么就不及別人目光銳利,思想深刻。在當代作家中,韓少功是一位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作家。他對全球化、市場化、民主與憲政、消費時代、大眾文化、道德風尚與人文精神多有涉獵,縱議古今,宏論滔滔。一次次將矛頭直指媚洋、媚權、媚俗的時代病相,不斷發出警策時政的獨特聲音。張承志則以另一種個人方式抵抗流俗,堅守批判性的價值立場。在這個四處鶯歌燕舞的社會中,張承志的否定性姿態十分可貴。他總是果決銳利,從不首鼠兩端、閃爍其詞,始終坦蕩真誠、獨立不倚。他總想借助回族血液中頑韌剛毅、孤傲強悍的因子,彌補漢文明中圓融無礙、中庸世故的先天不足。“他總是想憑自己振臂一呼,喚醒在燈紅酒綠中昏睡的庸眾。”[7]他們都以筆為旗,揭示真相,倡導書寫有尊嚴的文字,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特立獨行的思想立場和精神信念,令人敬佩。
胡風先生早就說過中國作家都帶有精神奴役的創傷,該說的話不敢說,不情愿說的話又敷衍地說。嚴酷的政治斗爭與思想鉗制使絕大多數作家精神受閹割,思考受限制,靈魂欠風骨,喪失了自我意識與權利意識。膝蓋骨總是軟的,老是匍匐在權勢之下站不起來,變成了時事政治的傳聲筒,歌功頌德的大喇叭,唯唯諾諾的跟風者,身體與精神都處于被雙重奴役的狀態。現今真正的批判要展開,首先需要自我意識、權利意識的覺醒,更需要獨立思考,自做主宰,只認真理,而不管什么個人利害的獨立自由狀態。批判是出于俯瞰時代歷史而獲得真知,是火眼金睛的深刻認知,力透紙背的厚積薄發,而不是信口胡謅、隨意褒貶。“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為也。” 批判靠的是“忠信篤敬,抱道而居”[8],是以清醒冷峻的理性燭照陰影與黑暗,它要求作家離開人云亦云的隊伍,避開擁擠的流行思想大道,既不迷信別人的見識言論,也不盲從上級的指示命令,只對自己負責,對真理負責。它勇于探險,一意孤行,決不妥協,決不曲媚,也不憚貧困孤苦,即使身居社會的邊緣,也拒絕膚淺的歌頌,而要進入思想的深處與遠方,去挑戰權威,戳穿謬誤,揭露欺騙,刺破各種偽裝,用批判突破各種思維屏障,讓思想沖破牢籠。
尤其是面對當前信仰缺失、理想淪喪、崇高遭嘲諷,歷史被惡搞,解構名人,顛覆常識成風,惡趣味、惡俗到死之際,批判必須仗義執言大顯身手,決不當隨波逐流的浮萍,不做潮流的跟屁蟲,而要發揮其促進人類進步,樹立文明“風向標”的作用。桑塔格說:“把自己看作是一場非常古老的戰役中一位披掛著簇新盔甲登場的武士:這是一場對抗平庸,對抗倫理和美學上的淺薄和冷漠的戰斗。”這種姿態異常可貴,值得我們大力提倡。
2、批判不僅是矛頭對外的,也是矛頭對內對自己的。
矛頭向外,批判社會和他人相對容易;矛頭向內,反省和批判自己則困難得多。莫言說過他的寫作有時是“將自己當罪人寫”,是通過寫自己的內心,吸納批評,排出毒素。他說:“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內心陰暗困難。批判他人筆如刀鋒,批判自己筆下留情。這是人之常情。作家寫作,必須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須與人之常情對抗,因為人之常情經常會遮蔽罪惡。……敢對自己下狠手,不僅僅是懺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鏡盯著自己寫……”[9]通過寫作來驅除魔鬼——私欲、物欲、貪欲,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查根源,是一種非常難得的品質,自己能克服自身的毛病,就能更加看清別人的問題,從而也更易去糾正錯誤,根治疾病。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我們就是我們所創造的觀念的俘虜”。這意味著很多時候人是自己誤導自己,自己坑害自己。按照這一思路,每個人都會受流行的時代風潮、理論觀念蠱惑支配,將謬誤當真理,將真理當謬誤,戴上一副有色偏光眼鏡去看世界。今日流行階級斗爭學說,就用階級理論去打量世界,區分敵我友;明日流行斗爭哲學,又嘗試用斗爭觀點去看待事物,判斷是非立場。后天由于反對自由化,又稀里糊涂地投身反對自由的行列。反復的灌輸與被灌輸、洗腦與被洗腦,使個人的頭腦變成別人的跑馬場和垃圾桶,自己卻一無主見,成為人云亦云沒有任何理論或原則標準的傀儡和空心人。以這種觀念先行、意識謬誤的態度審視生活、藝術,不僅感覺會錯亂缺席,也會喪失獨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若想自己的批判準確、深刻、犀利,首先得從解剖自己開始,不掩飾,不推諉,先將自己識透認清,才能突破個人思想的牢籠,推己及人并毫無顧忌地指點江山,坦然面對整個世界。試設想,一個連自己都不敢正視與批判的人,你怎敢相信他的批判?反之,如果連自身的缺點都能毫不留情地揭發批判,那么對他人和世界的批判自然就可信多了。魯迅先生曾從《一件小事》中看到皮袍下躲藏的“小我”,他毫不留情地對自己靈魂中的陰暗面進行拷問,自揭心靈中存在的“鬼氣”、“毒氣”,“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因此才能更加深透地認識國民劣根性,批判“精神勝利法”,徹底揭露舊時代是如何用瞞與騙坑人害人。巴金曾從對文革的懺悔反思中發現自己的病灶,“我犯過多少錯誤,受到多少欺騙。別人欺騙過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騙過我。不用說,我講過假話。我做過不少美夢,也做過不少噩夢”[10],他通過直面文革和歷次運動給自己人格帶來的扭曲,深刻反思不讓人說真話,及大量說假話對中華民族造成了創深痛巨的災難,從而勇敢地提倡“說真話”,并用自己真誠的懺悔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活下去”。“說真話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困難”,[11]這些發自肺腑的感悟,揪心牽腸,是自我批判、“自我救贖”的最好例證。由于具有這樣的思想認識,才保證了其后來的創作達到文學和思想的一個可貴高峰。
3、批判是一個健康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凈化器。
批判并不局限于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層面,還應對整個時代、社會、文化和文學提出質疑與批判,包括對權力、權勢及其附庸者的指斥和不容忍。詩人牛漢確信:“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的事業必須和社會生活的法則及其律動,以及推動并支持人類向上發展的生命的激發力結合起來。”其詩作才能“向太陽的有光/向真理的得真理/為了天堂出現,先入地獄”。“在牢獄里/頭發向上生長/骨骼也要向上生長”。[12]這種永遠向上的精神追求,是保證人類頑強前進永不墮落的根本。
當寫作被體制操縱,被利益集團綁架,被流行時尚裹挾,被小資和中產階級的趣味和欲求擺布,低俗文化歡蹦亂跳,公眾的審美趣味往下走,文藝缺少人文價值,缺少藝術的優美品質,缺少精神的勇毅與節操,缺少創造的生機與活力,批判更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除害劑、健康文化生活的凈化器,能激濁揚清,除惡掃害,植芳造林,傳送思想的陽光,有力抵制“低俗覆蓋高雅,庸俗惡俗成時風”的潮流。
早就有人提出必須確立信仰,因為信仰事關知識分子的精神出路和民族的精神狀況。一個沒有精神信仰而實用主義大行其道的民族,肯定會崇拜官本位、金本位和等級制,會粉飾現實,無視和回避現實的苦難和危機,陷入粗鄙的侏儒精神里。還有人批判犬儒主義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抹殺了善惡是非,導致頭腦發達、良心萎縮,最終只留下勢利世故。在許多領域都相當“繁榮”的中國社會,理想主義的潰敗和批判理性的瓦解卻很少有人關注,拜金主義在四下占領思想文化消費市場,卻完全無助于提高社會文化品質;物質財富的迅猛增長沒有帶來相應幸福感的增長,嚴重的兩極分化卻撕裂了很多人的心;價值失范、道德墮落帶來精神危機與迷信盲從。一位外國管理學大師在中國旅行時,發現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書店卻寥寥無幾,他由此擔憂一種“集體智商的衰退”。這種擔憂從盛世看到迷思,決非空穴來風。祝勇在《歷史寫作的四個關鍵詞》里批評:“中國人越來越輕視歷史、鼠目寸光,眼睛緊緊鎖定現實的利益,不見未來,更不見歷史,所有的冒失、愚蠢、迷茫,都是來自對歷史的無知。”[13]這種對現實和歷史方面的省思批判彌足珍貴。
文學作為社會的良心,必須對生活保持敏銳的警覺。需要抗拒一切歪風邪氣,拒絕與世俗同流,更不能向低俗或丑惡低頭。必須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堅定地維護人類基本的價值觀念,如自由、民主、博愛、理性等等,批判自私、貪婪、嫉妒、仇恨、暴力、殺戮,努力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倡導人性的提升,同時反思與批判歷史或當下現實社會中存在著的各種不合理現象,超越現實的束縛和個人私利,深切關懷國家、民族、乃至世界上一切公共事務,對未來進行嚴肅的思考,幫助人們領悟社會的本質和人生的真諦。
當然,文學的批判對社會現實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無法直接改變現狀改變社會。但它由于貼近我們的倫常日用,滲入我們的意象世界,而必然影響人們的認識和態度,能慢慢改變人們的立場、觀念和對社會的看法。因此,我們依然要用文學關心人類的命運,關心民族與國家的發展,用文學的力量揭示“全球化”的困境,為現代人的心靈開拓新的自由空間。要倡導有尊嚴有價值的寫作,為人文精神的下墜起到減速和剎車作用,為人類的自我救贖乃至自我凈化做一些積極有效的貢獻。當人們業已固化的審美經驗模式阻滯了對新藝術的接納時,批判能拓展人的審美經驗,改鑄我們的審美文化。一種文化如果想避免僵死和封閉,也必須不斷地對自身進行分析、批判和審視、檢省,吐故納新,去偽存真。
4、批判不僅是顛覆,也是建設。
需要特別要強調的是,批判發端于人內心最深刻、最真實的情感沖動,即不滿現狀,變革求新的意志。它擺脫一切壓制和強權的意志,保持青春創造的活潑與鋒芒,既是破壞又是建設,既是忤逆又是道德,能極大地拓展我們懷疑與未知的疆域,促進認知的深化與擴展。所以我主張強化批判性,不僅僅是一種揭露、譴責和抨擊,也不是簡單的打倒、刻意的顛覆,還有對理想和希望的一種折射與寄托。它基于人類或知識分子的正義和良知,能引起廣泛共鳴,而不光是個人的怨氣牢騷。
茅盾在讀魯迅著作時體會到:“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除‘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中的芝蘭。”[14]拔除蕭艾,培養芝蘭,去惡扶善,說透了批判者的所作所為、目的用心。批判金剛怒目劍拔弩張,似乎是專擅攻擊斗爭,其實它根本的立足點是為了變革為了建設。諸如魯迅之所以徹底批判丑陋的國民性,正是為了建設美好的國民性。巴金批判中國人愛說假話,正是為了倡導人人說真話。我們之所以提倡加強文學的批判性,并非熱衷于展丑揭短,乃是為了要除惡懲腐、掃丑蕩黑。批判不僅要揭露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各種丑陋,而且要吸收災難帶來的沉痛教訓,借鑒成功范例,更好地建設“美麗中國”。
文學作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礎和介質,既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見證,也是一時一地人心、民心最深刻具體的展現,同時還是不同時代、不同民族認識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形象反映。2015年獲世界科幻雨果獎的劉慈欣說:黑暗和災難是“極有價值的主題,這種描寫像一把利刃,可以扎到很深的地方,使人類對未來的災難有一種戒心和免疫力。”[15]這話說清了寫黑暗與災難并非為了渲染恐怖,而是為了提高抗拒能力、防范能力,從而減少黑暗和災難給人們帶來的威脅危害。只要是不甘做思想的懶漢庸人,便應當運用歷史之思、現實之刺去探尋破解困局和難題的方法,將現實建造得更好一些。
因為對現實不滿,所以要批判。因為心懷希望理想,所以要批判。作家李洱把“不倦的尋求看成是所謂的先鋒精神:不與現實茍合,才會有真正的現實感,這意味著你的理解和質疑同樣重要,論證和想象同樣重要,猶豫和果斷同樣重要。”韓東說:“文藝需要創新,因此有破壞和重建的層面,先鋒側重破壞,或者是以破壞的方式建立。先鋒因此是對立者,反叛者,革命者。”周昌義說:“文學在社會生態鏈中的一大任務是用人道主義理想質疑現實,對現實永不滿足。”[16]他們皆認為討好式寫作、無風險寫作、妥協式寫作會對真正寫作造成戕害和毒殺,因此提出要向庸俗化的寫作發起勇敢挑戰與反叛,通過對現存理論的質疑,去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
在當前這個唯利是圖的時代,文學批判拜物教、拜金潮,反潮流反風氣,抗拒生產沒有文學價值的文化消費品,應該是一個作家思想靈魂中最基本的素質,也是一個人優秀品質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忠實于自己的獨立思想,保持一個作家應有的良知和風范,堅持知識分子的批判權利,用一種積極的“建設心態”致力于批判黑暗污穢,抗擊無恥墮落,粉碎一切精神桎梏,對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缺失和陰暗給予勇敢的揭露,繼續殫精竭慮創造文學精品,堅定不移地做自己熱愛的事業。這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而非為一己私利,為了能早日建成一個真的、善的、美的國家而精勤努力。
周濤心目中的作家“是一個自然與歷史及人類心靈史、思想史的卓越游牧者,一個豪邁而意志堅定、頭腦清醒睿智的孤獨旅行家。在世紀末世紀初交會的地平線上,你正苦苦地找尋更多更豐富屬于你最輝煌的思想和情感,饋贈給饑餓的人們。”[17]這樣的作家其實就是一個最理想人性的追求者、一個具有探索性、批判性的思想家。
文學存在的價值是溫暖人心,永遠照亮生活世界,幫助我們心明眼亮,看清世事人生。優秀的文學作品除了向人們提供一種新的生活態度、新的美學風格、新的想象世界之外,還應發揮它的思想能力,促使讀者產生新的思想維度,質疑、批判或重新思考文明、制度、政治、文化等關乎社會現實和人生的諸種問題。包括對存在進行意義的探索,對當下社會做出更加積極的建設性反應和批判。王蒙在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時發表感言說:“真正的文學拒絕投合,真正的文學有自己的生命力與免疫力,真正的文學不怕時間的煎熬。不要受各種風向影響,不盯著任何的成功與利好,向著生活,向著靈魂,寫你自己的最真最深最好,中國文學應該比現在做到的更好。”[18]這極為清醒睿智的反應,提醒我們要從多方面去奮發努力,向歷史和現實汲取更多的力量,然后張弓搭箭,對世間存在的一切貪嗔癡、丑陋荒謬、奴性和虛偽現象給予致命一擊。
注釋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4年度西部項目(14XZW044)的階段性成果。)
[1]見馬·布雷德伯里編:《現代主義》第9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2]《燈下漫筆》,《墳》,《魯迅全集》第1卷第217 頁。
[3]弗吉尼亞·伍爾夫:《論現代小說》第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
[4]薩特:馬德萊娜·夏普薩爾,《作家其人》,第230頁。
[5]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6]劉醒龍:《泛經濟時代的天職》,見2011年9月16日《人民日報》。
[7]轉引自何清:《文體選擇與心靈自覺》,見《民族文學研究》2011年第6期。
[8]黃庭堅:《山谷集》卷二十七,《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
[9]莫言:《盯著人寫》,見2011年9月16日《人民日報》。
[10]巴金:《隨想錄》第3集《真話集》后記,第16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1]巴金:《說真話》。
[12]轉引自張同吾:《錚錚鐵骨鑄詩魂》,見《文藝報》2013年10月16日。
[13]祝勇:《散文的新與變》,見2013年9月30日《文藝報》。
[14]茅盾:《最理想的人性》,載《文藝陣地》1941年6卷5期。
[15]劉慈欣:《重建科幻文學的信心》,見2015年8月28日《文藝報》。
[16]轉引自姚霏:《先鋒文學:不與現實茍合》,見2014年12月14日《春城晚報》。
[17]周濤:《高榻》第284頁,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18]劉颋、劉秀娟等:《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感言》,見2015年8月17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