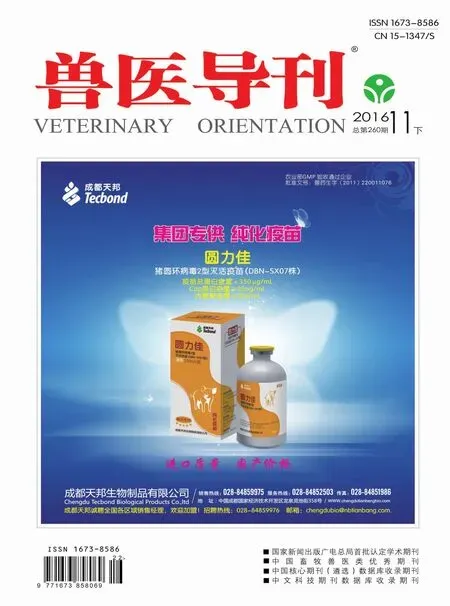談奶牛性控凍精技術
馬 瑩
(濟南畜牧技術推廣站,山東濟南 250031)
談奶牛性控凍精技術
馬 瑩
(濟南畜牧技術推廣站,山東濟南 250031)
提高對性控凍精技術實踐效果宣傳力度,通過重點區域、重點小區的示范使用,使廣大養殖戶意識到性控凍精的使用價值,從而慢慢接受并使用性控凍精;政府各部門制定優惠政策,加大對奶牛養殖的扶持力度,調動奶農的養殖積極性;加大對性控凍精技術的研究資金投入,著力降低性控凍精生產的成本。
奶牛;性控凍精;技術使用
目前奶牛的主要繁殖方式是人工授精技術,從成本、效果來看,應用性控精液(X精液)通過人工授精來獲得雌性犢牛是最佳途徑,也是我們要推廣的奶牛性別控制技術。
1 性控精液獲得方法
性控精液的獲得方法主要是流式細胞儀法,牛精液中X精子和Y精子的DNA含量差異大更加容易分離,目前X精子的分離準確度可達90%以上。流式細胞儀分離法其主要流程包括采集精液——精液品質檢測——合格者染色——流式細胞儀分離——性控精液冷凍——解凍。在精液分離冷凍處理過程中,精細胞可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干擾,如:采集到處理的間隔時間、高度稀釋、核染色、機械壓力(通過檢索儀時、激光照射、離心、冷凍等)。有研究表明,采集到處理的間隔時間越長,分離處理的效果越差,間隔時間一般不應超過24h,造成分離效果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在間隔時間內,環境因素會造成線粒體產生的活性氧(ROS)增加,較高的ROS水平將會使精子線粒體發生膨脹,誘導線粒體膜通透性發生改變,釋放細胞色素C及其他凋亡相關因子損傷精子,損傷的精子又進一步增加ROS的生成,最終導致精液品質下降。另外,在精液冷凍解——凍過程中會造成部分精子的損傷和死亡,從而,產生更多對精細胞有害的ROS,精細胞的氧化損傷程度與精子冷凍效果有密切關系。為此,研究者一直以來,致力于研究精液冷凍保存的方法,探索選擇合適的染色液、稀釋液、鞘液、收集液、保存液、抗氧劑種類以及合適的冷凍保存方式,來提高精液冷凍保存的效果。稀釋液的種類和配方對精液的冷凍效果非常重要,組成稀釋液的主要成分包含糖類、鹽類、蛋白類及一些抗凍保護劑。常用的糖類有葡萄糖、蔗糖、乳糖和果糖等,稀釋液的糖類物質不僅為精細胞提供能量,還具有一定的防凍作用,甘油是一種常用的抗凍保護劑,因為甘油濃度對精子活力和頂體完整率有一定影響,對精細胞有一定的毒害作用,因此在運用中應注意控制其濃度。有研究發現,卵黃配合抗凍劑甘油對精液的冷凍保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卵黃的適宜添加量在15~20%,再進行充分攪拌混勻。添加抗氧化劑主要是抑制精細胞內的自由基的生成,預防不飽和酸發生過氧化,從而對精細胞膜起到保護作用。添加的抗氧化劑種類主要有維生素和一些酶類,維生素C和維生素E在具有重要的抗氧化作用,稀釋液中添加維生素E能夠增強牛精子抗氧化酶活性,可以使精子冷凍—解凍后的質量得到提高,其添加的適宜劑量為1.5mg/ml。在冷凍稀釋液中添加維生素C對荷斯坦種公牛X精子的影響發現,隨著解凍時間的延長,維生素C能夠減緩精子的死亡,而解凍時間短則效果不明顯,其適宜添加量為4~6mg/ml,并且發現荷斯坦公牛X精子在解凍后,其精子活率、質膜完整率及頂體完整率都有顯著提高。對奶牛性控凍精生產工藝進行改進發現,改進后的精子活率、頂體完整率、母牛受胎率、犢牛性別控制準確率以及精液中抗氧化物酶活性都有顯著提高,在大幅度降低成本的同時加快了分離速度,并且提高了每支細管中的有效精子含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凍處理前可以對精子進行優選,將死精畸形精進行剔除,可以有效降低冷凍處理后的死精數,使得ROS產生減少,從而提高精液品質。
2 輸精技術
性控凍精有效精子數遠低于常規凍精,價格高于常規凍精,因此如何提高受胎率,節省成本就顯得非常關鍵了。在運用性控凍精輸精時,不僅要嚴格掌握好輸精時間,而且要有過硬的輸精技術,才能達到理想的受胎率。有很多資料表明:性控凍精輸精部位不同,受胎率也不同,而且存在明顯差異。子宮角深部輸精比子宮體輸精受胎率高出很多,效果也更好。但也對人工授精員提出了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在輸精時要求做到:慢插、輕拉、緩出,輸精完畢,套管口不應有血跡,具體如下:(1)輸精前用紙巾將陰戶擦干凈,嚴禁用消毒水清洗陰戶;(2)進槍時,以35°~40°角向上插入5~10cm,避開尿道口后,再改為略向前下方進入陰道;(3)從直腸把握子宮頸;(4)內外兩手協調操作;(5)不應以外面手強硬操作;(6)輕柔地使輸精槍通過子宮頸,滑向子宮體內至子宮體前沿,達卵泡側子宮角深部大彎處;(7)輸精槍到達輸精部位后緩慢注入精液;(8)輸精完畢,緩慢退出輸精槍,按摩子宮直至外陰有強烈收縮最佳;(9)如需促排可在輸精后肌注LRH-A325~50μg。
3 奶牛性控凍精應用的體會
對專業技術工作,態度一定嚴謹、認真負責,業務嫻熟。充分掌握實施對象的全面情況,如種精液的保管,種精液的解凍時間的問題,精子活力是否達到3.5以上,有效精子數應不少于1000萬個。還有輸精時間和次數的考慮,一般發情開始后或排卵前12h左右適宜輸精,發情期內輸精1~2次,相隔8~12h為佳。做好工作前牛只及操作人員,器具的衛生檢查和衛生消毒處理,備品的擺放,技術工作無小事,無死角,為工作人員及牛只創造優質的環境,防止應激情況的出現。臨床來看,母牛的受精效果是,子宮正常的與患病的牛只的情期受孕率比為62%和46%,差異非常明顯。力爭達到衛生檢查工作、并做好患牛治診斷,主要是確保母牛受孕成功。
[1] 趙永靜.提高種公牛精液品質的幾項措施[J].養殖技術顧問,2014,(10):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