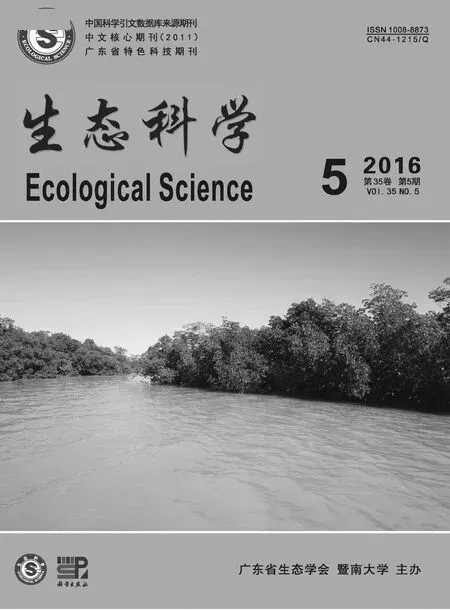廣東省2000—2012年生態足跡分析
付開, 馬姣嬌, 胡夢瑤, 徐頌軍
廣東省2000—2012年生態足跡分析
付開, 馬姣嬌, 胡夢瑤, 徐頌軍*
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 廣州 510631
運用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對廣東省2000—2012年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進行了分析, 并且用ARIMA模型對2013—2020年的生態足跡變化趨勢進行了預測。結果表明: 2000—2012年, 廣東省人均生態足跡呈現上升趨勢, 人均生態足跡由2000年的0.8158 ghm2·cap–1增加到2012年的1.1784 ghm2·cap–1; 人均生態承載力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 由2000年的0.3748 ghm2·cap–1下降到2012年的0.3122 ghm2·cap–1; 人均生態赤字由2000年的0.4410 ghm2·cap–1增加到2012年的0.8662 ghm2·cap–1; 萬元GDP生態足跡由2000年的0.6631 ghm2·mil–1下降到2012年的0.1783 ghm2·mil–1。2000—2012年人均生態足跡均大于人均生態承載力, 廣東省生態經濟系統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預測顯示2013—2020年的人均生態足跡由1.1850 ghm2·cap–1增加到1.2222 ghm2·cap–1, 人均生態赤字由0.8763 ghm2·cap–1增加到0.9368 ghm2·cap–1。針對廣東省的生態現狀, 從優化產業內部結構, 合理利用土地資源,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減少人均生態足跡消耗的政策和建議。
生態足跡; 生態赤字; 可持續發展; 廣東省
1 前言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1987年首次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來的,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 已經逐步從理論走向實踐[1]。如何定量評估區域生態系統是否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態成為當前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的前沿和熱點[2]。為了更加直觀、準確、明了的評價可持續發展狀況, 國內外學者提出了很多評價指標體系和計算方法, 其中應用最多的就是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其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人WILLIAN E.Rees提出[3],之后由他的博士生WACKERNAGEL對生態足跡的方法和理論加以完善, 因生態足跡具有易于理解、計算簡單、易與其他評價指標相結合等多個優點,生態足跡的方法引起了世界學者的廣泛關注, 并應用于國家、城市、產業等不同領域。國內外學者對生態足跡理論進行了廣泛的運用和實踐[4-5], 近年來,國外生態足跡研究方面日趨完善, 隨著技術和指標的更新, 研究領域也更加深入, 加強了大跨度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6-7]; 在國內, 生態足跡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邱壽豐等運用國家生態足跡賬戶分析了福建省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8], 謝高地等對中國的生態空間占用進行了相關研究[9], 李正泉運用傳統的生態足跡模型核算1995—2013年浙江省人均生態足跡, 分析膳食結構改變引起的生態足跡組分變化[10], 胡美娟在三維生態足跡模型的基礎上, 運用足跡廣度和足跡深度構建南京市三維生態足跡影響因子指標體系[11]。但是生態足跡模型在這些應用中仍然有一定的缺點, 例如數據選取的時間序列上連貫性和更新不夠, 數據處理方法不一致、模型參數計算或者取值不合理等問題。由于對廣東省近些年的生態足跡動態研究甚少, 基于此運用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定量分析廣東省2000年—2012年生態足跡動態變化趨勢, 并且對廣東省2013—2020年的生態足跡進行了預測, 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2 研究區概況
廣東省處于東經108°13′—119°59′, 北緯3°28′—25°31′, 面積大約為18萬平方千米, 地理位置優越,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隔海相望。廣東省是我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省份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 經濟總量連續多年位于我國前列, 廣東省經濟主要以外向型經濟為主, 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區, 珠江三角洲經濟發達, 區位優勢明顯; 2012年之前廣東省產業結構比重大小依次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主要以電子信息產品和紡織業為主; 2013根據廣東省之前已出臺的《關于加快現代產業體系的決定》之后, 作出重點發展第三產業的戰略部署, 主要包括金融、信息服務、商務會展、文化創意、現代旅游、健康服務等行業, 產業結構比重大小依次變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這是廣東省第三產業比重十年來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主要以金融業為主;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隨著廣東省人口的增多, 生活質量的提高, 人們對自然資源過度索取以及不合理利用使得廣東省生態環境壓力越來越大, 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導致資源和環境的不協調, 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制約了廣東省可持續發展。如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已成為重要的科學問題。文章采用生態足跡的理論方法分析探討生態經濟活動對廣東省的自然生態系統影響程度, 為實現廣東省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3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文運用生態足跡計算模型需要用到的數據來源于(2001—2013年)《廣東省統計年鑒》, 廣東省國土資源廳相關土地調查數據以及參考相關文獻[12],全球平均產量來源于FAO數據庫[13]。
3.2研究方法
3.2.1 生態足跡計算模型
任何已知人口的生態足跡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或者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總面積[14]。生態足跡計算主要基于兩個基本假設[15]: (1)人類能夠估計自身消費的大多數資源、能源及其所產生的廢棄物數量; (2)消耗的資源和產生的廢棄物可以通過換算轉換成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生物生產性土地分為耕地、林地、建設用地、牧草地、化石能源用地、水域六種土地類型。計算公式:

式中: EF為總生態足跡; ef為人均生態足跡; N為人口數, ci為i種商品的人均消費量; rj為均衡因子, pi為i種消費商品的平均生產能力; aai為人均i種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產面積, i為消費商品和投入的類型.為了使計算結果能夠轉化為一個可以比較的標準, 需要在每種類型生物生產面積前乘上一個均衡因子, 以轉化為統一的、可比較的生物生產面積[16], j為土地類型。
3.2.2 生態承載力的計算模型
生態承載力又叫生態容量, 是指一個地區所能提供給人類的生態生產性土地的面積總和[17]。根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的報告, 在計算生態承載力時要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面積[18]。本文采用聯合國糧農組織1993年計算生態足跡時的標準。耕地和建設用地的均衡因子為2.8, 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均衡因子為1.1, 草地和水域的均衡因子分別為0.5、0.2; 耕地和建設用用地的產量因子為1.66,林地、草地、化石能源用地、水域的產量因子分別為0.91、0.19、0、1。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 EC區域總生態承載力; ec為人均生態承載力; aj為人均實際擁有第j類土地的的生物生產面積; ri為均衡因子; yj為產量因子。
3.2.3 ef和ec的比較
當ec>ef時, 為生態盈余(er), 表明該地區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況.當ec<ef時, 表現為生態赤字(ed),即該地區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態。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ef為人均生態足跡; ec為人均生態承載力; ed(er)表示人均生態赤字或人均生態盈余。
3.2.4 萬元GDP 生態足跡

萬元GDP生態足跡反映資源利用效率, 它結合資源投入和產出來考慮生態效率[19], 萬元GDP生態足跡的值越大, 表明資源利用效率越高, 反之就越小。
3 廣東省生態足跡動態變化分析模型—ARIMA模型構建
ARIMA模型是一種把非平穩時間序列轉化為平穩時間序列, 然后將因變量對它的滯后值以及隨機誤差項進行回歸所建立的模型, p為自回歸項; q為移動平均項數, d為時間序列成為平穩時所做的差分次數, 在預測之前首先要確定p, q, d的值, 才能建立模型, 只要該模型確定, 就可用現時間序列的過去值和現值來預測未來的值[20], ARIMA模型建立的步驟主要包括序列平穩性檢驗、模型初步識別、模型參數估計、模型診斷分析四個方面。自回歸移動平均(ARIMA)模型B-J法中最為重要的基本模型之一, ARIMA模型的預測精度較高, 適用于非平穩時間序列的短期預測[21]。在實際問題中, 許多序列不近視為平穩序列, 不能直接用ARIMA模型, 但是有些序列經過處理后, 可以產生一個平穩的新序列,從而可用ARIMA(p, d, q).設{Yt}為非平穩時間序列, d階差分后的平穩序列為{Zt}, 則:……等依次差分成平穩時間序列Zt, 使Zt滿足:


Zt為平穩序列, 因此可建立模型ARIMA(p, d, q):
可得

式中, d為求和階數, 即差分階數: p和q分別為平穩序列的自回歸和移動平均階數。
4 結果與分析
4.1生態足跡動態變化分析
根據廣東省2001年到2013年廣東省統計年鑒和廣東省國土資源廳提供的數據, 由于數據量較大,僅給出2008年生物資源消費數據, 如表1, 利用公式(1)、(2), 匯總計算出廣東省2000年到2012年的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承載力如表2和表3, 本文在計算人均生態足跡時, 由于缺乏2002、2003和2011年的人均實際土地面積數據, 因此計算時用相鄰年份的數據的均值來代替; 利用公式(3), 計算出廣東省2000年到2012年的人均生態足跡盈虧如表4; 利用公式(4)得出萬元GDP 生態足跡如表5; 由表2、表3和表4得出廣東省2000年到2012年的人均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和生態赤字的變化趨勢如圖1, 由表5繪出的廣東省2000年到2012年的萬元GDP生態足跡如圖2。
由表1、表3和圖1可知, 廣東省2000—2012年人均生態足跡總體呈上升趨勢, 由2000年0.8158 ghm2·cap–1上升到2012年的1.1784 ghm2·cap–1,凈增0.3626 ghm2·cap–1, 增幅達到44.4%。人均生態承載力總體呈下降的趨勢, 下降幅度較小且比較平穩, 從2000年的0.3748 ghm2·cap–1到2012年的0.3122 ghm2·cap–1; 由表4的生態足跡盈虧情況和圖1可知, 2000—2012年廣東省一直處于生態赤字狀態, 并且人均生態赤字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由2000年的0.4410 ghm2·cap–1增長到2012年的0.8662 ghm2·cap–1, 生態供需極度不平衡, 可知2000年—2012年廣東省生態環境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況。改革開放以來,各行各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廣東省以外向型經濟為主, 外資的引入對廣東省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的作用, 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 在資金引入、先進技術應用等方面領先其他地方, 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的轉型, 人民生活的不斷提高, 使得省內外人士源源不斷流入珠三角地區, 城鎮化率不斷提高, 期間明顯快于我國為其他地區, 2000—2010年是廣東省城鎮化發展的加速期, 城鎮化率居全國前列, 2010—2012廣東省城鎮化增長速度有所減少, 但仍保持上升的勢頭。城鎮化伴隨工業化發展, 能源是工業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資源, 這些都能引起生態足跡發生變化。

表1 生物資源消費足跡Tab. 1 Calculations of Eco-footprint of biotic resources

表2 廣東省2000—2012年人均生態足跡匯總Tab. 2 Eco-footprint per capita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2 (ghm2·cap–1)

表4 廣東省2000—2012年人均生態赤字匯總Tab. 4 Eco-deficit per capita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2 (ghm2·cap–1)
4.2生態足跡構成分析
由表2可知在人均生態足跡構成中化石能源地所占比例最大, 約占整個人均生態足跡的50%左右,其次是草地、耕地, 最后是水域、林地和建設用地,在研究時段內, 建筑用地增幅最大, 達到16.6%, 這和近年來省內的城鎮化快速發展密切相關, 需要大量土地用來建設; 其次是化石能源地增幅達到9%;最后是草地增幅達到4.5%、水域2.3%、林地1.6%、耕地–4.9%, 由于建筑用地消費比重在整個人均生態足跡中很小, 所以化石能源地是影響人均生態足跡變化的最主要原因, 化石能源消費最大的原因是與歷年來城鎮化和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 城市化進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耕地的消費呈下降的趨勢, 說明隨著社會的發展, 人們對農產品的需要也在慢慢下降, 但是耕地仍然是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 草地的消費足跡增大是由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們對肉類產品的需求也在增加, 林地在整個人均生態足跡中所占比重最小, 增幅很小, 對整個生態足跡影響不大; 由于廣東省屬于沿海省份, 水產業比較發達, 人均水產品的消耗量也比較大。綜合可得, 耕地、化石能源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是影響人均生態足跡變化的主要原因, 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建設用地的擴張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都會引起人均生態足跡的變化。

表5 廣東省2000-2012年萬元GDP生態足跡匯總Tab. 5 Eco-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yuan GDP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2

圖1 廣東省2000—2012年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承載力和人均生態赤字動態變化Fig. 1 Eco-footprint, eco-capacity and eco-deficit per capita dynamic variation between 2000 and 2012 in Guangdong

圖2 廣東省2000—2012年萬元GDP 生態足跡變化Fig. 2 Change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yuan GDP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2
4.3萬元GDP生態足跡變化分析
根據表5和圖2可知, 廣東省在2000年—2012年時間段內的萬元GDP 生態足跡是逐年下降的,由2000年的0.5717 hm2·mil–1下降到2012年的0.1783 hm2·mil–1, 年降幅為18.4%, 萬元GDP生態足跡逐年下降反映了廣東省資源利用率不斷提高,主要原因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 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廣東省失去了其主導地位, 由初期的第二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慢慢轉為由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 在此過程中積極響應政府號召, 發展循環經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和升級, 對貫徹廣東省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5 ARIMA模型建立與生態足跡預測
(1) 序列平穩性檢驗
本文把廣東省2000—2012年的人均生態足跡作為原序列, 由上文可知序列是一個非平穩時間序列, 為使數據變得平穩, 需要對原數列進行差分運算。對原序列做一階差分, 從一階差分后單位根檢驗可知(表6): ADF的值還大于1%水平下的臨界值,所以序列仍然存在不平穩性.對原數列進行二次差分, 二階差分ADF檢驗結果可知(表7): ADF的值小于1%水平的臨界值, 由此可知該序列是平穩的。
(2) 模型識別
由(1)可知, 原序列進行二次差分后趨于平穩,即d=2, 然后通過做出二次差分后序列的ACF和PACF圖來確定ARIMA(p, d, q)模型的階數p和q,

表6 一階差分序列單位根檢驗結果Tab. 6 Result of the first-order difference sequence unit root testNull Hypothesis: D(Y) has a unit rootExogenous: Constant, Linear TrendLag Length: 2 (Automatic-based on SIC, maxlag=2)

表7 二階差分序列單位根檢驗結果Tab. 7 Result of the second-order difference Sequence unit root testNull Hypothesis: D(Z, 2) has a unit rootExogenous: Constant, Linear TrendLag Length: 1 (Automatic-based on SIC, maxlag=1)
從圖3可以看出序列的自相關系數和偏自相關系數都是拖尾的, 初步識別, 建立模型ARIMA(p, 2, q).通過自相關-偏相關分析圖可知, 顯著不為零的偏相關系數的個數為3, 顯著不為零的自相關系數的個數為2, 推測p的值可能為1, 2, 3, q的值可能為1, 2, 所以可建立的模型有ARIMA(1, 2, 1), ARIMA (1, 2, 2), ARIMA(2, 2, 1), ARIMA(2, 2, 2), ARIMA (3, 2, 1), ARIMA(3, 2, 2)幾種。
(3) 模型參數估計
通過AIC即最佳準則函數定階法來確定p和q,一般來說AIC值越小, p和q值越適合。通過計算得到模型參數估計的AIC和SC值, 選擇ARIMA(3, 2, 2)模型。

圖3 二階差分的PAC和AC圖Fig. 3 The PAC and AC graph of second order difference
建立ARIMA(3, 2, 2)模型:
(1-0.0981B-0.2103B2-0.3009B3)(1-B)3Yt=(1+0.03 87B1+0.9613B2)et
S.E=0.0073, AIC=-6.7132, SC=-6.5317
Adjusted R-squared=0.9932, DW=2.498
(4) 模型分析
根據上面確定的ARIMA(3, 2, 2)模型, 對原數據進行回歸擬合, 模型中的殘差序列(Residual)以及原數據的實際值(Actual)和擬合值(Fitted)的序列圖見圖4, 從圖可以看出, 模型的實際值和擬合值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并且模型的殘差值比較小, 所以該模型還是比較理想的。
(5) 生態足跡預測
根據ARIMA(3, 2, 3)模型預測廣東省2013年到2020年的人均生態足跡, 同理運用ARIMA(2, 1, 3)模型預測2013—2020年的人均生態承載力, 可預測得出人均生態赤字, 匯總如表8所示:
6 結論與討論
根據生態足跡模型對廣東省2000—2012年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進行了計算, 并且運用ARIMA模型對廣東省2013—2020年生態足跡進行了預測, 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通過計算, 廣東省人均生態足跡由2000年的0.8158 ghm2·cap–1到2012年1.1784 ghm2·cap–1, 人均EC由2000年的0.3748 ghm2·cap–1到2012年的0.3122 ghm2·cap–1, 研究期內人均生態足跡呈整體上升的趨勢, 人均生態承載力呈下降的趨勢, 人均生態足跡一直大于人均生態承載力, 環境處于生態赤字狀態, 并且人均生態赤字逐年增大, 由此表明廣東省近年來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況。

圖4 序列擬合效果Fig. 4 Fitting effect graph of second order difference sequence

表8 預測結果Tab. 8 Result of prediction (ghm2·cap–1)
(2) 耕地、草地、水域和化石能源用地都出現一定的生態赤字, 其中耕地生態赤字呈減小的趨勢,水域、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生態赤字逐漸增大, 可知水域、草地和化石能源地對廣東省生態可持續影響最大。
(3) 廣東省萬元GDP 生態足跡逐年下降, 由2000年的0.6631 hm2·mil–1下降到2012年的0.1783 hm2·mil–1,但在研究期內由2000年的0.6631 hm2·萬元–1下降到2001年的0.5832 hm2·mil–1, 再上升到2002年的0.5981 hm2·mil–1, 最后一直下降到2012年的0.1783 hm2·mil–1, 整個時間段內表明: 在廣東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 經濟增長方式發生轉變。
(4) ARIMA模型的預測結果表明: 在未來的時間段內, 隨著經濟的發展, 人均生態足跡持續上升,人均生態赤字還會進一步增大, 廣東省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將會繼續面臨更大的挑戰。
由于數據資源有限, 本文沒有分析影響廣東省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子,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對廣東省各個市生態足跡所占比重以及影響各個市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子進行深入研究, 根據影響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機制有針對性的制定合理的發展對策。根據本文對廣東省的現有研究提出加強耕地保護、優化產業結構、降低碳排放的增長速度、提高資源利用率等建議來緩解廣東省生態壓力。
[1] 陶在樸(奧地利). 生態包袱與生態足跡—可持續發展和重量及面積觀念[M]. 北京: 經濟科技出版社, 2003.
[2] 楊震, 牛叔文, 常慧麗, 等. 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的區域生態經濟發展持續性評估[J]. 經濟地理, 2005, 25(4): 542–546.
[3] REES W 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 leaves ou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 4(2): 121–130.
[4] 徐中民, 程國棟, 張志強. 生態足跡方法的理論解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6, 16(6): 69–78.
[5] VAN VUUREN D P, BOUWMAN L F. Exploring past and futur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for world region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5, 52(1): 43–62.
[6] YONG Geng, LI Ming, XU Dong, et al. Urba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Shen yang in China and Kawasaki in Japa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4, 75: 130–142.
[7] NICCOLUCCI V, GALLI A, REED A, et al. Towards 3D National Ecological footprint Geography[J]. Ecological Modeling, 2011, 222: 2939–2944.
[8] 邱壽豐, 朱遠. 基于國家生態足跡賬戶計算方法的福建省生態足跡研究[J]. 生態學報, 2012, 32(22): 7124–7134.
[9] 謝高地, 魯春霞, 成升魁, 等. 中國的生態空間占用研究[J].資源科學, 2001, 23(6): 20–23.
[10] 李正泉, 馬浩, 肖晶晶, 等. 浙江省1995—2013年生態足跡動態變化探析[J]. 生態科學, 2015, 34(6): 170–176.
[11] 胡美娟, 周年興, 李在軍, 等. 南京市三維生態足跡測算及驅動因子[J].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 2015, 01: 91–95. [12] 郭秀銳, 楊居榮, 毛顯強. 城市生態足跡計算與分析——以廣州市為例[J]. 地理研究, 2003, 22(5): 654–662.
[13]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FAOSTAT Domains [EB/OL]. [2016-04-05]. http://www.fao.org/statistics/en/.
[14] 楊開忠, 楊詠, 陳潔. 生態足跡分析理論與方法[J]. 地球科學進展, 2000, 15(6): 630–636.
[15] 徐中民, 陳東景. 中國1999年的生態足跡計算與發展能力分析[J]. 應用生態學報, 2003, 14(2): 280–285.
[16] 張樂勤, 陳素平, 榮慧芳, 等. 安徽省池州市2001—2010年可持續發展動態測度與分析[J]. 地理研究, 2012, 31(3): 439–448.
[17] HABERL H. How to calculate and interpret Ecological Footprint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the case of Australia in 1926-1995[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8: 25–45.
[18] 劉先, 謝屹, 常菁菁, 等. 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的江蘇省可持續發展狀況分析[J]. 林業經濟問題, 2012, 32(1): 90–94.
[19] 王樹強, 張貴. 基于秩和比的京津冀綜合承載力比較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4, 33(4): 19–24.
[20] 張勃, 劉秀麗. 基于ARIMA模型的生態足跡動態模擬和預測—以甘肅省為例[J]. 生態學報, 2011, 31(20): 6251–6260.
[21] 譚秀娟, 鄭欽玉. 我國水資源生態足跡分析與預測[J].生態學報, 2009, 29(7): 3559–3568.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
FU Kai, MA Jiaojiao, HU Mengyao, XU Songjun*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s,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2000-2012, and predicted the change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by using ARIMA model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presented a rising trend from 2000 to 2012.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of the city increased from 0.8158 hm2in 2000 to 1.1784 hm2in 2012. 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had a decrease trend; 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decreased from 0.3748 hm2in 2000 to 0.1783 hm2in 2012. The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increased from 0.4410 hm2in 2000 to 0.8662 hm2in 2012.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yuan GDP decreased from 0.6631 hm2in 2000 to 0.1783 hm2in 2012.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was always bigger than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from 2000 to 2012, which meant that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f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unsustainabl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reased from 1.1850 hm2in 2013 to 1.2222 hm2in 2020; the ecological deficit increased from 0.8763 hm2in 2003 to 0.9368 hm2in 2020. Considering the unstable eco-situation in Guangdong, we propose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duc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footprint; eco-capa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angdong Province
10.14108/j.cnki.1008-8873.2016.05.009
F062.2
A
1008-8873(2016)05-056-09
付開, 馬姣嬌, 胡夢瑤, 等. 廣東省2000—2012年生態足跡分析[J]. 生態科學, 2016, 35(5): 56-64.
FU Kai, MA Jiaojiao, HU Mengyao, et al.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J]. Ecological Science, 2016, 35(5): 56-64.
2015-12-29;
2016-01-1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NO.41271060)
付開(1990—), 男, 河南開封市人, 碩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生態與生態旅游, E-mail: 1625767027@qq.com
*通信作者: 徐頌軍(1962—), 男, 廣東人, 博士, 教授, 主要從事植物地理學、環境生態學和旅游生態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E-mail: xusj@s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