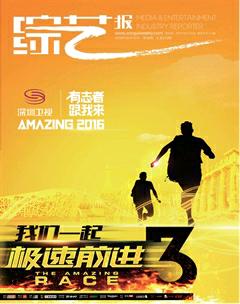“網紅經濟”:從夜總會到德云社
包冉
網紅自古有,今年特別熱。
大出風頭的papi醬、各類直播平臺上20萬余男女主播,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在分眾、垂直、細分領域,眾多粉絲體量不大、黏性和盈利能力一流的“專業網紅”,呈現出更持久的生命活力。更別提在資本和資本市場追捧下,正前赴后繼踴躍投身于網紅事業的無數老中青。
與以往一樣,出于投資者和被投資者的強烈名利動機,關于“網紅經濟學”的炒作又開始了。典型打法老一套,無非有三:
其一,整出一些新名詞,鼓吹一場新顛覆,不惜把小姑娘比喻成“當代魯迅”,也不顧“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放眼全球互聯網發展,只有“長尾理論”“免費的經濟學”和“共享經濟”可以視為互聯網對經典經濟學與社會學理論的原發創新。其他,影響力大如“社交網絡”者,其理論基礎早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便由人類和社會學家提出并驗證,互聯網對社交網絡當然很重要,但解決的是應用層面的問題,即為其提供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運營試驗場。一個客觀現實是,迄今為止的三大原發性網絡經濟理論創新,其商業實踐和理論提出均源自美國。以中國互聯網大而不強的發展現狀,動輒標榜理論顛覆創新,不是勇敢者的自信,而是無知者的無畏。
其二,轟轟烈烈搞運動,新瓶里面裝舊酒。網紅是什么?“網”,說的是媒介,其核心是互聯網帶來的自媒介形態;“紅”,說的是目標,是大眾關注度和輿情話語權。
傳統意義上的“造星”,有一套成熟的自上而下的拔擢、培養和推廣機制;嚴格意義上的“網紅”,則是自下而上、不依賴組織、網民自發追捧的成名路徑——二者殊途同歸,但法則截然不同。所以,當文娛類上市公司捧出大手筆的“網紅計劃”,其實質還是工業流水線上的造星機制,絕非真正意義上的網紅生態。
其三,網紅的商業模式很傳統,要么是夜總會,要么是德云社。“粉絲打賞”“虛擬禮物”“廣告競標”“社群激勵”“電商變現”……看上去很“互聯網思維”的立體商業模式,究其實質,要么是消費服務,要么是消費產品。
消費服務的典型模式是夜總會,其標準動作叫“捧”,消費動機是欲望宣泄,最大樂趣在撒錢速度、力度和廣度的比拼。桌面互聯網時代的成功者如YY、9158和六間房,其主力業務的實質就是“在線夜總會”——“名伶獻藝、公子撒錢、屌絲喝彩”,也順便捧出了一批“網紅”。
消費產品的典型模式是劇場和影院,其標準動作叫“購票”,消費動機是短暫的夢境和對現實的遺忘,最大樂趣在角色代入的快樂或悲傷、人以類聚的共鳴或共訴;老話兒說,“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進者,如邏輯思維,其實質和德云社無二——你負責掏錢買票“愛的供養”,我負責讓你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做“快快樂樂的衣食父母”。
夜總會和德云社,走到一定規模,必然會帶來品牌溢價。前者的老板可以憑此溢價大開分店,消費價格一定會高出市場均價;后者的老板可以做平臺,想捧誰就捧誰,想讓誰紅就讓誰紅,就像郭德綱之于小岳岳,羅振宇之于Papi醬。二者的老板都可以做自有品牌附加值的衍生產品,就像夜總會的酒、德云社的班、邏輯思維的書。
商業本質的雷同,并不否定后來者的天資、勤奮和成功。但非要包裝成“偉大的創新”,那可就有點矯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