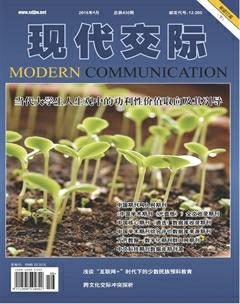關于MTI術語翻譯標準的討論
王楠 楊璐
[摘要]在信息化浪潮下,為適應我國對應用型高層次人才的需求,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翻譯專業碩士應運而生。不同于以往的學術型碩士,專業碩士的培養更符合各個職業的需求,滿足市場多元化的需要。而培養翻譯專業人才時,專業術語的翻譯是檢驗翻譯從業人員專業性的試金石。本文從忠實性、可讀性、統一性三個方面對MTI術語的翻譯標準進行討論,以期對術語翻譯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MTI 術語翻譯 翻譯標準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8-0071-02
術語是專業領域用于表達或定義科學概念的語言單位,是一種通過語音或文字來表達或限定概念的約定性符號。(馮志偉,2011)術語翻譯就是用譯入語再現原語術語所承載的信息,實現科技及社會科學的跨文化交流。目前,國內對于術語翻譯的研究尚處于空白。而隨著翻譯專業碩士(MTI)這一新興專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英語專業人才及學者開始關注翻譯實踐與研究。術語翻譯能力體現的是譯者譯文的專業性與科學性。因此,無論是作為翻譯碩士入學階段考試測試的題目,還是日后教學的課程項目,術語翻譯都對翻譯行業從業人員具有重要意義,對術語翻譯設定相應翻譯標準也就成為了規范術語翻譯的重要途徑。本文將從忠實性、可讀性及統一性三方面對MTI當中常出現的術語翻譯進行討論。
一、忠實性
忠實性即是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標準(text-centered criteria),是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費道羅夫、卡特福德以及巴爾胡達羅夫都曾提出的“等值”概念,其中的文本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與形式對應(formal correspondence)都肯定了忠實性作為翻譯標準的基礎。下面筆者就從文本內容與語言形式兩個方面來討論忠實性原則。
(一)文本等值
“文本等值”的含義是指譯文的文本內容應與原文的文本內容相一致。如:改革開放政策可譯為“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但是很多學生看見這樣的句子“China has carried out the Opening-up Policy for over three decades”,卻誤認為“the Opening-up Policy”就是“改革開放政策”,忽略了術語名稱的確切涵義,故將句子誤譯為“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已有30年的時間”,而正確的譯文應為“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已有30年的時間”。
一般情況下,重要術語的譯名必須準確概括其全部意義,如果意譯做不到,寧可取音譯來滿足兩種語言文本內容的一致性。(陳福康,2000)如:“NASDAQ”譯為“納斯達克”,“Utopia”嚴復將之譯為“烏托邦”,既有諧音的意味,又有“烏有寄托之鄉”的含義,在文本層面就形成了等值效應。此外,有時為便于文化交際,一些術語或縮略語可以不譯或采取零譯法。像“WTO”“NATO”“OPEC”“Internet”“ISO”“ISIS”等等這些國際常用術語可以不譯,這樣也能夠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文本內容。
(二)形式對應
除內容應與原文一致外,譯文的語言形式與風格也要盡量同原文的語言形式一致。如:“兩彈一星”可以翻譯成“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一國兩制”則可翻譯為“One country, two systems”,其中“一”和“二”兩個數詞的概念形式必須翻譯出來。此外,“以人為本”可以翻譯為“put people first”或者譯為“people-oriented”,也大大地保留了原文的語言風格。通過上述例子不難看出,譯文不僅應該忠實于原文的內容,而且還要符合譯入語的語言規范。
因此,所謂的“忠實”其實也同嚴復的“信達雅”當中的“信”含義一致,譯文必須忠實地表達出原作的思想內容。任何一種文體形式的翻譯,都離不開忠實性原則。尤其對于專業性較強的術語來說,如果做不到忠實于原有譯名,原語言文本所要表達的含義就無法正確、完整地再現出來。
二、可讀性
可讀性就是指譯文或譯名可以被譯入語讀者理解,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的最低層次對等就指出譯文讀者能夠和原文讀者一樣能夠理解體會到原文的思想內容。這是以讀者為中心(reader-centered)的角度提出的標準。再好的譯文如果缺乏可讀性,難以得到譯入語者的理解,就喪失了翻譯傳達信息、實現交流的意義與功能。例如,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Democracy”譯為“德莫克拉西”簡稱“德先生”,“Science”譯為“賽因斯”稱為“賽先生”,筆者認為將“Democracy”與“Science”生硬采取音譯法,很難讓讀者理解成民主與科學的含義,可讀性因而大大降低。
再比如:三個代表不能譯“three representatives”,這樣簡單粗暴的譯法會讓目的語讀者難以理解其含義。應該將“三個代表”的含義具體解釋出來,即: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三個代表”可譯為“three represents theory (The Party should always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na's advanced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lways represent the onward direction of China 's advanced culture, and always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由此可以看出,忽視譯名的可讀性可能產生歐化漢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洋涇浜”與中式英語兩個方向的后果,其根本原因都是受到了原語言模式的影響。從語言形式到語言內容,譯者常常會采取所謂的“直譯”來進行生搬硬套,卻使得譯文完全喪失了可讀性,喪失了傳遞信息的意義。
三、統一性
尤金·奈達曾指出:“讀者對譯文的反應應該與原文讀者對原著的反應相一致。”(Nida,2004)也就是說,翻譯不僅要強調語言的表達形式,更要強調讀者對譯文的反應,并且要把這種反應與原作讀者的反應對比來看。如果專業術語的譯名不統一,英漢兩種語言的讀者對兩種語言的文本所作出的反應就無法“統一”起來,政治經貿交流活動的信息傳遞也必然會出現偏差。因此,翻譯碩士學習階段的術語翻譯必須有譯名的統一性認識。
(一)政治術語譯名的統一
對于多數政治類術語的英譯情況來說,盡量要與國務院新聞辦、中央編譯局及外交部翻譯司發布核準的譯名統一。不少高校MTI入學考試會考察中央文獻政治術語的翻譯,這要求考生不是簡單采取哪些翻譯方法,按照自己的理解胡亂翻譯就可以。中央編譯局會定期公布中央文獻政治術語的規范譯文,使得中國政治外宣類文獻具備統一的參照標準。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小康社會“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合作共贏“win-win cooperation”等,這些譯名都具備一定的國際通用性,所以在進行政治術語翻譯的時候一定要嚴格符合國際通用的形式,避免胡編亂造,同時還要精準地傳達出我國的政治主張及立場。
(二)商貿專業術語譯名的統一
商貿專業術語譯名的統一,是指譯者把漢語的商貿術語翻譯成英語時,必須使用國際通用的商貿英語術語,按照英語的習慣表達信息,英譯漢也是如此。(劉法公,2012)但是我們發現,不同的譯者或不同的工具書對此類專業術語的翻譯比較隨意,完全忽視“譯名”統一的原則。比如:土地使用權,有“land-use right”“land-use rights”,還有“land use right”多個譯名,具體應該使用哪個譯名就考驗到譯者的英語水平,但是無論使用那種譯名,都要盡量做到譯名在整篇文本的同一性,即在整個文本當中凡是出現該術語的地方都要用相同的譯名,而不應出現前后不一致的譯名。
此外,許多漢語詞匯多是經歷了幾個版本才最終確立下來的,如:外向型經濟,從“foreign-oriented economy”到“outward-looking economy”,再到“export-oriented economy”,經歷了多個版本的改變。由此可以看出,商貿專業術語譯名的統一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但譯者在進行商貿術語的翻譯時應盡量做到譯名的統一。
(三)組織機構地名譯名的統一
組織機構名稱的譯名大多數已經固定,這就要求譯者應以統一固定的譯名來傳遞信息。這里所說的統一固定的譯名就是指流傳已久的,行業內公認的譯名,而不是譯者只憑自己的理解進行臆造所翻譯出來的譯名。比如:“WHO”指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英文縮寫,而不是“誰”的含義;“ASEAN”的含義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另外,有些地名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已有了固定譯法,并得到廣泛使用。即使這些譯名不符合規范,不夠妥帖,甚獲明顯錯誤,但因多年來已為人們所公認和熟悉,早已成為人們的共同語言,它們也應當繼續沿用下去,而不宜再行“發明、創造”。如“San Francisco”舊金山(按英語發音應譯為“圣弗朗西斯科”或者“三藩市”);又如“Seoul”經歷了直譯譯名與音譯譯名的轉變,曾經習慣譯為“漢城”,而現在卻經常翻譯為“首爾”。如果只按照譯者的主觀臆斷為術語定譯名,而不使用約定俗成的譯名,則容易引起讀者的困惑與混淆,且不利于譯名的穩定和統一。
四、結語
作為MTI入學考試及研究生教育階段必須具備的技能,術語翻譯能力決定了譯者對具有專業性較強的文本的翻譯掌控能力,也決定了譯者的譯文水平與質量。如何建立科學有效的術語翻譯標準,規范術語翻譯,形成標準化或多元化翻譯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大體就忠實性、可讀性與統一性幾個方面進行了翻譯標準的討論,但歸根結底術語翻譯的標準還是要建立在大量術語譯名的積累上,所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沒有量的積累,也無法憑空翻譯出恰當得體的術語譯名出來。
【參考文獻】
[1]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修訂本)[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2]馮志偉.現代術語學引論(增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姜望琪.論術語翻譯的標準[J].上海翻譯,2005(01):80.
[4]Nida,E.A.& C.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Discussion on MTI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Criteria
WANG NAN YANG LU
(13003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o meet the demand of China on higher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he major of 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emerge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academic master, application-oriented master suits better on profession demand and satisfies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the market. Therefor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has become a litmus test on testing translators professional ability when training master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o this thesis is centering on discussing MTI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criteria based on three aspects: loyalty, readability and unity, hoping to offer inspirations on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Key Words:MTI;terminology translation;translation criteria
責任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