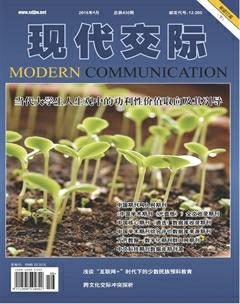評《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
韓前偉
[摘要]法國年鑒學派在20世紀后半葉的史學實踐中有著重要影響。作者彼得·伯克在《法國史學革命》一書中自如運筆,簡明扼要地將年鑒派的一輪花甲歷程分析得絲絲入扣。此書優長,在乎言簡意賅,然限于篇幅,于學派所當論者,亦多缺遺。故是書所無者,如學術政治、興起背景、可能之寫作手法等,皆應為讀者知。
[關鍵詞]年鑒派 《法國史學革命》 內在理路 學術政治
[中圖分類號]K5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8-0107-02
一、“入局”與“旁觀”,作者的冷靜敘述
記得劉少奇有句論“批評”的名言——優點講夠,缺點講透。所論確當,不過,若不能“深味”批評對象,恐怕難以做到“講夠”“講透”。作者彼得·伯克自言:“我有時將自己說成年鑒派的‘同路人,也就是說,一個(像許多其他外國歷史學家一樣)受這一運動啟發的局外人。近三十年來,我相當緊密地追隨著它的命運。”①(文內若無特殊說明,所引內容皆出自《法國史學革命》)彼得·伯克雖將其界定為“局外人”,但又說“我相當緊密地追隨著它的命運”。而且作者亦曾訪問年鑒學派的重要人物,并與之保持聯系。所以稱其為“入局”亦未嘗不可。彼得·伯克接著說:“盡管如此,劍橋與巴黎之間的距離,還是遠到了足以(由我來)撰寫一本評價年鑒派成就的史書。”此外,他在本書“鳴謝”部分寫道:“跟我一樣,他們力求在與年鑒派打交道的同時,與它保持一定距離。”由此看作者寫此書也可稱之為“旁觀”。因恐著史為現實裹脅,且“塵埃落定”,歷史方可“水落石出”,故向有所謂“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說法。不過,因是歷史進程的參與者,所以比之后輩,歷史的親歷者往往更易對往昔之其人、其事,抱有“了解之同情”,這也是“入局”撰史的優長。憑藉“入局”,作者自如運筆,簡明扼要地將年鑒派的一輪花甲歷程,分析得絲絲入扣。復因“旁觀”,作者亦能保持客觀的態度,正如書中所說:“人們可以說,布洛赫對英國史的興趣及其對克制性陳述的酷愛,讓他多少被視為榮譽英國人。”作者在書中總是小心翼翼地拋出某個前提,以使其敘述免于偏執、武斷。如作者用一句“盡管費弗爾和布羅代爾兩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學術政客,但是接下來的部分基本上不會談到運動的這一側面——比方說,索邦與高等研究院之間的競爭,或是為控制職位和課程的爭權奪利的斗爭”,便巧妙地限定了寫作內容。考慮到另一本由弗朗索瓦·多斯撰寫的研究年鑒派的重要作品——《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②中對學術政治的大量描寫。我們似可認為彼得·伯克的“這一巧妙限定”甚至影響了全書風格——顯然這比多斯的作品要多些“書卷氣”。“旁觀”的彼得·伯克,在文中,特別是在第五章“全球視野下的年鑒派”中,亦道出了學派的不足與局限。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反映法國特性的不足與局限,也是全球視野下學派“獨特價值”之所在。畢竟年鑒派以法語思考、用法語寫作,它應對的是法國歷史文化。是故,它的課題、方法與史觀皆是對法國的史學展現。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植根于法國命運的年鑒派,其優劣是非皆需以法國實際為第一標準。年鑒派的勝利正在于它契合了法國的歷史邏輯,它不必也不能去順應其他國家的歷史邏輯。作為承受方,我們應以“接受啟發”而非“照抄照搬”的態度,去觀察年鑒派的海外影響。所以年鑒派首先是“法國史學革命”,這場運動實質上是在法國情境、邏輯下對法國舊史學的反動,運動的一切皆規定于法國性。
在所有介紹年鑒學派的著作中,《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恐怕是最精練的一本。作者說:“本書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評價年鑒派的成就。”還說:“本書只能勉強算是思想史研究。它并不奢望成為研究年鑒運動的權威學術論著,我希望21世紀會有人來做這份工作。”顯然,身為“新文化史”的旗手,彼得·伯克在此無意自謙,只是作為其非代表作,作者確也不愿窮竭心血。不過,誠如馮友蘭所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惟其如是,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詳也。”③所以此書“至今仍是國際史學界介紹、評價年鑒派學術成就的最佳入門書”。
二、過分的“內在理路”依賴,使全書缺乏時代與社會感
全書雖以短精制勝,但有限的篇幅,也制約了相關內容的擴展。客觀地說,在作者英式克制敘述中,年鑒派的不少內容只好無奈缺席。加之作者欲主以敘事,故于概括著墨無幾,且不喜分析,言及學派起承轉合處,一味從“學術”里尋,給人就事論事之感,殊不知,實踐是認識的源泉,通篇讀來,只見一“脫離”社會與時代的年鑒派。論起寫作思路,本書倒極合余英時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理路”說。余英時認為思想史本身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我們可從思想自身的變遷中尋出其前后階段演化的內在線索。④這或多或少使人想起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和內外因原理。不過,余英時自言“內在理路”“是要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也有它的自主性”。⑤但他也補充道:“我在本書中雖然采取了‘內在理路的觀點,但是我并未將它與‘外緣影響對立起來。”“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緣解釋,而且也可以與一切有效的外緣解釋互相支援、互相配合。”⑥據此看,學術創新不一定意味著對舊有認識和范式的全盤否定。事實上,就創新與“舊有”的關系來看,創新可分為積極的創新、消極的創新兩類,應鼓勵積極的創新,即那些融通“舊有”而非建立在“傳統廢墟”之上的創新。有理由相信,彼得·伯克有能力將本書內容組織的更為豐富。不過,因篇幅所限和其他一些未言明的所在,作者拒絕了這一可能的誘惑。作者將其首章題定為“歷史編撰學舊體制及其批評者”,正體現了本書寫作的“內在理路”取向。不錯,索邦舊史學的“束縛”和社會科學提供的路徑,確實構成了年鑒運動興起的學術要因。不過,從“長鏡頭”和“大景深”的角度看,本書確實忽略了分析年鑒派與時代和社會大勢間的關系。
一戰摧毀了近代以來西方人樂觀的進步主義觀念和對人類理性及光輝人性的堅信,使歐洲人產生了幻滅感。于是,歷史學家們開始注意研究戰爭的根源,并逐步將關注范圍擴大至政府政策或外交協商過程之外的各種力量。如此,史學的研究范圍在一戰后逐步開始擴大。接著,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給整個西方社會造成了一種嚴重的恐慌和懷疑心理。這進一步推動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們去反思舊有的研究范式和理論。這時,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學科細化、專業化、制度化后,開始重新出現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研究的意識。時人聲稱:“經濟歷史,我們時代的統一的人文科學,產生于1929年和1930年初,即世界范圍痛苦的危機之中。”⑦
應該講,這些社會與思潮的變遷,作為所謂的“外緣因素”,都刺激著史學家對史學傳統、研究對象和相應的研究方法進行反思,而且也推動了年鑒派所借重的各類社會科學的發展。但在書中,這些聯系都被省略了,作者筆下是一“年鑒派之年鑒派”,而非“歷史、法國之年鑒派”,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三、拒絕民族志誘惑,即是忽略學術政治?
如前記,作者在文中聲明:“我也多少帶著遺憾,抵制了撰寫布勒瓦·拉斯派爾街54號居民——他們的祖先、聯姻、派別、庇護與被庇護的網絡、生活方式、心態等等的民族志研究的誘惑。”不錯,民族志的誘惑被擯斥了。不過,我有時想,作者既能“入局”,若節制地增加些傳記色彩,并對年鑒派集體心態進行適可而止的探討,或許更為有趣。謹慎的心態史研究和有分寸的傳記描寫,實際上可解構任何被神化的存在。或年鑒派果真可當得起一句“20世紀最富創見、最難以忘懷、最有意義的歷史論著中,有相當數量是在法國完成的”。但歷史是由人創造和書寫的,史學史也是作為人的史學家的學術實踐。所以,深入史學家的精神世界,特別是將其學術活動還原為其現實生活和生命體驗的一部分。這時,我們發現,由時空距離造成的形象放大,將不復存在。所以心態研究、傳記寫作在一定情況下,應當“祛魅”。以年鑒派為例,在其“一整個書架的出色著作”背后,是學術政治的大行其道。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年鑒派史家絕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們關切政治,以權力為其研究開路。作者盡管預先聲明,本書不關心學術政治,但彼得·伯克還是用“費弗爾控制權力”“布羅代爾控制權力”兩個短條目,對其學術政治做了簡要交代。作為關心年鑒派的讀者,我們有必要知道得更多。在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一書中。我們可發現以年鑒派為例的“學術生產”。年鑒派重視奪取出版、傳媒陣地,并以此作為學術打壓和擴張的得力手段。“年鑒學派的成員奪取了傳媒社會的所有關鍵崗位。……大多數出版社負責歷史叢書的都是年鑒學派的人。他們身居要職,大權在握:哪些著作能夠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宮,全由他們定奪。享有霸權地位的年鑒學派還控制著新聞機構,并用其宣傳自己的出版物,從而保證其影響和爭取更多公眾。從研究實驗室到發行渠道,法國的史學生產幾乎都被年鑒學派所壟斷。”此外,年鑒派也深諳交結權貴之道。權力只向找準位置的人開放,幸運的是,年鑒派有自知之明,選擇了知識。“歷史和權力向來密切相關。20世紀的權力與以往有所不同,年鑒學派的力量在于成功地依附于這些新型權力。而權力則利用歷史學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性。歷史學家將某種意義賦予政權,并成為其合法性的擔保人。”事實上,后期的《年鑒》雜志與銀行家、金融家、資產階級政客和技術官僚們的關系日漸密切,而這些人正是政府倚重的力量。我們還應知道的是,社會科學不僅通過向年鑒派提供理論,也以提出挑戰的方式,推動著其發展。實際上,年鑒派的某些觀點是為論戰而提出的,如布羅代爾為對抗列維·斯特勞斯人類學的永恒結構理論,而提出他的著名的“長時段”理論。“他以歷史學家的王牌——時段來對抗列維·斯特勞斯”。
這些都一再表明,成功的學術政治,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現實中的年鑒派。但帶著主觀目的與某些現實權勢的結合,都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研究實踐。是的,我們在接受啟發的同時,也應鼓勵獨立和負責的懷疑。明人陳獻章在《論學書》中說:“前輩學貴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對某一外來學派的盲目推崇和眾口稱好,則往往反映了時下文化自覺意識的薄弱,無論這一民族曾是如何的偉大與輝煌。
注釋:
①彼得·伯克,劉永華(譯).法國史學革命[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4.
②弗朗索瓦·多斯,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③馮友蘭.中西哲學小史·序[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④余英時.從《反智論》談起,載《余英時文集》第二卷[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⑤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J].三聯書店,2005.
⑥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J].三聯書店,2005.
⑦李鐵,張緒山.法國年鑒學派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評價[J].東北師大學報,1995(01):31-35.
責任編輯: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