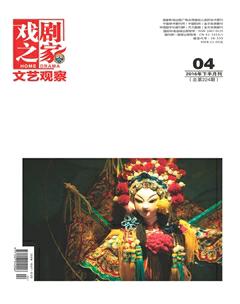唐·德里羅小說《白噪音》中的科技倫理解讀
劉含穎 韓靜 路卿
【摘 要】二十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單向度發展引發了一系列倫理問題,諸如環境污染、生態災難、資源枯竭、戰爭威脅等,危及人類自身生存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同時對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家庭觀等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美國后現代作家唐·德里羅的小說《白噪音》從當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在后現代生活的雜亂和無序中抽絲撥繭,解讀并批判技術理性主導下科技異化所引發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家庭人際關系的疏離以及人的自我迷失。
【關鍵詞】德里羅;《白噪音》;科技倫理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4-0283-02
二十世紀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并被廣泛應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自然環境、社會和人自身都產生了極其深遠而又復雜的影響:一方面,科技的發展有力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給人們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科技的單向度發展又產生了一系列倫理問題,諸如環境污染、生態災難、資源枯竭、戰爭威脅等危及人類自身生存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同時對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家庭觀等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何賦予科學技術更多的道義責任,如何把真、善、美等普世的倫理價值與科技有機結合起來,共同促進人與自然的協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自身的完善和發展,是縈繞在眾多有識之士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科技倫理問題,特別是技術(工具)理性統治下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自然、社會和人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當代美國先鋒作家唐·德里羅一直關注的焦點之一,其上世紀八十年代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力作《白噪音》乃是詮釋其科技倫理思想的一個理想切入點。
《白噪音》以藝術的手法生動再現了美國后工業時代的科技困境。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科學技術發展迅速。以科學技術為載體,消費主義、電子媒體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影響和控制日益加劇,并由此引發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化。同時,科技的單項度發展與資本主義制度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導致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無盡索取、環境污染和人類自身生存環境的惡化。德里羅從當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在后現代生活的雜亂和無序中抽絲撥繭,解讀并批判技術理性主導下科技異化所引發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家庭人際關系的疏離以及人的自我迷失。
一、科技單向度發展引發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
馬克思曾經指出:“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1]P775 現代工業文明的一個突出弊端是人類變得日益自大,誤讀了自己的力量,以致將自己創造的“文明世界”置于自然世界之上,將自然降低為可供掠取、奴役的對象,人與自然的關系日趨緊張。
《白噪音》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技術的世界,消費主義的盛行,技術的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在小說主人公杰克的家里,各種高科技產品、現代化的家用設施應有盡有,共同產生了“消費文化的白噪音”。商品的過度包裝產生了大量不可降解的垃圾,而人們的過度消費必然依賴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這意味著對自然無限的索取和擴張。因此,小說描繪了在高度發達的后工業時代一個被異化了的物質世界。在這里,環境惡化、垃圾遍地,“陽光、空氣、食物和水,每一樣都是致癌的”[2]P99,人類自身生存環境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主人公杰克一家生活在美國中部的一個小鎮——鐵匠鎮,在這個工業并非高度發達的小鎮上,環境的污染和人們生存環境的惡化依然觸目驚心。人們生活在“波與輻射”之中,各種現代科技產品產生的輻射、高壓電線產生的電磁場、媒體的噪音,構成了無時無刻都在威脅人類健康的“白噪音”。至于環境污染,“新聞節目里每天都報道一樁有毒物質的泄漏事故:致癌溶液從儲罐外溢,砷從煙囪冒出,放射污染的廢水從發電廠排放”[2]P191。杰克的兒子海因利希年方十四,前額的頭發就開始往后禿,杰克不禁納悶“難道我養育他長大的地方,附近就是我不知道的化學物傾倒場,有夾帶工業廢料的氣流通過?”[2]P22小說第二章“空中毒物事件”更加凸顯了科技的盲目發展對自然和人類自身可能帶來的危害。一種名叫尼奧丁衍生物的有毒廢物的泄露使全鎮人陷入了恐慌。在這種實驗室制造出來的死亡威脅面前,人們顯得如此渺小而又無所適從。最終,同樣是在高科技的干預下,通過在毒物團中央植入某種微生物,來吞食其中的有毒物質來消除這一威脅。但是,“沒有人知道,一旦霧團被吃掉后,有毒廢物會怎么樣,或者一旦這些微生物吃完霧團后自己會怎么樣。”[2]P177德里羅從生態主義的視角審視技術理性統治下現代工業文明的弊端。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不僅危害自然環境,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資源,壓抑自然,掠奪自然,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并會最終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
二、對科技的過度依賴導致家庭關系的異化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人類社會共同體的一種基本形式。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各種高科技產品走入尋常家庭,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科技不但影響人們的生活、娛樂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教育和溝通模式。傳統家庭以愛為基礎,家庭成員大多具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和奮斗目標。現代社會中,由于高科技的介入,人們的生活娛樂方式呈現多元化,家庭成員擁有相對獨立的人格、社交圈和生存方式,夫妻之間的“共同語言”減少,造成家庭穩定性的降低和離婚率的增高。
《白噪音》中的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就經歷了五次婚姻,而他的現任妻子芭比特也曾多次離婚。他們和他們各自多次婚姻中所生的四個孩子組成了一個美國后現代社會中典型的“后核家庭”。兩人的婚姻尚不足兩年,四個孩子不是同父異母,就是同母異父,這使得家庭成員之間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家庭成為了世上所有錯誤信息的搖籃”[2]P91。為了維系家庭關系的紐帶,增進彼此的了解,杰克的妻子芭比特定下一個規矩——每逢周五的晚上,全家六口人要坐在一起看電視。在杰克看來,“媒體是美國家庭中的一股首要力量”[2]P55,昔日相互依賴、彼此信任的家庭關系,必須要通過科技的產物——電視來維系。
家庭成員對科技的過度依賴,也減少了彼此間溝通的機會。杰克和妻子芭比特都被關于死亡的思索所困擾,總在想“誰會先死”。為了壓抑死亡恐懼、拒絕死亡,杰克求助于希特勒研究、超市購物和看電視,芭比特則選擇放棄倫理、道德、情感,出賣自己的肉體來交換一種高科技的精神藥物——戴樂兒。兩個人面對恐懼和苦惱,沒有相互溝通、共同應對,而是在技術理性的思維定勢控制下,企望科技及其附屬產品來為他們解除困境、超越死亡。杰克的兒子海因利希常常心事重重、難以捉摸,卻從不將自己的心事向家人傾吐,他不顧自己的感覺和正在下雨的客觀事實,執意強調晚上才會下雨,僅僅因為“收音機里說今晚”;芭比特的女兒丹尼斯擔心母親濫用藥物會產生副作用,卻從不開口向她詢問,而是自己鉆研《醫生手冊》,查看“一串串的藥名”。科學技術給現代家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劇烈沖擊,對科技的過度依賴,顛覆了傳統的家庭模式,造成家庭成員間的疏離和關系的異化。
三、技術理性主導下人的自我迷失
法拉克福學派左翼代表赫伯特·馬爾庫塞對當代發達工業社會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批判。他認為,由于科學技術脫離道德、倫理單維度發展,當今的工業社會已呈現病態化。技術決定了一切,科技必然帶來進步的定性思維使得技術成為純粹單向度的技術。技術的強大力量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約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海德格爾所倡導的人類詩意的生活已經被異化。技術理性支配下,自然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枯竭、社會矛盾的加劇、戰爭的威脅等無時無刻加劇著人的恐懼、焦慮、困惑,人的自我迷失也就成為必然。
技術理性主導下的單向度的人失去了對真、善、美的追求,對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它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失落、心靈的荒蕪、同情心的泯滅、道德的淪陷和信仰的喪失。《白噪音》中的人們端坐在電視機前,寂靜無聲、麻木不仁甚至是幸災樂禍地觀看水災、地震、泥石流、火山爆發,“每一場災難都讓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災難,看到更大、更宏偉的東西。”[2]P71杰克和海因利希收看從某個殺人犯家后院挖掘尸體的現場報道,當沒有新的尸體被發現后,“一片期望落空的感覺。愁意和空虛感籠罩全場。沮喪、遺憾的情緒。我(杰克)努力不去感到失望。”[2]P24
如上所述,對技術的過度依賴造成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疏離,因而美國文化所推崇的家庭價值觀無法為人的心靈世界提供慰藉和庇護。同時,傳統的宗教精神業已淪落,小說結尾處被杰克認為理所當然懷有偉大古老信念的瑪麗修女,自己并不信仰上帝和天堂,只是佯裝相信。人們為了填充自己失落的精神世界,求助于媒體和消費,由此誕生了美國現代社會的兩大經典場景——舉家圍坐觀看電視和超市購物。電視融入了美國人的精神生活,人們盲目相信媒體的只言片語,卻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感知和判斷。在工業社會所倡導的消費文化的刺激下,超市簡直成為了“從精神上充實我們、裝備我們的生機勃勃的宗教殿堂”[2]P40。杰克全家因瘋狂購物而喜氣洋洋,通過購物,杰克實現了價值和自尊上的擴張,“使自己充實豐滿了”。《白噪音》從當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平凡時刻出發,生動展現了技術理性指導下美國人精神世界的重重危機、悖論、掙扎與迷失。
德里羅的小說《白噪音》聚焦于八十年代美國后工業社會,從當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解析并批判技術理性主導下科技單向度發展所引發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家庭人際關系的疏離以及人的自我迷失。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如何規避科技對自然、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負面影響,如何將科技與倫理有機結合,在發展技術的同時恪守普世的價值觀念、社會準則和行為規范,如何賦予科技以更多的道德責任和人文關懷,是德里羅對科技理性統治下的后現代社會人們的存在方式提出的質疑和提醒,也引發了我們對科技倫理問題的眾多思考。
參考文獻:
[1]馬克思.馬克思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唐·德里羅.白噪音[M].朱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3]陳愛華.法蘭克福學派科學倫理思想的歷史邏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4]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5]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6]王諾.歐美生態批評[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