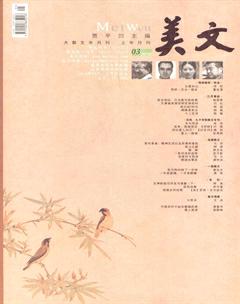眼睛里有光
鄭艷
一個人很孤單。
一群人很溫暖。
40位特邀嘉賓,50位案例嘉賓,600多位投身教育、關注教育的參會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主辦的“LIFE教育創新首屆峰會”,集聚了一群眼睛里有光的人。
“教育關乎生命、融于生活、適于終身,教育創新源于社會中每個個體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點滴改變。”這是主辦方的倡導,亦是參會者認同的理念。
一
什么是好的教育?
帶著這樣的反思,主辦方遴選了一批可持續、可推廣的教育創新案例,梳理出若干深度交流的主題。通過實踐者的分享,來探討應該怎么做的問題。
兩天時間,四個分會場。從早到晚,談論主題涵蓋:“學校改革如何從現實中突圍”“課程改革走向何方”“多樣化的辦學方式”“無處不在的藝術教育”“多元文化的傳承”“教室里的革命2.0”“零零后零距離:傾聽學生的聲音”“互聯網時代的個性化學習”“教師如何創新”“教育如何培養思辨能力”“教育公平3.0”“為職業做準備的教育”“新父母,新教育”等。
一批校長以各自風格分享學校的管理理念與實踐:北京的竇桂梅、王錚,重慶的劉希婭,成都的李勇,山東的張福濤,深圳的程紅兵,寧波的李慶明,內蒙古的干國祥,山西的寧致義……
一批教育創新案例的生動呈現:泉源實驗班、成都華德福、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詢中心、北京蒲公英中學、日日新學堂、歌路營、長沙“工之友”……
一批老師們的精彩講述:錢鋒的“萬物啟蒙課程”,陳耀的“一千零一夜家庭實驗室計劃”,徐莉的主題式教學實踐……
還有圍繞不同主題展開的思想碰撞和交鋒。
微改變、微公益、微創新。
在獲得肯定的同時,社會各界對每個案例、每個實踐者也都有一些質疑和批評,每個話題也是如此。這些嘗試都在探索的過程中,值得關注、思考、借鑒,因為教育本身不應該是固化的。
這樣的會議和活動,匯聚創新型教育個人和團體,并幫助這些行動傳播、反思和成長。
二
好的教育人,該有怎樣的胸襟與眼界?
觀摩學習這次會議,帶給我深深觸動和感動的,是一個個教育創新案例背后的一個個實踐者,一個個教育人。
每個人都有局限,或囿于現實條件束縛,或拘泥于經驗,但在一場場交流分享中,我看到這些教育人對自身的突破,對環境的突破,看到執著努力的打開局面,看到自我的提升,以及由“我”到“我們”的團隊拓展。
胸襟與眼界不斷打開,才會屢有新思、新念、新境地。
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我和伙伴們在房間討論。結合我們自己這些年的辦會體會,分析這次會議帶給我們的啟發。從內容設計到嘉賓邀請,從媒體互動到會務細節……最后落到一個個具體的教育人,落到“百聞不如一見”時的真切感知。
我說,這是我的參會經驗中,收獲最豐富的一次。這收獲是多維度的,將作用于我的本職工作,更將作用于我的生命狀態。
三
“他的故事依舊讓人期待。”
這是2013年青年節,《南方人物周刊》對張良的專訪中,結束時的句子。彼時,經歷了20年媒體和商業領域的張良,開始做回內心深處的自己:投身教育領域,做“有意思、有意義”的事。
對張良的關注,源于十幾年前,源于《南風窗》。當時供職于湖南衛視,在《新青年》欄目中訪問了時任《南風窗》總編輯的秦朔。后來,又補充采訪,整理成文字專訪,題為《責任感不是面具,是我們的心靈》。
這本雜志讀得多了,就越來越對張良留下印象,對由記者做至副總編輯的他,其文字中體現出的見識與情懷留下印象。
雜志生存的真實基礎,來源于它的人文定位,來源于擁有出色策劃和采寫能力的團隊成員。秦朔和張良,是這本雜志獲得廣泛影響的重要原因。
離開《南風窗》成為CEO之后,張良令人不可思議地投入災區調研,寫出被稱為新聞專業主義范本的作品《汶川地震168小時》。
又然后,他投身教育領域,躬身實踐,成為泉源實驗班的首任班主任。
“在20多萬所中小學中,一定有不為人知的暗火在涌動。它們的光芒微弱,無法照亮更大的范圍。而我想知道,這些火光如何發出,火種又該如何傳遞。”
張良現為“蒲公英教育智庫”副總裁。該智庫出品的《新校長》雜志,我和伙伴們都是訂閱用戶。
這次會議上,張良分享了“泉源實驗班”的實踐經驗,提出“未來教育將告別手工時代,進入系統的對決。”
作為同樣在新聞行業體會過魅力,亦感知過局限的個體,張良的轉型與探索,給我帶來感染、引領和力量。
四
“關注和幫助一下長沙的‘工之友,農民工自己組織起來的教育自救,非常罕見,非常了不起!”
這是會議結束,收到我的致謝留言后,楊東平先生給我的回復。
赴北京參會,我見到熟悉而親切的鄭琰老師、劉堅教授。見到許多不熟悉,但氣質接近的參會者。
會議有許多感人瞬間,在我記憶里,最清晰的,是楊東平先生的哽咽。
當時,我正坐在那個分會場。楊先生是點評專家。點評田生梅介紹的長沙“工之友”這個創新案例時,楊先生說,“我沒想到她們的基礎這么薄弱,這么不容易……”
哽咽,幾秒鐘的停頓。
臺下,許多人的眼睛都濕潤了。
只有真正的心懷悲憫,才會在不經意間,真情流露。
楊先生一直跋涉在促進教育優質與公平的路上,無論遭遇什么,他始終在行動。他堅信,更多公眾參與教育的對話與創新性的行動,中國教育的生命力和多元化才能夠得到增強。他是“知行合一”的信仰者。
這次會議的成功,也體現出他個人和團隊的強大影響力。
五
這次赴北京觀摩學習,帶給我最大的收獲,是進一步明確了方向感。
寫下這篇隨筆時,我剛剛將十幾年間,刻錄個體生命年輪的文字進行了整理,進入編輯出版流程。在回看的過程里,我發現,雖然生命不可思議,但記憶真是有選擇性的。
所經歷過的猶豫、懷疑、彷徨、沮喪等等灰色心緒,都沒有記錄下來。沉淀下來的一個個細節,是感召、歡愉、感動、莊嚴……
價值觀決定行動。看到這些記錄,我發現,多年來,自己的價值觀是:生活的客觀現實已經諸多灰霾,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我必須盡可能擁抱光亮。
在整理的過程中,一個念頭愈發清晰和強烈:這本散文集之后,要收斂散點式的吸收和呈現,要選擇一個領域沉潛下去。
這個領域,即是教育。
這念頭,源于師范專業所埋下的心靈火種,源于這些年的因緣際會,源于靠近了真正優質的教育人。
作為一個眼睛里有光的人,我希望和一群眼睛里有光的人一起進行生命旅行。
如張良所說,沒有比教育更有趣更持久的行當了,它超越一切的隔閡,有人的地方就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