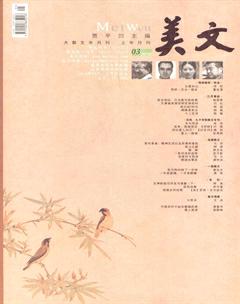鵝湖在哪里
譚仲池
鵝湖在哪里?
鵝湖在鉛山縣的綠色畫卷和蛙聲稻香里。尋訪鵝湖,是想了卻常在心中縈繞的一件心事。多少年來,我總想去感受鵝湖這片錦山秀水,殷實風情的生活氣息。相傳鵝湖山上有一個湖,種滿了荷花,當地人稱之為荷湖。東晉時,這里住了一戶姓龔的夫婦養了許多白鵝,有一天白鵝不見了,但看見天上出現了一道彩虹,像紅鵝一樣。從此,當地人就更其湖名為“鵝湖”。
一清早,我就走到信江邊。看到江上飄拂的乳白色的晨霧,籠罩著醒來的鄉村和朦朧的青山碧野。此時,我仿佛聽到清風里傳來了“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美麗柔婉的詩句。頓時,就覺得天高山遠,琴瑟和鳴,鄉音繚繞,心胸無比開闊,好像腳下的江水都在涌動奔放愉悅的波濤。
這波濤就托著我的雙腳和貪婪的心,緩緩地在鵝湖的大地上漂泊。此時,我的眼前那連綿不斷的蒼山,似乎在有節奏地搖滾著濃重的綠色。田頭坡邊聳立的青磚瓦屋,也掩映在綠樹翠竹里,折射著太陽鍍上的金色光芒。看著這鄉野的美麗晨景,我在想像晚唐詩人王駕寫《社日》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滿足和自豪的。詩曰:“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棲半掩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像這樣的詩畫情景,極其生動形象地描繪出當時鵝湖的殷實生活和淳樸鄉俗。不能不讓今人也生幾分羨慕。是啊!我們正在建設生態和諧文明富裕的新農村,不就是要實現這種生態環境優雅,人心向善向美,物質文化精神生活豐富的全面小康之夢么?習近平總書記去年4月在三亞市考察新農村建設時就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這個“老鄉”太重要了。是啊!農民富了,農村興旺了,國家強盛就有了根基。
今天,我就是要來感受一下鵝湖老鄉的現實生活景況。翻開手中的《鉛山簡介》,有一組這樣的數字讓我興奮感慨不已。這個地處武夷山北麓,面積2176平方公里,人口43萬的山區縣,已成為全國“十二五”水電新農村,電氣化規劃江西省的示范縣。全縣森林覆蓋率73.7%,山林面積250萬畝,活立木560萬立方米,毛竹面積52萬畝,活力竹6600余萬根。全國第二大銅礦也坐落在境內。現在的鉛山縣正全面融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和海西經濟區建設的宏偉藍圖之中,呈現出一片蓬勃發展生機。鵝湖山國家森林公園已成為鉛山的一張精美名片。這就是我看到的綠色鵝湖。舉目四顧,這里的鄉野、村落、小溪、湖塘、牛羊、白鵝、雞鴨,乃至鄉路上,屋場邊奔跑的小狗,都浸潤在澄凈流動的空氣,飄拂著清甜的花香里。正在田間勞作的鄉親,彎腰把一行行新秧和著心中的金色夢幻,一齊插入田間的明鏡里。
鵝湖在哪里?
鵝湖又在紅茶之鄉的清芬和連四紙的竹影里。當我們在老鄉家里品賞清甜的紅茶,看到河口古鎮的舊街上,仍留有不少明清建筑。其房屋向內縱深悠長,門楣則都是石塊相拼而成。門檻也是石條壘就。歷經歲月風雨洗禮的青磚石塊巷道現在仍可見車轍和腳踏出的深深印痕。這里是“萬里茶道”第一鎮。也又因造紙業的興起成為江南五大手工業中心之一。據史料記載,當時這個小鎮,就有茶行50家,大小紙店100多家,會館10多家。幾百年來,“河口紅茶”“連四紙”名揚四海。接著,我們來到漿源村造紙廠,就看到了用傳統方法造紙的全過程。當我們用手觸摸已烘干的新紙,那種薄而爽,潤而柔,雅而文的感覺在心中油然而生。特別是我們又看到用“連四紙”新印刷出來的線裝書《稼軒詞》時,更萌生思古之幽情,大家都感嘆不已。現在“連四紙”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更看到了它生機蓬發的光明前景。
更叫人難忘的要算在武夷山的桐木關采茶。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采茶。一開始,我就主動向正在采茶的鄉村姑娘請教。像她們一樣,細心地、輕輕地摘下茶樹上,那片片綠綠的嫩芽。這些鮮嫩的茶芽沾在手上,有一種清潤而細軟的感覺。我生怕它們飛走,還偷偷把幾片嫩芽,放在口里細細咀嚼起來。開始有些許苦味,漸漸苦味變成了清甜,清甜變成了清、甜、香,然后是說不出的美妙滋味。就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清爽,沁入心田。我當時就想一定要買些新茶回去,珍藏起來,只供文朋詩友品賞。我回到賓館看資料才知道,今天我品嘗的野茶,叫“正山小種”,是河口紅茶中的上品,產自武夷山桐木關,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就遠銷亞歐市場。有史料記載,這種紅茶一直是英國王室的傳統茶飲。
鵝湖在哪里?鵝湖還在辛棄疾壯懷柔腸的辭采和鵝湖書院的弦歌里。在信江北岸山頭,矗立著南宋著名愛國詩人辛棄疾的巨大雕像。他左手撫劍,右手握卷,背負鉛山縣城,北望中原,神態沉靜,目光如炬。鉛山是辛棄疾最后的歸宿,是他的第二故鄉。辛棄疾晚年就是在鵝湖這片山水間,披星戴月,挑燈看劍,聽蛙填詞。他現存的629首詩詞中,據考證,就有225首是隱居鉛山鄉野時所作。尤其是,他看到山河破碎,竟痛心疾首地喊出,“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吶喊。仰望辛棄疾,我看到了沙場烽煙,刀光劍影,也聽到了他“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可憐白發生”的慷慨感嘆;又看到了他“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凄然喜悅。就是這個辛棄疾呀:你的愛國情懷,國恨鄉愁,劍膽詩心,曾照耀和激勵著一代一代的炎黃子孫為國為民壯懷激烈,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是呵!當我們在首陽山你的墓前默默站立,向你傾吐心中的萬千感懷之時,我分明看見滿山的樹木花草,都頓時在明媚的陽光里,輕揚著無限的綠之蓬勃和綠之波濤,散發著大自然生命的無窮氣息。這就是你的魂靈和精神的風華,麗辭的雄韻在飛翔、揮灑、升騰。青山常在,詩心依然活在蒼翠和歲月的流光里。
鵝湖真是太古典、太嫵媚、太深邃、太壯美。雖然,我們一路馬不停蹄,風塵仆仆,汗濕衣襟,但游興未有絲毫的減退。相反,我們如在讀一本大書,已經步入其中最動人的篇章里。那里有更崎嶇和深幽的故事;有更撥動心弦的優美旋律。我們癡迷地朝鵝湖的深處走去。不知不覺就來到了一片氤氳著遠古幽思,深厚人文氣息的鵝湖書院。這是一個圣潔的文化殿堂。院門內額上的“圣域賢關”就道出了鵝湖書院的神圣。《漢書·董仲舒傳》云:“太子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因我是從湘江邊的岳麓山麓出發,來這里造訪鵝湖,自然也就有心,要用自己的腳步來丈量鵝湖書院與岳麓書院的歷史淵縷和文化情緣。答案很使我欣慰激動。鵝湖書院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當時謂“四賢祠”。南宋淳祐十年(1250),宋理宗賜名為“文宗書院”。明朝景泰四年(1453),又重修擴建,并正式定名“鵝湖書院”。我在鵝湖書院西碑亭的碑上看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國子監五經博士、進士吳士良在碑中寫道:“天下四大書院——嵩陽、岳麓、白麓洞、鵝湖書院”。宋代哲學家朱熹與陸九淵兄弟的“鵝湖之會”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而朱熹和張栻的“岳麓會講”則發出思想文化辯論之先聲。鵝湖書院的“窮理居敬”和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就如兩盞明燈光耀萬世。兩書院這種明理、傳道、解惑、潤心,求真,追效先賢,治學致知,教人育才的千古高風,也如鵝湖書院中的詠石磨對聯,道出了千年書院講學之奧妙:“石磨咕咕,尋蹤探理,千回轉;燈盞熠熠,明本推心,萬古芳。”歷史果然如石磨的哲學,至今鵝湖、岳麓書院仍然弦歌不絕,書聲如縷,是當代學子們心靈的源頭活水,穿越塵世的智慧明燈。
我在鵝湖書院內徘徊沉思,我不敢驚擾這里的樹木、花草、亭臺、水榭、蓮池,乃至屋閣飛檐上的小鳥,地上的一片石板,一塊青磚。我悄悄默立在正在書院芳草地上,曲徑邊寫生的大學生身后。看他們用手中的筆,牽著虔誠的心緒,用纖細的線條,在描繪鵝湖書院遙遠昨日的莊嚴面容、晴朗聲音,從容腳印和背影。看著從這群年輕學子手中,站立起來的鵝湖書院,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動,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是啊!現在我們進入了信息化的時代,世界變成平的。許多人的閱讀和思考漸次變得碎片化。人們忙碌、奔波的路上,總是容易被眼前的功利,心中的浮躁牽引而不能自拔。常常被燈紅酒綠,浮華繽紛,奢靡熏風,五光十色的物質和精神誘惑弄得頭昏腦脹,不知所向。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的步子不能沉穩,心不能“慢下來”,思維不能理智,感情不能拒塵,那么這個世界能好嗎?此刻,我也更深一層地領悟了朱熹的《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所蘊含的極深遠旨。是啊,我們偉大的祖國,偉大的民族,偉大的人民要實現自己的夢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遼闊的神州大地永遠都需要有一條奔流不息,清如許的文化河流。
鵝湖在哪里,就在追夢人的尋覓里。
鵝湖在哪里,就在頭上飄飛的白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