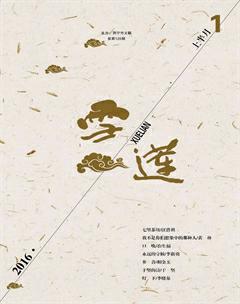為了所能抵達的遠
昌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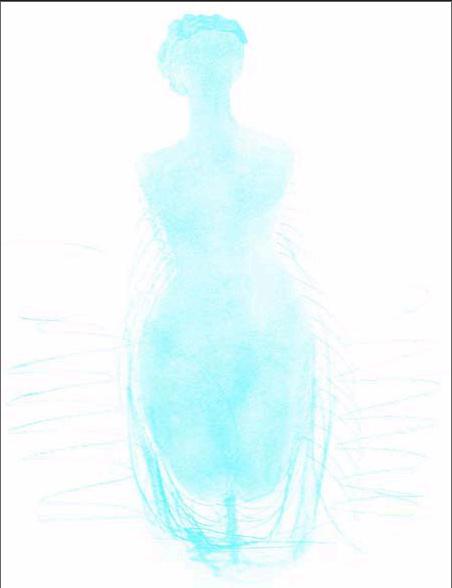
雪歸是這些年青海青年作家群中較為突出的一位女作家,小說等文學作品頻頻見于各類省外文學期刊,2012年被青海省作協(xié)推薦至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深造,在此之前,她的小說作品還曾獲得過全國電力文學大賽單篇作品一等獎、省政府文藝獎、青海省青年文學獎等,作家出版社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她的中短篇小說集《暗蝕》和《無腳鳥》,著名評論家、作家雷達、嚴英秀、井石、才旦、閻瑤蓮、馬光星等人相繼為其點評作品、撰寫文藝評論,刊于《文藝報》等報刊雜志。我長期關注雪歸和她的作品,她對于文學的熱愛與執(zhí)著令我感佩,而其小說中努力書寫的當代生存現(xiàn)狀以及作品中深含的悲憫情懷,更令我肅然起敬。
著力身邊資源的萃取與釋放
作為一名電力作協(xié)會員,雪歸創(chuàng)作了許多電力紀實類作品,曾先后參加了被譽為“電力天路”的青藏聯(lián)網(wǎng)工程和新疆與西北主網(wǎng)聯(lián)網(wǎng)750千伏第二通道輸變電工程建設的現(xiàn)場采訪。在柴達木腹地,在瀚海戈壁,在昆侖山下,她與數(shù)千建設者一起深刻感受了電力工程建設的艱辛與繁復,親眼見證了高原大地上涌動的一波又一波電力工程建設熱潮。當建設者“一切為了工程建設,一切服務于工程建設,一切服從于工程建設”,用勤勞和智慧,為著萬千百姓的光明進行著一項偉大的事業(yè)時,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去感悟、去體驗、去反思,寫下了《電力天路上最美麗的剪影》《黃沙磧里綠色新能源的春天》《吉祥大柴旦》等通訊和報告文學作品,發(fā)表于《中國電力報》《青海日報》《絲路陽光》《青海湖》等報刊雜志。
在雪歸的報告文學作品《飛越鹽湖》中,我印象深刻的有這樣一段:“采訪不時被打進來的電話打斷,這個間隙,我留意到窗外挺拔的青楊在風中高高挺立。這是高原常見的樹種之一,它把根深深地扎進這薄脊的土地之中汲取養(yǎng)分,它努力招展枝葉進行光合作用。為改善這大漠的環(huán)境與氣候,無言地奉獻著自己。看著它在窗外搖曳生姿,我聯(lián)想到這些天接觸到的這些建設者,他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家。風霜雨雪中,他們始終堅守自己的崗位,用智慧和汗水鑄就就一座座無字的豐碑。”白楊樹的精神是枝枝葉葉緊密團結,倔強挺立,哪兒需要它,它就在哪兒生根發(fā)芽,不論風沙雨雪,不管干旱洪水,它總是那么筆直,那么堅強,從不動搖。作者由眼前的建設者聯(lián)想到高大的白楊樹和白楊精神,可謂真正抓住了其精髓所在,形象地展現(xiàn)出了電力建設者頑強、向上、堅韌、奉獻的品格。
“巍巍昆侖不會忘記,漫漫黃沙和發(fā)展中的鹽湖,見證了這里曾經(jīng)演繹的無數(shù)場‘戰(zhàn)役,在促進新疆電力送出,徹底解決青海缺電問題,服務地方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它們還將繼續(xù)見證由無數(shù)鏖戰(zhàn)高原的建設者實現(xiàn)的每一步跨越。”類似這樣的片斷,在她的一些電力紀實類作品中有不少,如果不是深入施工一線,如果不是與建設者同甘共苦,如果不是細致入微地體察感受,很難有這樣深情而濃烈的語言。我們有些作家,總是習慣于閉門造車,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制造了不少假、大、空的文字,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其自娛自樂的創(chuàng)作行為習慣并無傷大雅,但真正的創(chuàng)作,一定要深入到生活中努力發(fā)掘和提煉,沉下心來認真思量,才可能有好的作品產(chǎn)生。雪歸以文學的形式,著力對身邊的資源進行了有效的萃取與釋放,值得肯定。
悲憫情懷下的關注與思考
除了電力紀實類作品,雪歸還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小說作品,以關注底層弱小、挖掘美好人性為視角,用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塑造了許多卑微卻堅韌的生命,展示了現(xiàn)代社會的紛繁復雜,彰顯了女性作家的人文關懷。
我堅信直觀與真切的苦難體認,更有利于一個創(chuàng)作者靈魂深刻,精神堅挺,也許這正是雪歸許多小說作品中所彰顯的悲憫情懷的來源之一。譬如《請你讓我開一次會》,小說寫了一個人迫切地想開一次會的念頭,不無夸張之嫌。那么現(xiàn)實中,真的有人想開一次會嗎?參加一次會議的意義又在哪里?當臨時工——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進入城市,遍布每一個角落之時,他們能否真正被這個城市所接納和認同?小說借開會說事,小說想表達的,遠遠超過參加會議本身,有誰知道小說的主人公何楚珪(“何楚珪”諧音“何處歸”,別有深意)又將歸何處?而《饑者饕餮》則是表達了一種心靈饑渴的狀態(tài)。孤苦伶仃的陸馬,與最低賤的魚——麥穗子,形成了依存和對照的關系。然而,麥穗子一條條死去,陸馬也被粗俗的笑聲驚醒,等待落空,生活依然孤單而苦澀。他“饕餮”了所有的麥穗子,用絕望和墮落,在無望的人生里掙扎。《杏花天》則將目光移向農(nóng)村,當尚秋菊進入城市,村莊烙印在她身上的痕跡越發(fā)清晰。單純、善良、勤勞、樸實……用這些詞形容尚秋菊似乎遠遠不夠。和丈夫長期分居兩地艱難度日的尚秋菊,和城里人尚敏的相遇,揭開了一段無比溫情的序幕。小說中尚秋菊和城里人尚敏那種惺惺相惜的體恤和理解,以及尚秋菊最終因尚敏一家,與丈夫之間的矛盾、沖突、抵抗,無一不讓人動容且心碎。《我不說》中,雪歸將思考的目光投向不為人注意的角落,為弱者吶喊,在他們那孤苦絕望的心靈上撫摸。
雪歸善于從細微之處入手,從很多微弱的雜相進入,一個不被人注意的細節(jié),或者眼前掠過的一種景象,都會引發(fā)她的聯(lián)想,刺激她豐富的內(nèi)心。《我不說》中靠撿破爛生存的啞巴,《我把蔣之菡丟了》中給富二代當保姆的小江,《鴿子的羽毛》中站大腳的耿雞換,《給你柴油一萬噸》中一次次面臨失業(yè)的小靳和“我”,《饑者饕餮》中孤苦無依的陸馬,《綻放》中被欺凌和侮辱的小矮人李海山,《金碗銀筷》中王根發(fā)一家窘迫的生活現(xiàn)狀,《暗蝕》中在現(xiàn)實面前倍感無力的桑青……等等類類,當社會現(xiàn)實作為一種堅硬冷漠無可跨越的事實,讓一些人進退失據(jù)時,雪歸卻以其獨特的敏感視角去發(fā)現(xiàn)和捕捉,又以最直觀的方式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白先勇說: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用文字將人類心靈中最無言的痛楚表達出來。他說自己文字中的感傷和悲劇色彩與生俱來。我從未和雪歸探討過她寫作的中悲劇性(有人理解為頹敗),早有哲人說過,悲觀是因為含了太多的希望。我相信她的骨子里,希望與悲劇色彩并存,其悲劇性色彩濃厚卻隱含希望與理想色彩的一篇篇小說便是佐證。
不少人不止一次呼吁:多一點悲憫情懷,少一點看客心態(tài)。雪歸借助小說文本,用她的方式,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懷著悲憫的情懷,執(zhí)拗地表達著她的關注和思考。雖然時代喧嘩掩蓋了疼痛,讓一些人逐漸鈍化和麻木,但是,總有如雪歸一樣的警醒者,用自己的方式發(fā)聲,主動承擔起了喚醒的任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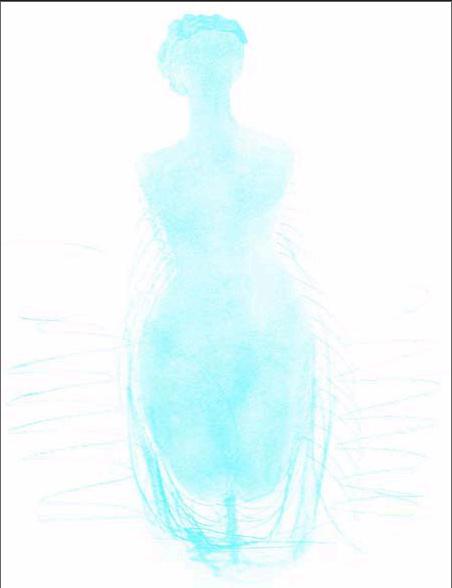
多維視角下的生活與生存本質(zhì)體認
生存還是死亡,《哈姆雷特》中丹麥王子的經(jīng)典獨白在莎士比亞之前幾千年就已經(jīng)存在,而在他之后的幾千年人們還在不斷地思索。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大概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生與死,都是人先天就有的傾向。關于死亡,我不想說太多,但是存在體驗千人千種,只是怎樣表現(xiàn)的問題。
雪歸的小說,有許多關于生活與生存本質(zhì)的體認。比如《我把蔣之菡丟了》,蔣之菡的世界乖戾無常,危機四伏;而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跡象,當小說的主人公“小姜”最終因失望而絕望,然后毅然離開冷漠的城市,回到被昏黃的燈光包裹著的小鄉(xiāng)村。而她的回歸也讓她重新找到了希望。從小說中結尾的那一句“沒人有穿,不是更有理由做下去嗎?”,我們可以看出小說企圖說明,退卻,有時也是一種不妥協(xié);小說還想表達,我把蔣之菡丟了,可我不想丟了我自己。
《我不說》中,我是啞巴,我如何能說?我怎樣說?我當然不能說。當受到凌辱的“姐姐”在黑暗中一聲聲哀求“我”,讓“我”不要說時,“姐姐”已然對這個世界完全絕望。生存的孤苦無依,希望的渺茫,生活的冷硬,這一切一切,都是壓在貧弱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當“我”存著最后的希望,回到起點想重新開始以前曾深惡痛絕但現(xiàn)在想來不乏溫馨的地方,卻發(fā)現(xiàn)那里變成了廢墟一片,“我”只有在遍地瓦礫中,久久地失神。我似乎進退失據(jù),出路在哪里?回去還是接著找尋,作者留下了謎題待解。
《給你柴油一萬噸》中,當一萬噸柴油突然進入這個小小的隨時瀕臨關門的民刊編輯部,當利益猙獰的爪牙橫空出世,兩個在城市里艱難漂泊的小青年,是否能抵抗誘惑?在利益的沖突之下,他們是否能安全無虞?柴油事件,徹底瓦解了一份小小的民間刊物。其實即使沒有柴油事件,《青楊坊》的生存,依然岌岌可危。這兩個青年,注定是悲劇人物。
再如《赤膽熊心》,膽汁熊是人類向大自然瘋狂攫取的又一個悲劇。小說從一只被束縛的膽汁熊的視角出發(fā),向我們展示了一只熊眼中的世界:疼痛、絕望、恐懼、饑餓……在這樣一個殘忍而冷酷的環(huán)境里,是隱忍茍活,還是徹底崩潰?膽汁熊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當那一只不愿徹底崩潰的膽汁熊,親手掏出那血淋淋的一團時,血腥、殘忍、絕望、死亡,作者向我們展示這些時,字里行間的存在之痛,震撼人心。
這些小說不乏多維視角下的悖論。不能否認,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悖論,但這正是生活的精彩,也是我們存在的精彩。如果說加繆的西西弗是荒謬的悲劇英雄,主要因為負重的他所經(jīng)受的磨難。那么當日復一日不斷重復一個沒有效果的行為,根本就是悖論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而已。或者主動出擊或者被動承受,雪歸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以文學的善意消化現(xiàn)實的不公
對于社會生活中的不公現(xiàn)象,我們應該持什么態(tài)度,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雪歸曾寫過一篇創(chuàng)作談,題為《如一粒塵埃的微小存在》。她說:“如一粒塵埃,有許多人在漂浮的狀態(tài)下以掙扎的方式生存。長久以來,現(xiàn)實生活之中有些人可能會生活在別處或者假裝生活在別處,可能會看不見這些人生存的方式。” 雪歸坦承,在現(xiàn)實面前深切的無力感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疼痛感,使她在不得不順受人世無常的同時,對生活與生存的本質(zhì)不同有了逐漸深切的體認,這也應該是她從早期的單純愛好轉為后來堅持寫作的動因之一。
長期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文藝理論和本土文化研究的何光渝曾說過:“文學的關鍵,在于你是不是僅止于謀求那種背離歷史和時代前進方向的‘自由,你對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切,是不是具有肯定和弘揚正面價值的能力……是否由此而做出了真正文學性的思考和表達。”閱讀雪歸的小說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不僅僅只停留在講述撲朔迷離的故事和渲染悲劇氣氛上,她還運用了許多諸如隱喻、象征等手法(如《饑者饕餮》中的魚,《杏花天中》的杏花,《赤膽熊心》中的膽汁熊,《請你讓我開一次會》中的會議等等),通過對人物繁復曲折的命運演繹,寄托出作者的一番深意。
雪歸企圖用自己對世界的善意消化不公:《柴油事件》中兩個充滿了理想的年輕人,因為柴油事件分崩離析,他們遭受的不平待遇,完全是現(xiàn)實社會的一個縮影;《金碗銀筷》中的老海,因為妻子生病便偷竊朋友的寶貝石頭,而主人公王根發(fā)卻一心想著石頭變錢幫老海一把,忠誠與背叛同時登場;《潮退浪涌》中,主人公潘昕為養(yǎng)活植物人丈夫,獻出自己的身體來改變命運的軌跡,人微言輕的保安李樹森卻時時關照并溫暖著她,艱辛困頓中又不乏溫暖與愛意;《春尖尖》中周蕊對母親的體貼、理解與寬容,令人動容;《這個冬天不太冷》中,冷漠而貧弱的李司馬被桑吉師父所感動,最終參與救助那個受傷的藏族小孩,其間所展現(xiàn)的人性的真、善、美,以及充溢期間的正能量,讓人備感溫暖與振奮。
雪歸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投向身邊的每一個在漂浮的狀態(tài)下以掙扎的方式生存的個體,他們的悲歡與榮辱,也是她的悲歡與榮辱,她已然是其中之一。在她的寫作過程中,她說她極力排斥和抵制著那種不痛不癢式的自我麻痹或者自我陶醉式的寫作,努力想透過生活的庸常,抓住痛點寫作。如何跳出一己之悲歡,在震撼人心中,達到對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高度關注和反思,這是一個真正具備道德素養(yǎng)的作家所應追求的目標。風景再遠,有志者終能抵達。希望“用一根針挖一口井”、用文學的小勺在生活的大海中舀水的雪歸,能夠更加謙卑、認真地寫作下去,最終實現(xiàn)所能抵達的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