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運行特點
李良品++廖佳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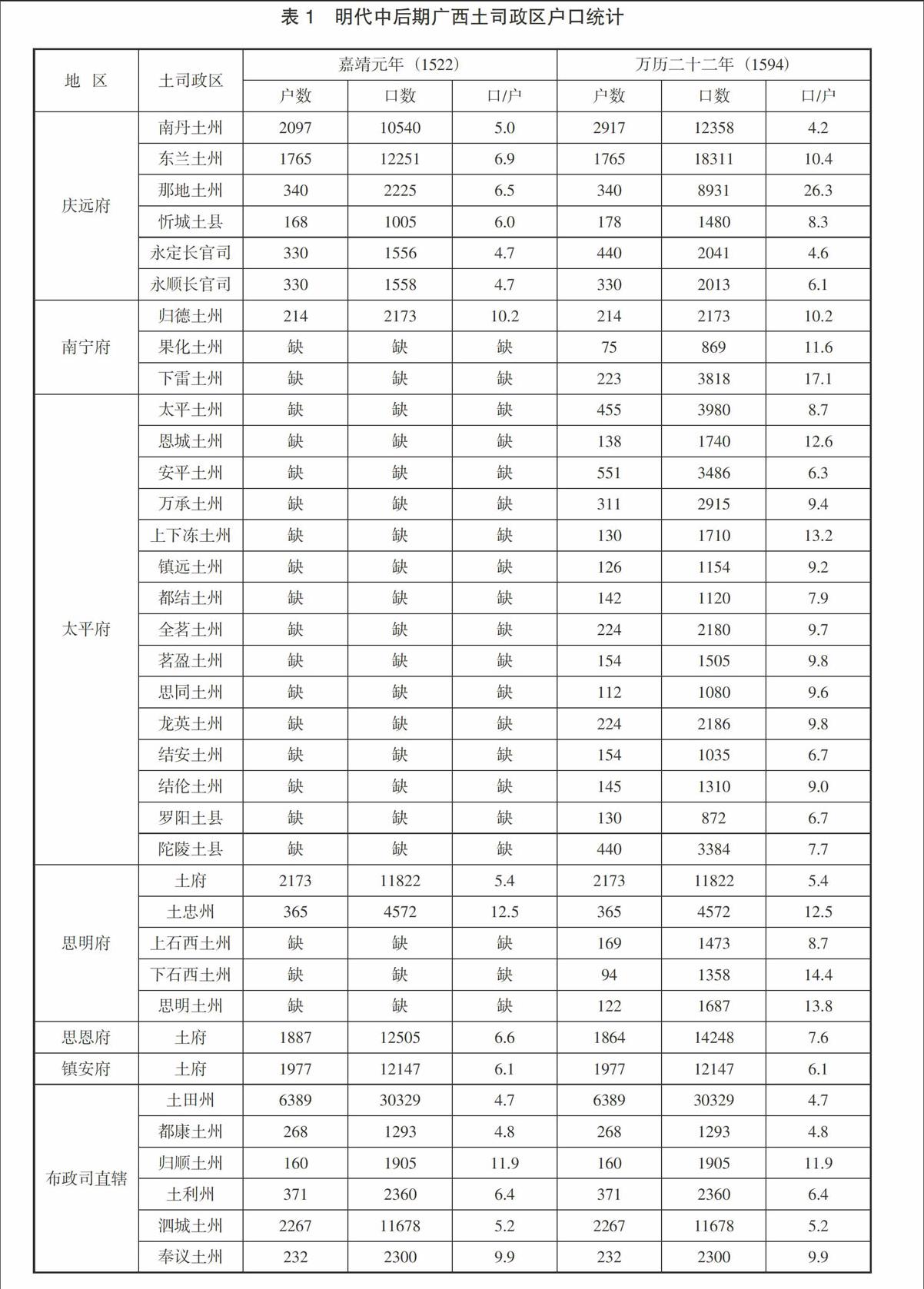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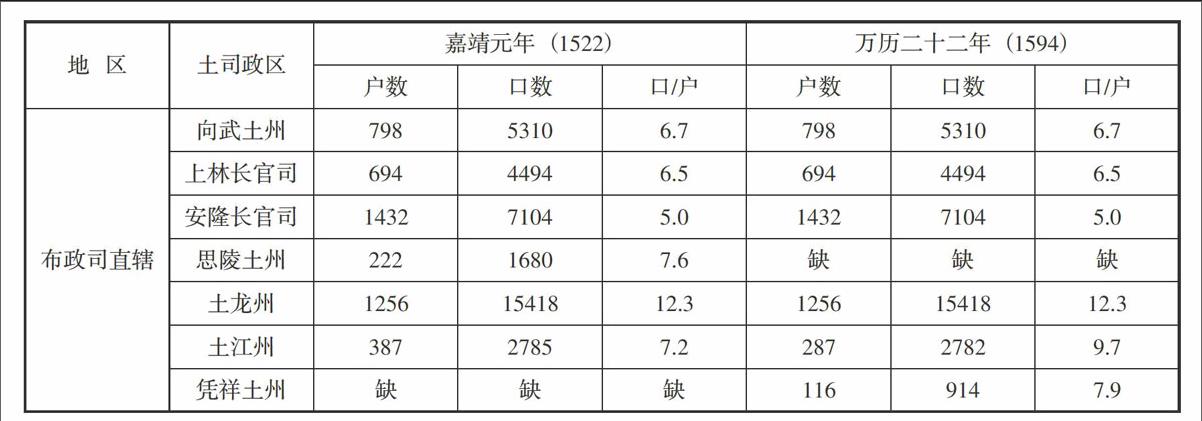

【摘 要】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其運行特點十分復雜,主要體現在“家國同構”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異性和合作共贏的依存性三個方面。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沒有一個個家庭的富裕,沒有鄉村社會的支持,就沒有國家的強盛;沒有強大的國家對家庭和鄉村社會強有力的保護,鄉村社會就不會有安寧的生活。因此,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上下互動、有效合作的關系。
【關鍵詞】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國家;特點
【作 者】李良品,長江師范學院教授,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重慶涪陵,408100;廖佳玲,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重慶北碚,400715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2 - 0134 - 007
古往今來的社會架構皆表現為家庭、社會、國家三種主要形態。[1 ]這三者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以不同方式存在。本文擬就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關系的運行特點作探討,以就正于方家。
一、“家國同構”的一致性
在傳統中國,一個家庭、一個大家族與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在政權結構和組織結構方面有其共同性,這個共同性集中體現了“家國同構”的一致性。它是以宗法關系為統領,以家長制為核心的。“家”作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細胞,是一種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她既是扎根于社會中的一種歷史的實體,也是一個包括了傳統思想、經濟結構等因素的社會單位。在明清時期的傳統中國,“家”作為社會細胞,除了具有維持家庭成員物質和感情生活的基本功能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成為維護國家專制統治的基層政治組織。“家族”是指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子孫組成的許多個體家庭,按照封建傳統的規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將最多的家庭,按照一定社會秩序結合成為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2 ]8它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廣義的家。“國家”是一個成長于社會之中而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以合法性為基礎的、帶有一定抽象性的權力機構,在其管理的領土內,“國家”擁有外部和內部的主權。這三者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族是家庭的延伸,國家則是家族的擴大。因此,在“家國同構”的明清時期,家長或族長在家庭或家族內的地位至尊,權力最大;君王或帝王在國家體系內地位至尊,權力最大。換句話說,家長或族長是家庭或家族內的一把手,是最大的管理者,而國君則是國家內的一把手,是全國子民的嚴父。父為“家君”,君為“國父”,君父同倫思想也正是來源與此。這種“家國同構”的政治模式不僅是儒家文化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而且掩蓋了階級關系和等級關系。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理想,在本質上反映了“家”與“國”之間這種同質聯系。《保靖彭氏宗譜》的《彭氏家訓》共分為修身、齊家和治國三篇,其中《修身篇》之下有“崇孝道”“正禮義”“務為學”“謹言行”“明德性”“慎交友”等六條,《齊家篇》包括“重教養”“齊家政”“尚友愛”“睦宗族”“勵勤儉”等五條;《治國篇》涵蓋“處世事”“和鄉里”“論為政”“清吏治”等四條。[3 ]可以說,這些內容均是國家在場下的封建族權與國家政權高度統一的范例,湖廣土司家族如此,其他家族可想而知。在“家國同構”的一致性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血緣關系是“家國同構”的基本依托點
眾所周知,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土司的承襲,十分重視血緣關系,也就是說,血緣關系在明清政治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央王朝的承襲是父子傳承,土司的承襲同樣是以血緣關系為主。如在土司的承襲中,明朝廷制定了一些辦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死子繼,嫡子繼承。其次是兄終弟及,叔侄相立,族屬襲替,妻妾繼襲,女媳繼職,最后是子死母襲。由此可見,土司承襲的次序是先嫡后庶,先親后疏。這體現的是一種血緣關系和親疏關系。特別是對土司承襲必須具備宗支圖本,那更是對血緣關系的硬性規定。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以無數個“親親”組織的家庭成為國家的基點,再以無數個具有血緣紐帶的家族組成國家的基本依托點。由此可見,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血緣關系無形之中成了“家國同構”的基本依托點。
(二)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忠孝是“家國同構”在倫理層面的結合點
忠孝一體,歷來是儒家學說的一貫主張。在儒家提倡的“五倫”中,將父子、君臣列于最前面,這實際上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在父權制存在的傳統社會,父子關系不僅居于家庭血緣關系之首,而且成為維系家庭關系的基礎;與此相應的,在政治等級制存在的封建國家,君臣關系不僅居于政治關系的第一位,而且也成為維系封建國家倫常的基礎。二是在傳統封建社會的明清時期,不僅家國是同構關系,而且父子、君臣同樣是一種同構關系。正是基于此,在孟子提出的“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中,“父子有親”之后接著強調“君臣有義”,這是“家國同構”關系的最集中體現。《保靖彭氏宗譜》之《彭氏家訓》的第一篇《修身篇》,開宗明義第一條便是“崇孝道”:“孝始于事親,忠始于報國。移孝以作忠,即顯親以全孝,人孝也。人子事親,無窮富當以奉養為先,奉養之道再遂其力,富者可以甘旨奉養,貧者可以菽水承歡。務須承順親志,悅以顏色,婉以言語,不可貌奉心違,以貽父母之優。子之孝,不如率婦以孝。蓋婦之居家時多,奉供飲食起居,自較周到。俗語云:“得一孝婦,勝于孝子”。[3 ]1由此可見,保靖彭氏土司家族對“孝”有著深刻的理解。我國自古有“忠孝一體”、“移忠于孝”的思想,這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倫理基礎的。[2 ]12可以說,“忠孝一體”作為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家國同構”在倫理層面的高度結合,確有其內在邏輯的合理性。
(三)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治理原則是“家國同構”在內容層面的共同點
在傳統中國,家禮是修身治家之具,國法是治國定天下之具。“家國同構”體現在家禮與國法的相通上,即將管理家庭關系的原則上升為治理國家的原則。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提倡讀書人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界。治家是治國的前提,治國是治家的放大。在傳統中國社會人與人的“差序格局”及“五倫”關系中,都十分注重“禮”,并視其為順應“差序格局”規范的行為準則。在明清時期,“家”“國”的組織系統和權利配置都是嚴格的父系家長制。國家組織結構與家族組織結構的一致,是屬于有形的可見的“家國同構”,而“家國同構”的核心是君權與父權的相互為用,君權乃是父權的延伸,父權專制的家庭模式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專制奠定了基礎。在現在還能見到的一些族譜中,對家族禮制有十分明確的規定,如《保靖彭氏宗譜》之《彭氏家訓》的第二篇《齊家篇》之“齊家政”有這樣一段文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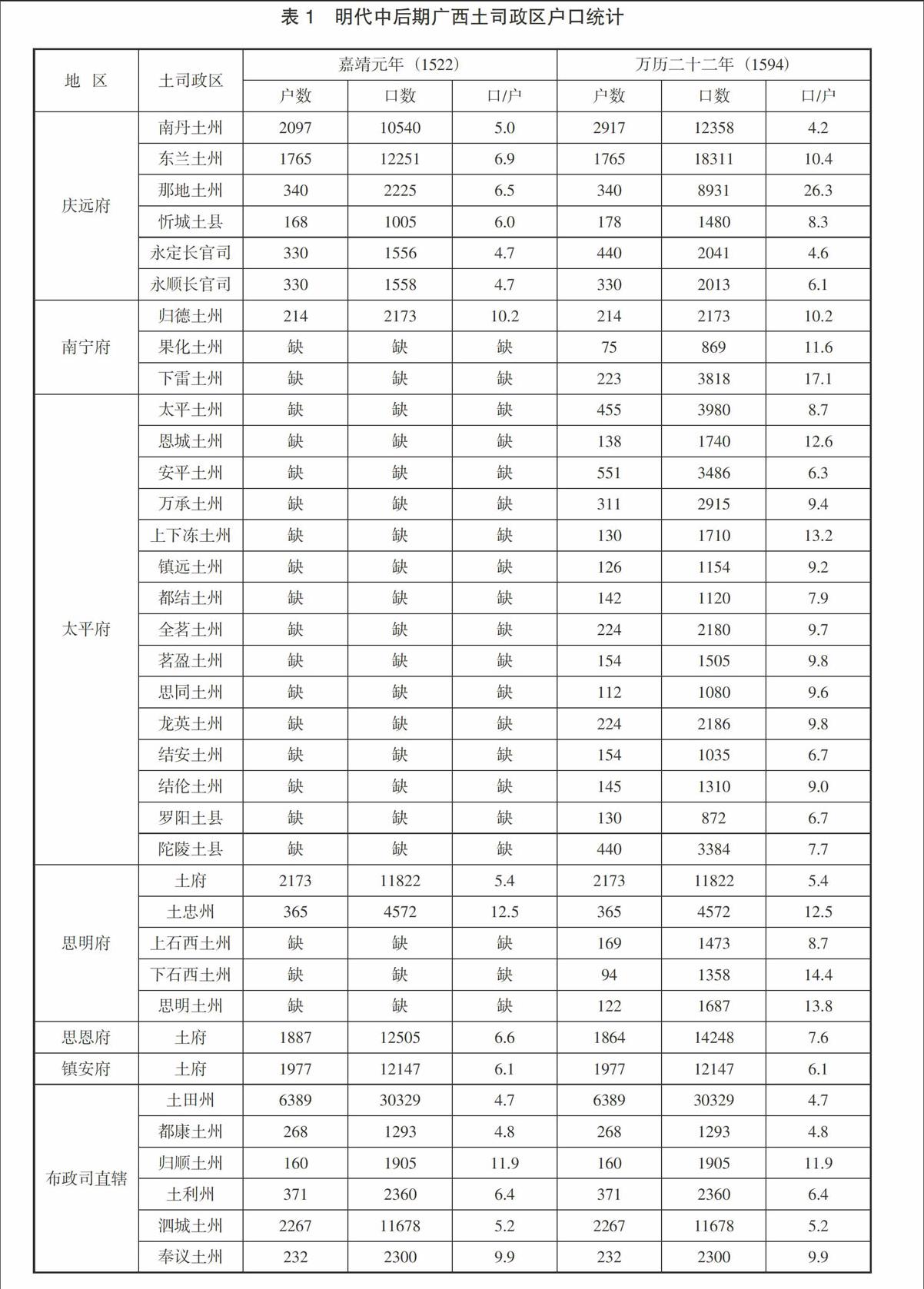
治家之道以正人倫為本,正倫以尊祖睦族、孝父母友兄弟為先,以敦親堂和鄉里為要務。近正人如父兄,遠惡人如虎狼。守之以勤儉,行之以茲鑲,約己而濟人,習禮而好德,如此可以興家,可以安身而立命。[3 ]2-3
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各族民眾,無論對家還是對國,均注重君權與父權的相互為用。因為鄉村社會以血緣關系建構的宗法,推而廣之就是國家的宗法。正是由于“家國同構”的一致性,決定了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始終未能獨立于宗法關系而存在。因此,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也遵循“家國天下”是一體的規律行事。“家”是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細胞,“國”是維護無數個社會細胞能夠健康成長的外部環境。實現“家”“國”雙向互動的良性循環,這既有利于保持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穩定和活力,又能加強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4 ]
二、“因俗而治”的差異性
國家治理理論告訴我們,國家治理應該是國家和社會(包括鄉村社會)協同共治,就當今社會而言,二者的協同共治仍是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根本要求。當然,明清時期的封建統治者沒有這樣的認識高度,他們對西南民族地區往往采取“因俗而治”的措施。“因俗而治”是包括明清統治者在內的歷代統治階級根據少數民族的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生產生活方式等制定的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邊政策。按照學界的看法,“因俗而治”就是因襲、保留少數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基本不變。如果“因俗”是根據和條件,那么,“治”就是目標與歸宿。如果根據和條件一旦發生變化,治理方式與目標也會隨之發生變化。[5 ]在一定程度上講,明清中央王朝實行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也就是在承認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各民族在歷史、地理、生產、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上存在的差異性,并根據不同民族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統治政策。這種政策體現了國家試圖通過“齊政修教”來達到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有效統治,從而實現明清統治者“大一統”的目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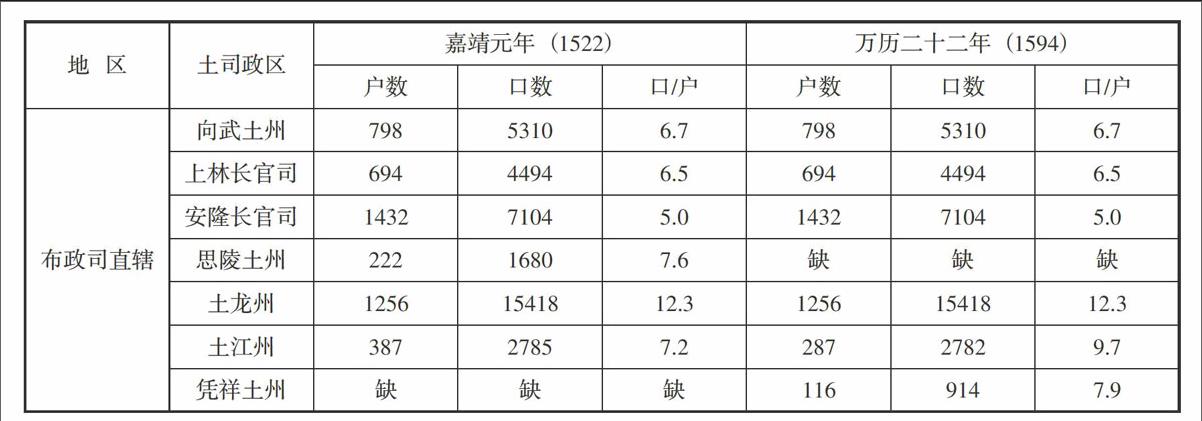
(一)政治制度
明代以降至清代前期,“因俗而治”的民族地區治理模式是把“齊政修教”提高到治邊政策的高度。因此,在這個治邊政策的指導下,明清中央政府根據西南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如同樣是實施土司制度,在川西藏族地區實行“軍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而在云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廣等少數民族地區則實行“軍政合一”的土司制度。這種“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明代及清前期對維護西南民族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雍正時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區實施大規模改土歸流,這不僅密切了西南民族地區與內地、與中央政府的聯系,而且也進一步強化了國家對西南民族地區的有效治理。當時,雍正皇帝在西南民族地區實施改土歸流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南明小朝廷負隅西南,頑強抵抗;二是吳三桂的叛亂肇始于西南,且都對清廷統治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因此,為了強化對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治理,實現全國“大一統”的目標,清王朝必然要在西南民族地區強力推行改土歸流。事實上,即便雍正皇帝實施的改土歸流不夠徹底,但這種加強對西南民族地區治理力度的方式,仍然有利于維護國家穩定和領土完整,仍然有利于實現邊疆與內地一體化以及固國安邦的愿望。[6 ]
(二)朝貢制度
明清中央王朝在對西南民族地區實施土司制度的過程中,朝貢制度為其主要內容之一。當一個土司歸附新的中央王朝后,須向中央王朝納貢。朝貢包括貢和賜兩個方面的內容,貢表現為各地土官的一種自覺行為,賜則是朝廷對朝貢土司的回賜。對各土司而言,賜甚至可以說是貢的目的。[7 ]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的土司朝貢十分踴躍,而其差異性也十分明顯:一是朝貢物品的差異性。從歷史文獻看,西南民族地區各地土司向中央王朝所貢物品多為方物。據《明會典》卷一百八載:當時西南地區“土官貢物”,除了金銀器皿、各色絨綿、各色布手巾、花藤席、降香、黃蠟、檳榔、馬、象、犀角、孔雀尾、象牙、象鉤、象鞍、象腳盤等物品之外,還有各色鐵力麻、各色氆氌、左髻、明盔、刀、毛纓,甚至還貢有胡黃連、木香、茜草、海螺、毛衣等方物。[8 ]582-585各地土司貢物情況不盡一致,如川滇黔交界地區土司主要是貢馬。可見,西南民族地區土司進獻何種貢品給皇帝,主要根據當地出產情況而定。在明代,四川播州和酉陽土司除了貢馬之外,就是獻大木。二是朝貢時間的差異性。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各地土司的朝貢或一年一貢,或三年一貢,或五年一貢。這種形成慣例的朝貢,稱為例貢。《明史》卷三百一十一載:“洪武六年,天全六番招討使高英遣子敬嚴等來朝,貢方物。……每三歲入貢。”[9 ]8031這種例貢針對不同的土司,其朝貢時間也不完全相同。清朝時,西南民族地區各地土司依然是“三年一貢”。《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六十五“土司貢賦”條載:康熙五十一年覆準,四川化林協屬各土司,三年一次貢馬,照例折價交收。[10 ]卷265除例貢之外,土司朝貢還有不定期朝貢,這類朝貢具有謝恩和謝罪性質。據《明會典》卷一百八《朝貢四》“土官”條有“謝恩無常期。貢物不等”[8 ]583之說。從這些史料記載看,中央政府除了規定各地土司“三年一貢”之外,還經常利用皇帝大壽、朝廷慶典、土司承襲、土司子弟入學等時機,要求西南民族地區的土司朝貢,并利用朝貢的機會,中央王朝與土司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對于不定期朝貢,沒有具體時間規定。至于慶賀性質的朝貢,明王朝規定,只要各地土司不錯過慶賀日子即可。如弘治六年(1493)正月,播州宣慰司派遣頭目、把事等京城謝恩慶賀,進貢馬匹,賜彩段、鈔錠有差。[11 ]868此外,還有贖罪性朝貢。這些均體現出西南民族地區土司朝貢的差異性。
(三)文教政策
明清時期“因俗而治”的民族文化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中央政府對宗教文化具有比較寬容的態度。以藏傳佛教為例:在川西藏區“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中央政府沒有采取大規模的創辦官學教育以儒化學子的方式,而是借助佛教文化,依靠“多封眾建,以教固政”的方式以達到對川西藏區的有效治理,從而實現了“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的目的。[5 ]同時,中央政府還在川西藏區設置“指揮使司、宣慰使司、元帥府、招討使司、萬戶府等,各級官吏僧俗并用,軍民兼攝。”[12 ]10明清中央政府寬容的治藏政策和寬松的政治環境,使得藏傳佛教不僅能在川西藏區迅速發展,還逐步向青海等地傳播。第二,明清中央政府“因俗而治”的政策保留和維持了西南民族地區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結構,有助于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創新,在客觀上促進了民族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如清代云南很多鄉規民約的碑刻里無不體現少數民族自覺接受國家主流文化、促進鄉村社會與國家間的文化互動的意識。試以《宜良縣萬戶莊鄉規碑(一)》為例。
公立鄉規
欲厚風俗,先正人心。然必禮教明,信義立,而后能砥節勵行,以正氣維正理于不替,使不垂訓于先。恐人心漸滅,寡廉鮮恥,不能爭自濯磨,以進于淳龐。今議立鄉規,愿我父老子弟凜遵,各以痛改前非,共登仁里。
——崇禮讓。辯上下,定民志,莫要于理教不明,則各分倒置,爭競成風,而和氣不能翔洽。惟愿吾鄉,長者正己率物,少者守分修身,斯游堯舜之世,為堯舜之民矣。
——敦信義。出入相友,有無相恤,雖異姓不啻一家。若相欺相詐,不惟親遜之風無聞,亦必孝慈友恭之道絕矣。道道率物,公平互施,當共勉之。
——禁斫伐。樹竹、花果各有其主,非其有而取之,俱屬不義。斫伐朝陽寺樹竹及人墳塋樹木者,罰豬壹口,重七十斤,酒伍拾元;斫伐人山場、園墅樹竹花果者,罰豬壹口,重陸拾斤,酒肆拾元。松樹各家畜種,亦宜加競培植。有著松毛與樹,必與管事說明。如私自取用,不與言明者,罰錢壹千文。
——禁踐踏。墳塋系人先靈憑依,如不分時牧放之人,縱放牲畜肆行踐踏者,罰豬壹口,重捌拾斤,酒陸拾元。踐踏田園、五谷、莊稼,致國賦無資,衣食無出者,罰豬壹口,重伍拾斤,酒肆拾元。
——禁偷竊。樹竹、茶果、糞草之類,各有其主。私行偷砍樹竹一株,罰銀伍錢,貳株罰銀壹兩,照數升罰。偷取豆麥、谷菜者,罰谷伍斗;偷取茶果、瓜姜等物者,罰谷伍斗;偷取糞草者,罰錢伍佰文;偷取竹筍壹支者,罰錢壹佰文,照數升罰。
以上條例,俱系公議鄉規,各宜遵守,互相覺查。見人斫伐、踐踏、偷竊,即向管事言明議罰。如互相容隱,知見不舉者,與本人同罰;亦須見查的確,不得挾仇誣人;虛誣捏報者,罰銀壹兩。
嗚呼!細行不謹,終累大德;嚴取于一介,謹嫌疑于瓜李。人生立身之大節,勿謂欺人于不見,而自敗其行。不惟孝悌友恭之無聞,而遺臭萬年,至孝子慈孫之莫改也!凡我父老子弟,各宜勸戒遵行,敢有故違,公罰毋悔。
大清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二十五吉旦 鐫立[13 ]18-19
從這則《宜良縣萬戶莊鄉規碑》可見,即便是全鄉在公議禁止斫伐、踐踏、偷竊之事,在前面也沒有忘記“崇禮讓”“敦信義”等內容,這是將國家主流文化變成了民族地區民眾的自覺行為,充分體現了文化互動與文化自覺。
三、合作共贏的依存性
從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動可以看出,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二者之間只有審時度勢、互動合作,才能實現共贏的目標。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頻繁的良性互動,其實就是一種合作。無論什么時代,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只有合作,才能實現共贏的目標,這是雙方的共同需要。如明清時期湖廣永順的彭氏土司,就在與明清中央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精誠合作中產生共贏的效果。據《清史稿》卷五百十二《土司一·湖廣》載:永順彭氏土司于清順治四年(1647),“率三知州、六長官、三百八十峒苗蠻歸附。十四年,頒給宣慰使印,并設流官經歷一員。……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納土,請歸江西祖籍,有旨嘉獎,授參將,并世襲拖沙喇哈番之職,賜銀一萬兩,聽其在江西祖籍立產安插,改永順司為府,附郭為永順縣,分永順白崖峒地為龍山縣。”[14 ]卷512從這些引文可見,永順彭氏土司與中央政府確實保持了一種有效的合作關系,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執行國家制度
永順彭氏土司在執行土司制度的過程中,認真踐行國家管理制度“地方化”的要求。經過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較為良好的互動,該地區鄉村社會的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國家需要朝著實現“大一統”的目標向前邁進時,永順土司能夠審時度勢,積極配合,主動獻土改流,并請求“歸江西祖籍”。由此可見,在自上而下地推進土司制度及改土歸流的過程中,永順彭氏土司在不斷地接受或執行“國家”制度,這是鄉村社會與國家有效合作的結果。
(二)積極納稅朝貢
作為地方土司,能夠按照國家分配的數額積極繳納“皇糧國稅”,這不僅是對國家賦稅制度執行過程中的有力支持,而且也是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合作的具體表現。永順彭氏土司積極向中央王朝進貢,而中央王朝賜給永順土司一定的賞賜,這是有效合作的最好例證。如“貢馬及方物,賜衣幣有差”[9 ]7991;又如正德“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獻大木三十,次者二百,親督運至京,子明輔所進如之。賜敕褒諭,賞進奏人鈔千貫。十三年,世麒獻大楠木四百七十,子明輔亦進大木備營建。詔世麒升都指揮使,賞蟒衣三襲,仍致仕;明輔授正三品散官,賞飛魚服三襲,賜敕獎勵,仍令鎮巡官宴勞之。”[9 ]7993尤其是彭氏土司主動改土歸流,朝廷“賜銀一萬兩”,這在清代的土司中,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可見,土司納稅朝貢等經濟方面的合作、互動,有利于加強土司首領與中央王朝的交流,減少彼此間的隔閡,增加鄉村社會對國家、對中央王朝的認同,增強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
(三)服從中央征調
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在軍事上的互動、合作主要表現為土司率領鄉村社會土兵參與征調。從歷史文獻上看,明清時期永順彭氏土司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一直處于和緩、彼此相安無事的狀態,具體表現為“征調”不斷。據張凱研究,永順土兵在明朝的征調主要分為“征蠻”“征賊”和“御邊”。永順土司土兵僅在明朝就被中央王朝征調進行大大小小戰役達54次之多,因此,中央王朝“賞賜”不絕。[15 ]正是因為永順彭氏土司與明清中央王朝保持了互動、合作的關系,所以,在改土歸流之后,湖廣巡道王柔見永順土司墳墓慘遭破壞,便要求當地官員及地方民眾保護土司文化,他在雍正十三年(1735)撰寫的《保護土司墳墓檄》文中表達了對永順彭氏土司“祖先墳墓,倘有棍徒侵削盜葬,甚至鄉僻處所有刨挖偷盜”[16 ]卷11的強烈擔憂。王柔面對這種情況,出示曉諭,要求地方官“查明三土司(永順、保靖、桑植)歷代土官墳墓共有幾處?坐落某保某甲某處山,逐細造冊,開報到道備案”[16 ]卷11。還提出對“不法棍徒侵剝樹木,恃強盜葬及刨挖偷盜等”情況以及地方官“失察”的處理。這不僅充分體現了清代朝廷命官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而且是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合作共贏的典范。
總之,只有家庭、社會、國家這三者之間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家庭、社會、國家才能穩定。無論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沒有一個個家庭的富裕,沒有鄉村社會的支持,就沒有國家的強盛;沒有強大的國家對家庭和鄉村社會強有力的保護,鄉村社會就不會有安寧的生活。由此可見,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上下互動、有效合作的關系。針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鄉村社會,明清時期的國家不是生母,便是嚴父;針對明清時期的國家,西南民族地區的鄉村社會不是親子,便是愛女,這或許從另一個視角反映出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王集權,等.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與中國家國一體倫理傳統的價值對勘[J].江海學刊,2011(1).
[2]楊金花.論“家”及其對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D].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9.
[3]彭司禮.保靖彭氏宗譜(序)[Z].保靖彭氏宗譜編委會,2008.
[4]舒敏華.“家國同構”觀念的形成、實質及其影響[J].北華大學學報,2003(2).
[5]劉淑紅.以夏變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體兩面[J].廣西民族研究,2012(3).
[6]陳躍.“因俗而治”與邊疆內地一體化——中國古代王朝治邊政策的雙重變奏[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2).
[7]李偉.烏江下游土司時期貢賦制度考略[J].貴州社會科學,2005(6).
[8]〔明〕申時行.明會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9.
[9]〔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0]〔清〕昆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
[11]李國祥,楊昶.明實錄類纂:四川史料卷[Z].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
[12]張學強.明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3]黃珺.云南鄉規民約大觀:上[M].昆明:云南出版集團公司,2012.
[14]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5]張凱,伍磊.明代永順土兵軍事征調述論[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1(6).
[16]〔清〕張天如.同治永順府志[Z].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PER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Liangpin, Liao Jialing
Abstract:The oper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very complicated. Its characteristic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isostructuralism of family and state, the diversity of "ruling by customs" and the dependencyof win-win cooperation. There is no national prosperity without getting rich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the support of rural society in anyageand any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there is no peaceful lifein the rural society without the powerful protectionof the state for the family and rural society. Thus,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state relationsshould bemutual dependency, interaction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Key Words:Ming and Qingdynasties; southwest minority area;ruralsociety;nation;characteristic
﹝責任編輯:袁麗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