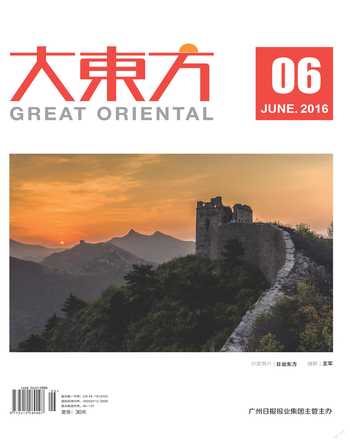爾普文化變遷的社會性別差異之比較
張潔 萬金林
摘 要:爾普文化對男女影響很深刻,盡管爾普發(fā)生了變遷,但是男女的社會性別差異在爾普文化中依舊表現(xiàn)得很突出。本研究將采用社會性別分析的方法,將人看做是有性別的,從“有性人”的角度去剖析社會現(xiàn)象,指出男女在爾普文化中存在的社會性別差異,探尋原因。
關鍵詞:爾普;社會性別;社會性別分析
一、喪葬中男性必須出爾普
民主改革前全體家支成員,無論貧窮富貴,尤其是男性,輩分在那,在喪葬中所出的最大爾普是頭牛或羊。這頭牛或羊,對非常貧困的男性來說,無疑是種巨大的經濟負擔,又因當日還要當眾公布各家所出的爾普數目,男性出于責任或顏面,甚至是借錢或者賒賬都要履行爾普義務。男子如果不出喪葬爾普,就會受到家支的冷落,甚至會被開除家支,而女性在喪葬中沒有出爾普的義務。
喪葬爾普中男、女為何會產生社會性別差異,尤其是男性為何必須出爾普?
筆者認為家支文化是男女產生社會性別差異的獨特文化背景。該文化賦予了男性這一重任,此舉動,對男性來講,不僅是責任,還是榮耀。傳統(tǒng)的性別觀念規(guī)定了男性強者身份,為了維護男性自己的尊嚴和榮譽,他們必須學會隱藏內心的想法,努力獲取成功和榮耀,顯示身份,又因要當眾公布爾普數目,男性可謂是拼了命多出爾普。男性的特權則成為一個陷阱,要求男性在任何時候都要履行其展示男子氣概的義務,這給男性帶來了緊張和壓力,對男性自由發(fā)展產生束縛。筆者通過社會性別分析進一步發(fā)現(xiàn),女性之所以沒有這項義務,完全是由于家支文化更多關注男性利益,忽視女性的存在,女性的無聲狀態(tài)看似是減輕負擔,實則是受到冷落、不平等待遇的體現(xiàn)。
隨著爾普的變遷,爾普形式可是物、錢或勞動力,且大多情況下要據事件的大小來決定出現(xiàn)何種類型的爾普,并且喪葬爾普也發(fā)生了變化,由男性全部承擔轉變?yōu)槟信餐謸俎D變到部分女性唱主角。民主改革后女性像男性一樣在喪葬爾普中開始發(fā)聲。家支家規(guī)還規(guī)定,出嫁的女兒在自己父母過世時出雙份爾普,可見開始將女性視為獨立存在的個體,只是男性依舊是是否出爾普、最終出多少的拍板者。改革開放后,喪葬爾普基本上使用人民幣。這些錢和物是男女共同勞動所得,爾普出多少,大都還是男性做主,少數家庭開始遵循女性意見。
喪葬爾普剛開始女性無資格參與,對女性存在的價值造成了忽視,后來即使有女性涉足爾普,但婦女自愿忍受性別文化對自己的規(guī)約,甘愿被否定、被忽視,參與社會活動也不會留下自己的姓名。
二、命金賠償中女性的賠償數目是男性的三倍
命金和糾紛爾普中女性命價高于男性。筆者認為其原因如下:
第一,女性具有再生產能力,殺死女人,不只是死自己一人,還會死去其傳宗接代的能力,故賠給女性的命金較多。第二,家支婚姻中的彩禮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買賣性,女性是夫家花錢買回的。第三,受大男子主義影響,涼山自古就有愛護婦孺的道德觀,男性認為女性和兒童是弱勢群體,需要保護,不允許對她們有任何傷害。
民主改革前,在糾紛處理方面,也存在社會性別差異。如拐妻案,無論女方有無過錯,男方都負主要責任。彝族諺語“拐妻賠九命,殺子賠一命”,體現(xiàn)了女性的社會價值和家庭作用,維護了夫家尊嚴。有學者或調查點的彝族男子認為:家支文化背景下的彝族女性,其地位不是我們表面看到的那么低,不是一直處于被壓迫狀態(tài),她們的責任也沒有男性的重,彝區(qū)社會在很多方面都“保護”著女性。但筆者認為“保護”,實際上反映女性的從屬地位,是對女性的忽視。比如,拐妻案表面上看女性沒有責任,實際上女性會遭受強大的輿論壓力和心理傷害。因為彝區(qū)對女性的道德要求和對女性角色定位的要求高于男性,女性因而到處受到劈頭蓋腦的輿論譴責。女性命金是男性三倍,可見女性是男性買的,涉及賠償,則彩禮錢、嫁妝錢都必須收回,出嫁有身價錢,非正常死亡有命金,女性可謂是交換的商品,用錢來衡量其價值。在尊重婦女的表象下,依舊隱藏著兩性的不平等,婦女仍沒有意識到與男性的性別角色差異,更沒有考慮如何發(fā)揮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和實現(xiàn)自身的價值。
三、男性通過爾普可以轉換宗族身份或者選擇姓氏
彝族換姓氏就等于換家支,換宗族,成為不同家支的人,想得到其他家支的保護和照顧,必須履行該家支所規(guī)定的義務。這個義務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有出爾普。女性則完全不同,她們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姓氏,出嫁前隨著父親姓,出嫁后,特別是遠嫁他鄉(xiāng),別人都不知道該女性的姓氏,只稱呼她為某某的妻子,女性根本無法更換姓氏。如果隨意更換,要么是不孝,要么就是背叛夫家。另外,前文提到爾普用于不幸之事,后來出現(xiàn)變遷,也用于喜事之中。例如通過出爾普資助貧困大學生順利完成學業(yè)。但大學生,更多的是男性,由于彝族貧窮,經濟發(fā)展水平低,女性成為大學生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說出爾普幫助的對象更多的是男性,爾普文化向積極方向變遷,男性成為受影響的主體。可見,爾普文化影響下,男女社會性別差異很明顯。
四、彝區(qū)男女爾普中的社會性別分析
現(xiàn)在彝區(qū)對糾紛的處理一般以國家法律為主,地方習慣法為輔。國家法體現(xiàn)男女一致平等,而習慣法更多的照顧女性、強力約束男性。社會提倡男女平等,女性是在平等邊緣徘徊的人,彝族女性更是最外層。因此,宏觀上要維護男女利益,實現(xiàn)平等,微觀上更注重保護女性利益,才能縮小男女差異,真正走向平等。如今爾普是以家庭為單位,男女都有義務履行,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男性,也為女性提供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女性在男性主導的文化中發(fā)出聲音,部分甚至走向主角位置,地位再次得到提高,但彝族婦女經濟上不獨立,社會政治事務上沒有過多的發(fā)言權,又因受教育程度低,婚姻制度不公平,外加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傳統(tǒng)性別觀念在文化傳承與變遷過程中通過教育活動的開展世代延續(xù)及封建禮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即使有女性成為是否出爾普、出多少的決定者,但也只占少數,彝族婦女整體上還是弱勢群體,還處于一種“混沌”狀態(tài)。
參考文獻:
[1]馬長壽遺著,李紹明、周偉洲等整理.涼山羅彝考察報告[R].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巴蜀書社,2006年.
[2]劉正發(fā).涼山彝族家支文化傳承的教育人類學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
(作者單位:玉溪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